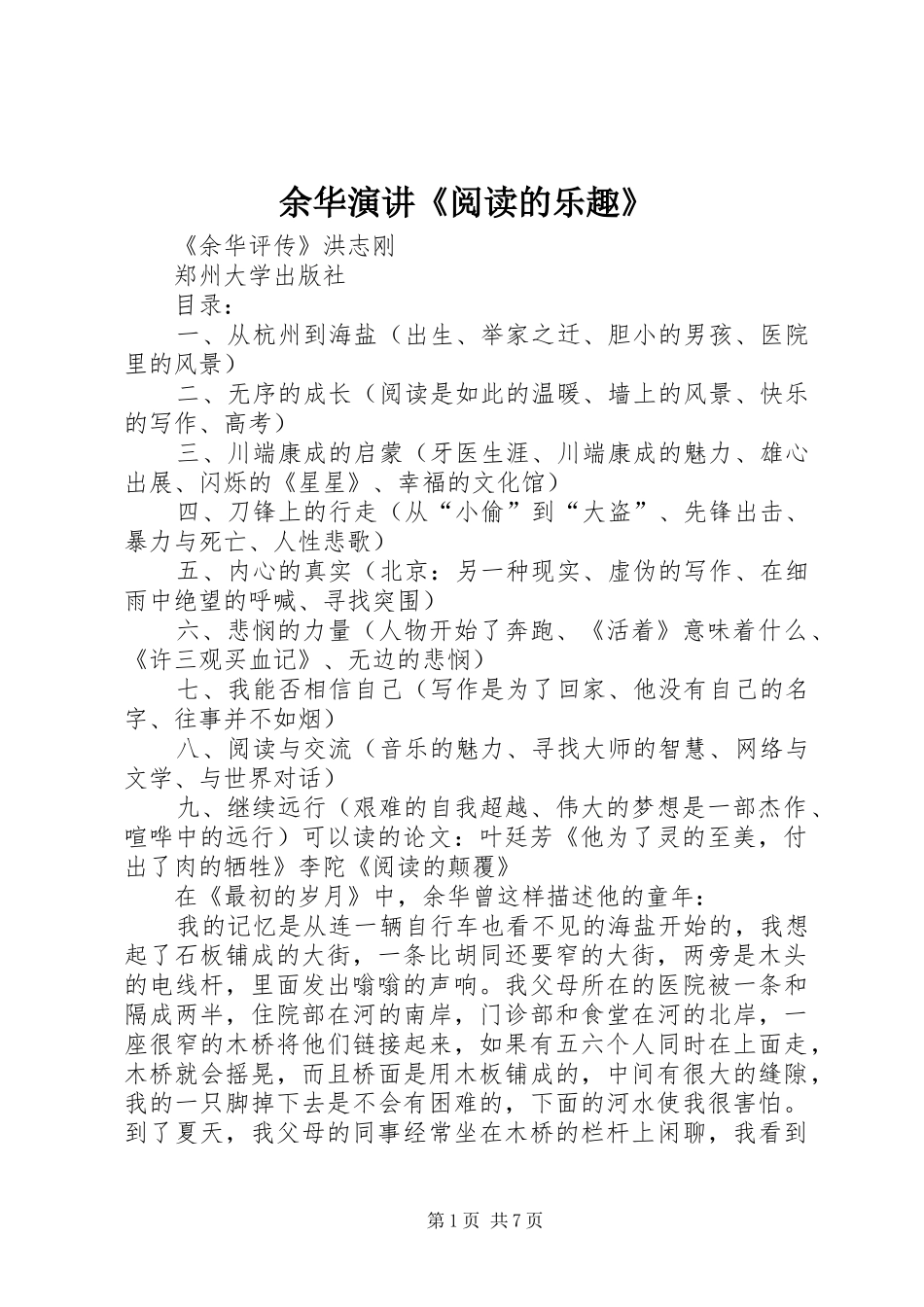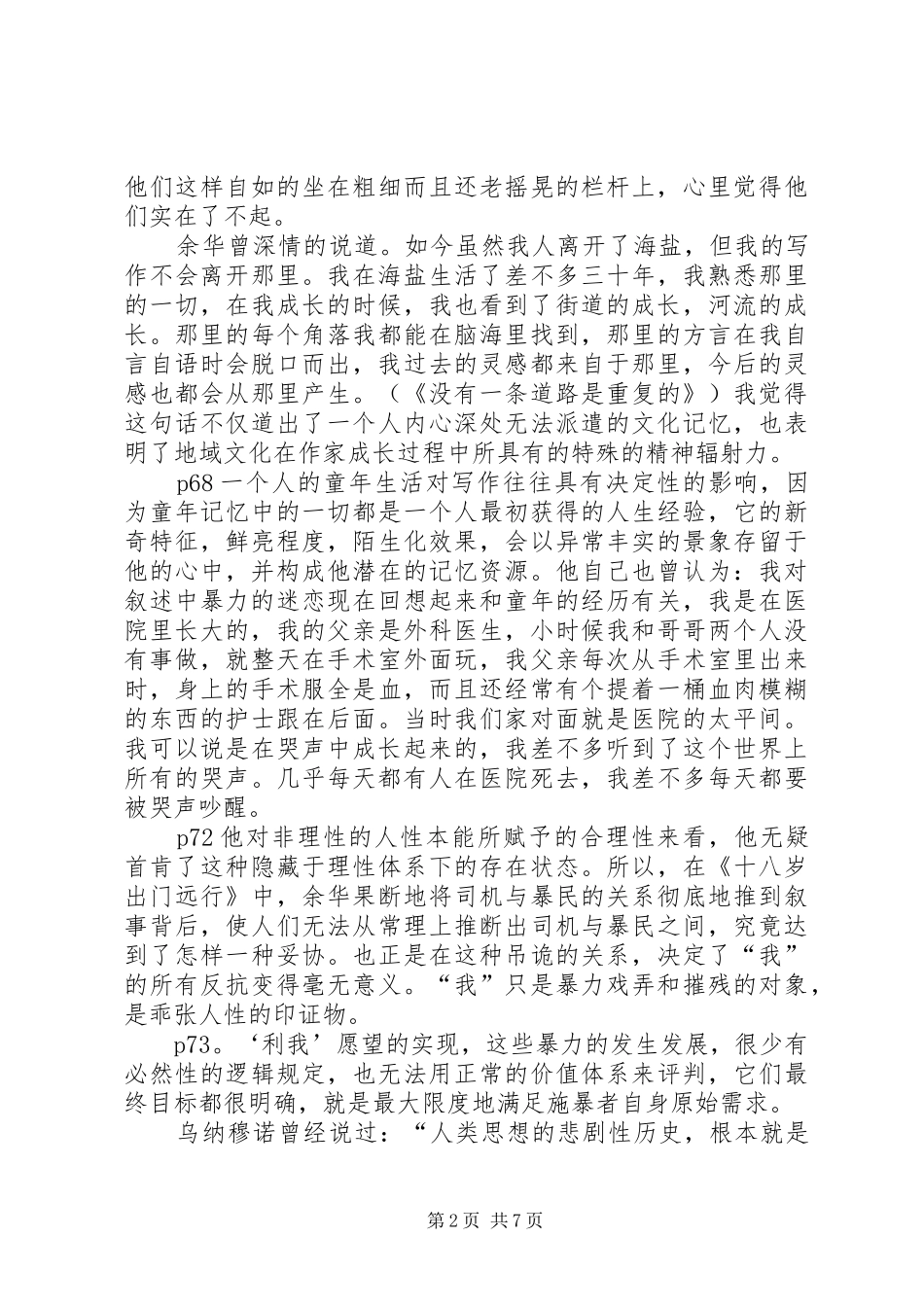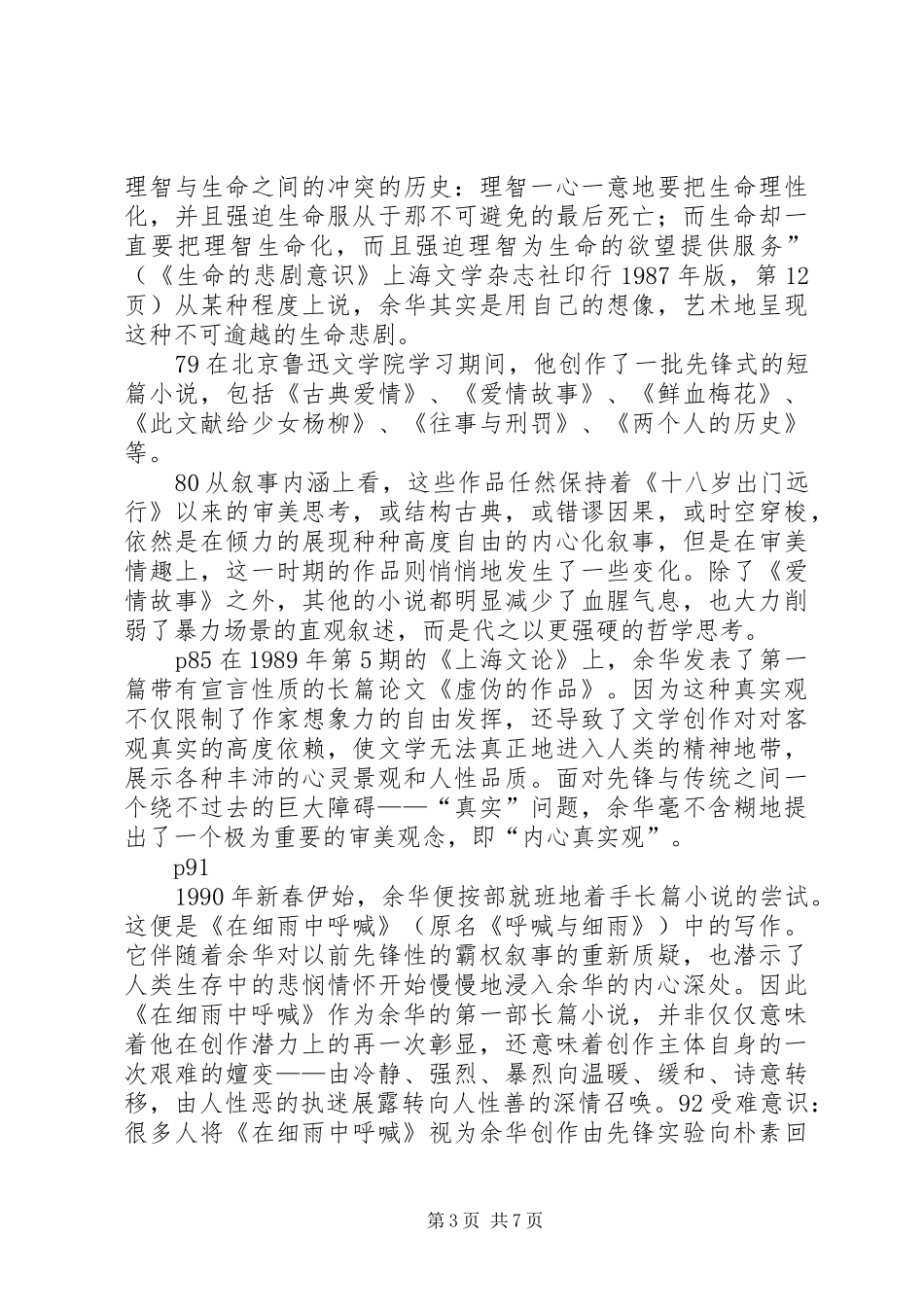余华演讲《阅读的乐趣》《余华评传》洪志刚郑州大学出版社目录:一、从杭州到海盐(出生、举家之迁、胆小的男孩、医院里的风景)二、无序的成长(阅读是如此的温暖、墙上的风景、快乐的写作、高考)三、川端康成的启蒙(牙医生涯、川端康成的魅力、雄心出展、闪烁的《星星》、幸福的文化馆)四、刀锋上的行走(从“小偷”到“大盗”、先锋出击、暴力与死亡、人性悲歌)五、内心的真实(北京:另一种现实、虚伪的写作、在细雨中绝望的呼喊、寻找突围)六、悲悯的力量(人物开始了奔跑、《活着》意味着什么、《许三观买血记》、无边的悲悯)七、我能否相信自己(写作是为了回家、他没有自己的名字、往事并不如烟)八、阅读与交流(音乐的魅力、寻找大师的智慧、网络与文学、与世界对话)九、继续远行(艰难的自我超越、伟大的梦想是一部杰作、喧哗中的远行)可以读的论文:叶廷芳《他为了灵的至美,付出了肉的牺牲》李陀《阅读的颠覆》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曾这样描述他的童年: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也看不见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和隔成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河的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他们链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是不会有困难的,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闲聊,我看到第1页共7页他们这样自如的坐在粗细而且还老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了不起。余华曾深情的说道。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海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都会从那里产生。(《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派遣的文化记忆,也表明了地域文化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辐射力。p68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写作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童年记忆中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最初获得的人生经验,它的新奇特征,鲜亮程度,陌生化效果,会以异常丰实的景象存留于他的心中,并构成他潜在的记忆资源。他自己也曾认为: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死去,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被哭声吵醒。p72他对非理性的人性本能所赋予的合理性来看,他无疑首肯了这种隐藏于理性体系下的存在状态。所以,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果断地将司机与暴民的关系彻底地推到叙事背后,使人们无法从常理上推断出司机与暴民之间,究竟达到了怎样一种妥协。也正是在这种吊诡的关系,决定了“我”的所有反抗变得毫无意义。“我”只是暴力戏弄和摧残的对象,是乖张人性的印证物。p73。‘利我’愿望的实现,这些暴力的发生发展,很少有必然性的逻辑规定,也无法用正常的价值体系来评判,它们最终目标都很明确,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施暴者自身原始需求。乌纳穆诺曾经说过:“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第2页共7页理智与生命之间的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地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生命服从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印行1987年版,第12页)从某种程度上说,余华其实是用自己的想像,艺术地呈现这种不可逾越的生命悲剧。79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创作了一批先锋式的短篇小说,包括《古典爱情》、《爱情故事》、《鲜血梅花》、《此文献给少女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