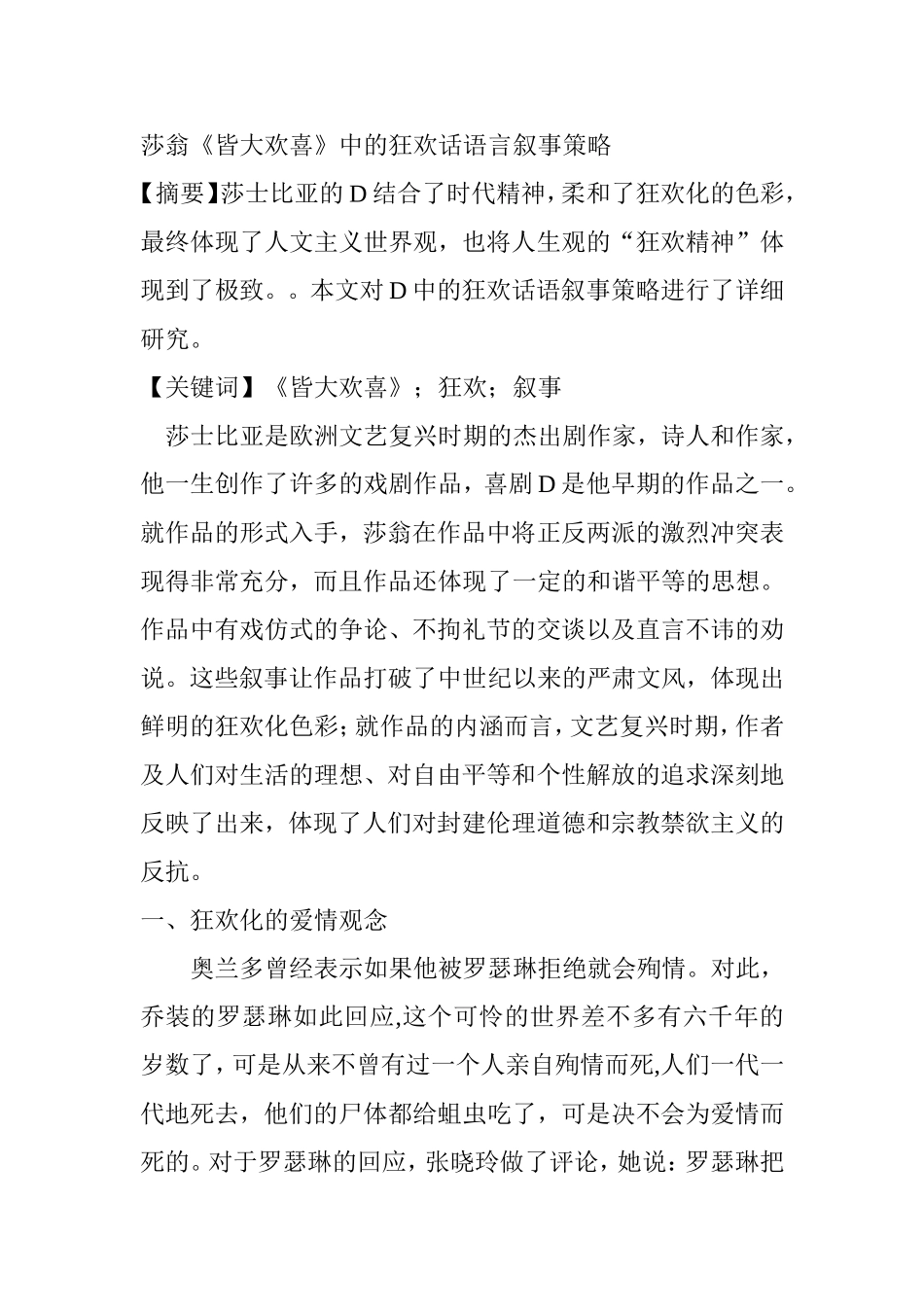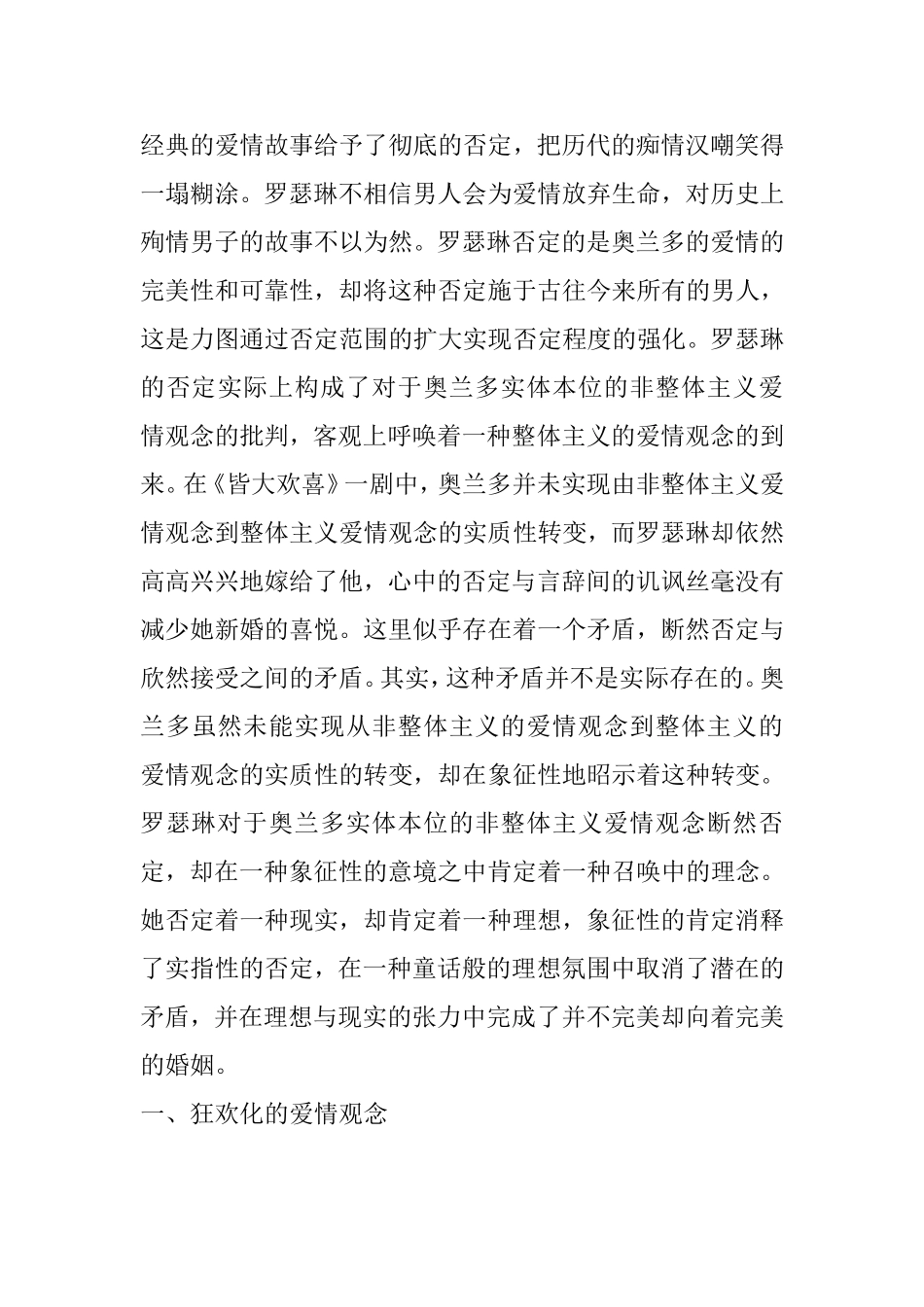莎翁《皆大欢喜》中的狂欢话语言叙事策略【摘要】莎士比亚的D结合了时代精神,柔和了狂欢化的色彩,最终体现了人文主义世界观,也将人生观的“狂欢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本文对D中的狂欢话语叙事策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关键词】《皆大欢喜》;狂欢;叙事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剧作家,诗人和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的戏剧作品,喜剧D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就作品的形式入手,莎翁在作品中将正反两派的激烈冲突表现得非常充分,而且作品还体现了一定的和谐平等的思想。作品中有戏仿式的争论、不拘礼节的交谈以及直言不讳的劝说。这些叙事让作品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的严肃文风,体现出鲜明的狂欢化色彩;就作品的内涵而言,文艺复兴时期,作者及人们对生活的理想、对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追求深刻地反映了出来,体现了人们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禁欲主义的反抗。一、狂欢化的爱情观念奥兰多曾经表示如果他被罗瑟琳拒绝就会殉情。对此,乔装的罗瑟琳如此回应,这个可怜的世界差不多有六千年的岁数了,可是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亲自殉情而死,人们一代一代地死去,他们的尸体都给蛆虫吃了,可是决不会为爱情而死的。对于罗瑟琳的回应,张晓玲做了评论,她说:罗瑟琳把经典的爱情故事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把历代的痴情汉嘲笑得一塌糊涂。罗瑟琳不相信男人会为爱情放弃生命,对历史上殉情男子的故事不以为然。罗瑟琳否定的是奥兰多的爱情的完美性和可靠性,却将这种否定施于古往今来所有的男人,这是力图通过否定范围的扩大实现否定程度的强化。罗瑟琳的否定实际上构成了对于奥兰多实体本位的非整体主义爱情观念的批判,客观上呼唤着一种整体主义的爱情观念的到来。在《皆大欢喜》一剧中,奥兰多并未实现由非整体主义爱情观念到整体主义爱情观念的实质性转变,而罗瑟琳却依然高高兴兴地嫁给了他,心中的否定与言辞间的讥讽丝毫没有减少她新婚的喜悦。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矛盾,断然否定与欣然接受之间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奥兰多虽然未能实现从非整体主义的爱情观念到整体主义的爱情观念的实质性的转变,却在象征性地昭示着这种转变。罗瑟琳对于奥兰多实体本位的非整体主义爱情观念断然否定,却在一种象征性的意境之中肯定着一种召唤中的理念。她否定着一种现实,却肯定着一种理想,象征性的肯定消释了实指性的否定,在一种童话般的理想氛围中取消了潜在的矛盾,并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了并不完美却向着完美的婚姻。一、狂欢化的爱情观念弗莱德里克的转变是一种象征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遵循着人物的生活逻辑的,而是遵循着作品的思想逻辑的;这种转变的思想意义的实现与表达依赖着整部作品的结构模式与意义模式;这种转变难以理顺其与情节线索的关系,却与作品的思想脉络达成了默契,在表层的违逆中实现了深部的契合。因而,表层的突兀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一种推动深层的意义之流的力量,这是蕴蓄在情节中的意义张力,体现了一种通过思想性表达自身的艺术性。与弗莱德里克相类似,对于奥兰多的情节设置中也存在着意义张力。不同的是,这里的意义张力不再牵涉着情节中的突转,而是牵涉着情节中的态势,不是关系着具有象征性的转变,而是关系着在象征中实现的转变。前一种转变在表层情节中自在自为,在象征中实现其意义,其存在的实现过程与其意义的实现过程相对独立。后一种转变不在表层情节中自在自为,依赖象征性的意义建构过程实现其自身,其存在的实现过程与其意义的实现过程合而为一。像该剧中的许多人物一样,奥兰多从尔虞我诈的公国来到纯粹无邪的森林,从恶的世界来到善的世界。从表层情节来看,他一直是善良的正面角色,没有经历明显的由恶向善的转变。然而,从深层结构来看,这诸多人物的“同向运动”构成了一个伦理意义提升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积聚着向上的力量,而置身其中的奥兰多也蕴蓄着一种伦理升华的潜能。在与罗瑟琳对其爱情的否定的对照中,在罗瑟琳与试金石的讥诮的言辞中,奥兰多通过象征实现转变。在此处,群体中上升性的伦理运动、罗瑟琳与试金石对于奥兰多爱情观念的讥讽以及奥兰多非整体主义的爱情观念中蕴藏的危机之间的逻辑张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