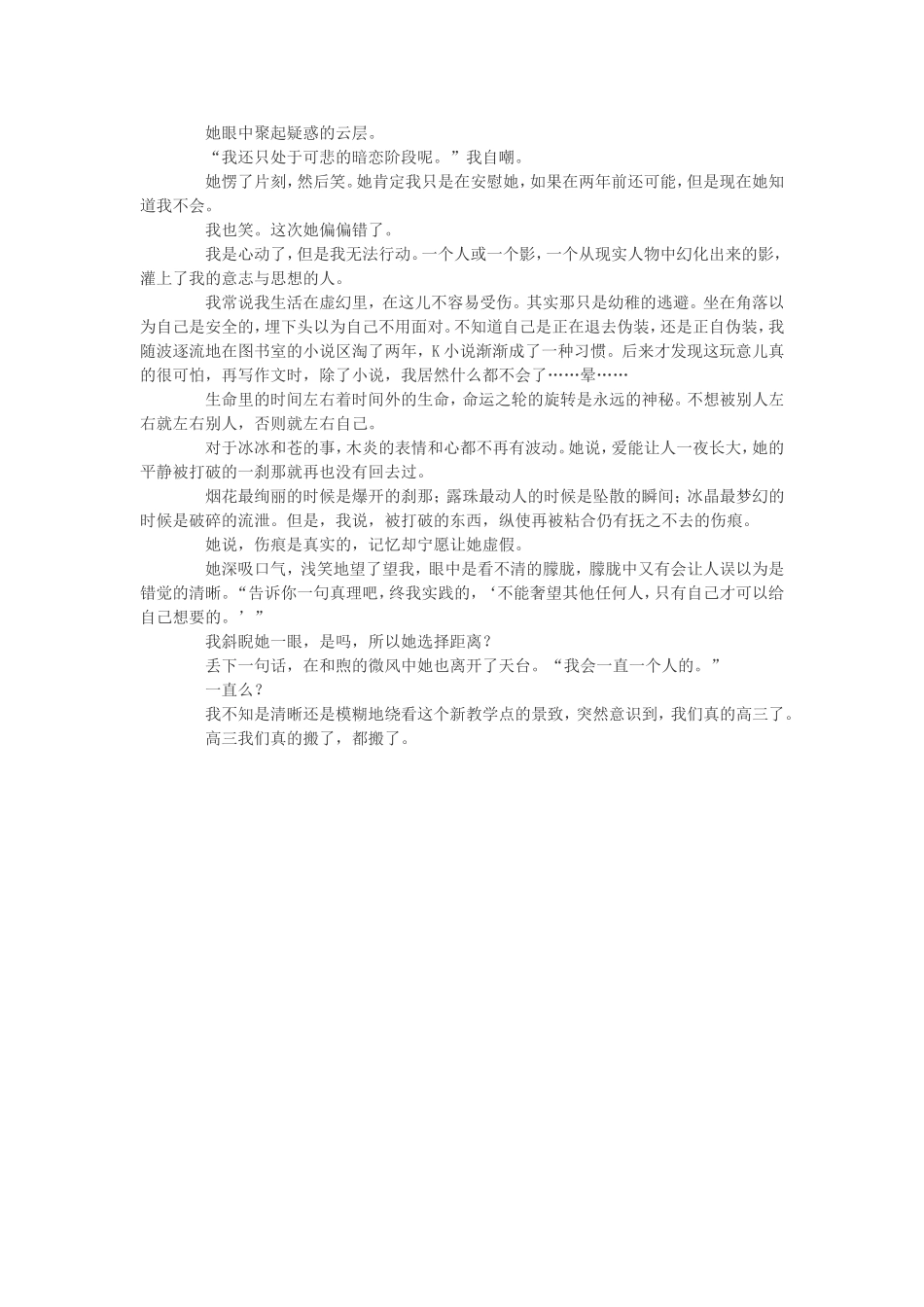高三,我们搬了沐岚逍逸开学搬教室,正常。一上高三我们搬了教室更搬了地盘。搬进了母校她儿子那儿--XX中学教学分点--一座一楼是超市、二楼是银行、三楼是教室的白色建筑。正确的名称大概应该叫做XX监狱少管分所。少管分所的教室短得让大伙不必去买强力胶也能相亲相“挨”的做直线运动(没有转身的余地),有两扇窗户可以透进新鲜空气,善哉善哉,还不至于憋闷而死。不过可惜,监狱就是监狱,铁栅栏是她的招牌,我们可以伸出双臂无法合拢的拥抱阳光,镶嵌在阳光中的是冰冷的铁栅栏。文理科班可以一解好奇地面对面地欣赏彼此的课上风景,然后是最能体现大家向心力的时候,在对相互的评论中将共鸣效应推向顶峰。真搞笑,学校的空间就那么点大却偏偏还不知满足的到处宣传广告,没有休止地招收一打又一打无辜的新学弟学妹们来压那已经不堪重负的楼道。想想高三的处境还不是普通的可怜。少管分所的“片面最惠待遇”不用再说了,住校的那群哥们儿也发扬大哥让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搬进了新家--百货商场的楼上、木板墙砌出的二十二人通间,将正宗的学生公寓让给了新来的学弟们,他们从此成为学生食堂的邻居、成为“虫拜”的偶像。无怪乎,在上高三以前的班上住校的兄弟有三十几个,而现在就只有“耶”了,两个。没办法,谁叫这群人如此这般的正直,又怎么好意思独个享受这样的“特别厚礼”呢?高三开始两周,我无比荣幸地登陆了三次“迟到光荣榜”,真是“五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全校知”。终于在帽子戏法第三次上演后,委座不能再忍受地给我开了个批斗大会,严刑逼供要我招出为何连连迟到。如果我还没因迟到的次数过多受到的刺激太大而患上暂时失忆症发话,好像前两天某某人还在高唱“迟到就是迟到,迟到没有理由”的论调。无奈我的牌是老得连牙齿都没有可掉的理由。我本就是属于飙车一族,可飙太快了也会出事,自行车它任性地跟我闹龟毛,一顿下就死活不肯继续动,开封战就此光荣。第二次,在我跨出门的瞬间,老爹突然从我身后出现,顺便蹦出一句气死人不偿命的话,你的衣服后面破了一个洞。没有迟疑地我被闪电击中,顿时石化,他倒好还事不管己啧啧有声地啜了口茶,像谈论天气般继续冒话,其实那个洞也不大,如果不仔细看还不会注意到,不过就算是看到了把当成今秋最新款式也就是了。困在我身上的咒语解开之后,我急急忙忙地冲进房间换了件衣服然后下楼取车,却很“惊喜”地发现,钥匙放在刚刚换下来的那件衣服里了……。第三次,更他妈的烈,闹钟直接没义气没油地给我慢了整整半个钟头才不慌不忙的轻声娇叹……所以我没办法大声说各位观众四张S,也就只有沉默呵沉默了。在走廊左边顺数的第二间教室,时常可以听到一个特意压低的女声,拼着不全的五音,沙沉地吼着“沧海一声笑”或“菌干儿参加了红军儿”……再看教室里的各座活雕仍旧面不改色地自做自事,那道催命夺魄符好像根本不存在。是习惯,麻木,还是早已漠然?浅笑无语。我很疯狂,在座位上拳来脚往比吃饭平常,桌上越垒越高的书,无辜地成了我练习手刀的绝佳对象。隔了处河汉界的大白便是我无影腿的青睐者,他却很扫兴地成天战战兢兢、神神经经,时刻提防着我的突袭。害我觉得自己像个魔鬼在残害祖国的幼苗,常常忍不住自责,自责过后又很郁闷,一郁闷自然要想发泄,于是黄飞鸿师父的佛山无影脚又顺承而出了……开学两周我的座位换了两次。不知是委座太低估我的外交能力以为换座位有用,还是我的功力实在太深厚,通常不到一个晚自习,身旁的同学就会乖乖地“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虽然我一般不穿裙子。不过介于我上任同桌小林子的情况,我很谨慎地问新同桌卢卢有没有强大的心里承受能力。他给我的回应是满脸写上问号地愕然。我就很好心地提醒他,不管有没有都必须做好心里准备,因为在我身边的心里能力训练课是很辛苦的。他还是将眉头拧成麻花状。我摇摇头轻声叹息,想起了小林子在与我同桌两天之后就对我说,他发现自己变浮躁了,又过了一天他无奈地抱怨他快被我搞疯了。结果呢,当然是不负众望地他被我改造得和我一起发疯。至于第一同桌,阿响,他和我坐在一起的时间最久却依然似最初那般一点没变,抵抗力强到连我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