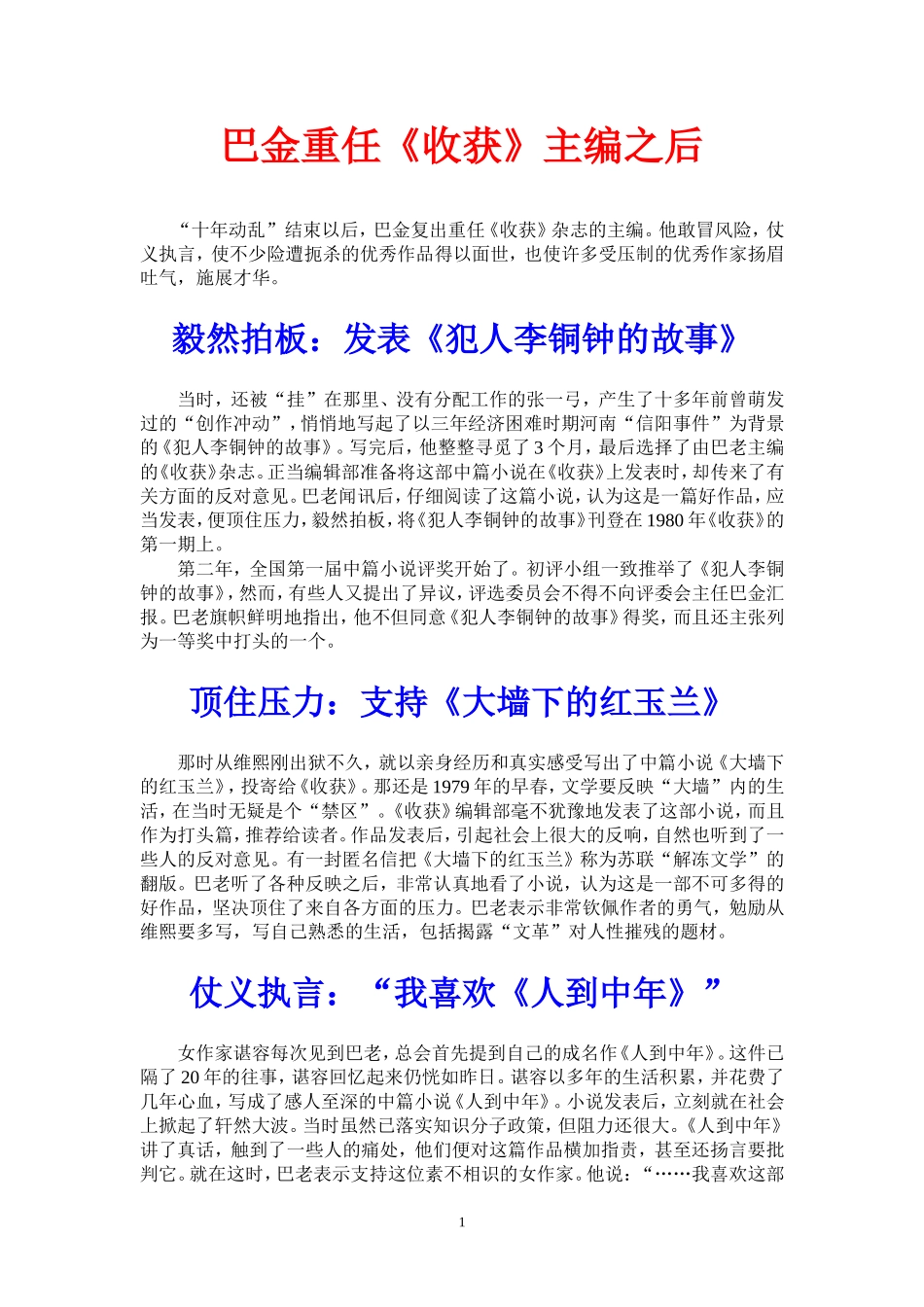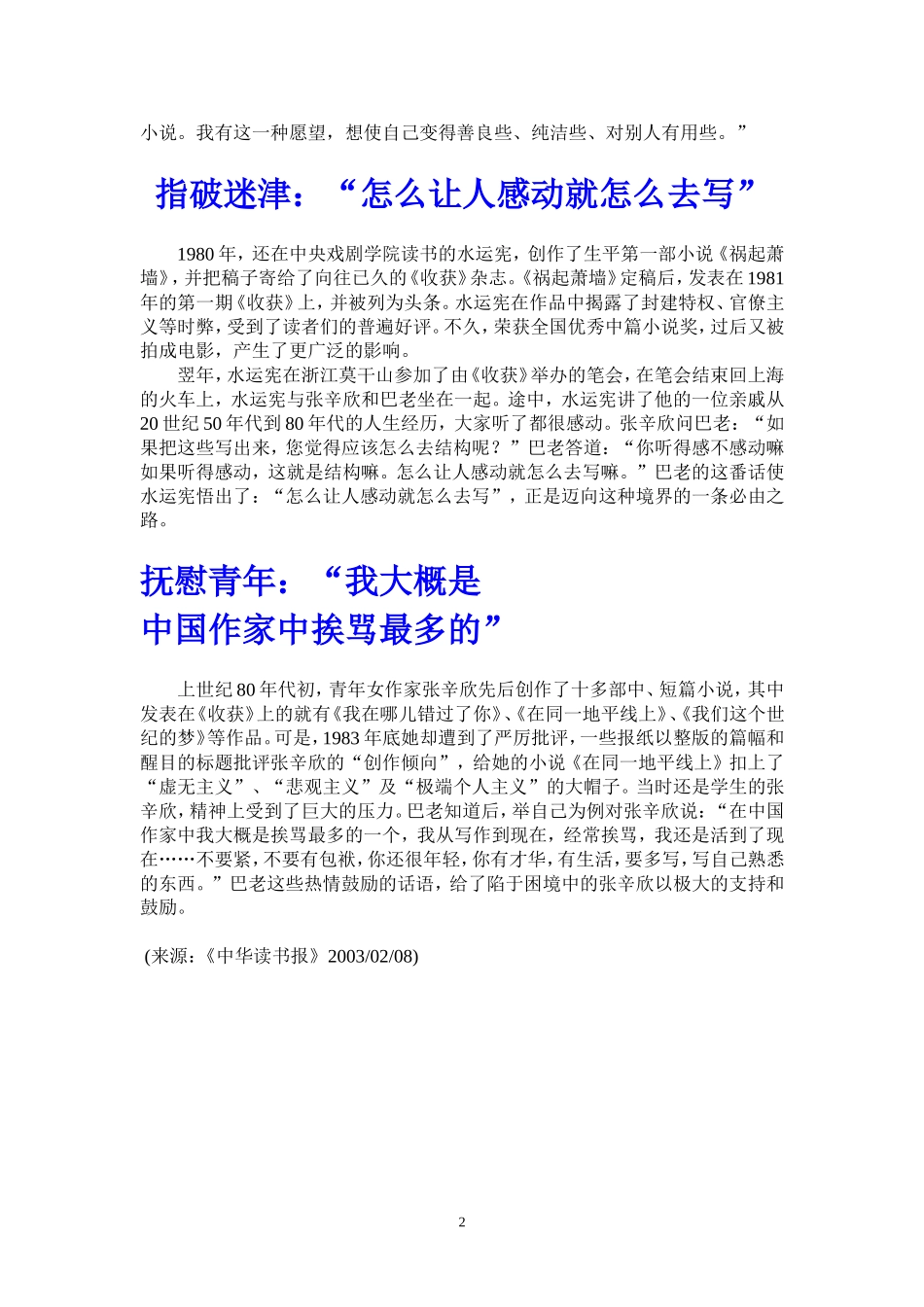巴金重任《收获》主编之后“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巴金复出重任《收获》杂志的主编。他敢冒风险,仗义执言,使不少险遭扼杀的优秀作品得以面世,也使许多受压制的优秀作家扬眉吐气,施展才华。毅然拍板:发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当时,还被“挂”在那里、没有分配工作的张一弓,产生了十多年前曾萌发过的“创作冲动”,悄悄地写起了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河南“信阳事件”为背景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完后,他整整寻觅了3个月,最后选择了由巴老主编的《收获》杂志。正当编辑部准备将这部中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时,却传来了有关方面的反对意见。巴老闻讯后,仔细阅读了这篇小说,认为这是一篇好作品,应当发表,便顶住压力,毅然拍板,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刊登在1980年《收获》的第一期上。第二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了。初评小组一致推举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然而,有些人又提出了异议,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汇报。巴老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不但同意《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得奖,而且还主张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顶住压力:支持《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时从维熙刚出狱不久,就以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写出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投寄给《收获》。那还是1979年的早春,文学要反映“大墙”内的生活,在当时无疑是个“禁区”。《收获》编辑部毫不犹豫地发表了这部小说,而且作为打头篇,推荐给读者。作品发表后,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自然也听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意见。有一封匿名信把《大墙下的红玉兰》称为苏联“解冻文学”的翻版。巴老听了各种反映之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小说,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坚决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巴老表示非常钦佩作者的勇气,勉励从维熙要多写,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包括揭露“文革”对人性摧残的题材。仗义执言:“我喜欢《人到中年》”女作家谌容每次见到巴老,总会首先提到自己的成名作《人到中年》。这件已隔了20年的往事,谌容回忆起来仍恍如昨日。谌容以多年的生活积累,并花费了几年心血,写成了感人至深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小说发表后,立刻就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虽然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阻力还很大。《人到中年》讲了真话,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他们便对这篇作品横加指责,甚至还扬言要批判它。就在这时,巴老表示支持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作家。他说:“……我喜欢这部1小说。我有这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指破迷津:“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1980年,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水运宪,创作了生平第一部小说《祸起萧墙》,并把稿子寄给了向往已久的《收获》杂志。《祸起萧墙》定稿后,发表在1981年的第一期《收获》上,并被列为头条。水运宪在作品中揭露了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等时弊,受到了读者们的普遍好评。不久,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过后又被拍成电影,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翌年,水运宪在浙江莫干山参加了由《收获》举办的笔会,在笔会结束回上海的火车上,水运宪与张辛欣和巴老坐在一起。途中,水运宪讲了他的一位亲戚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人生经历,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张辛欣问巴老:“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呢?”巴老答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就是结构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巴老的这番话使水运宪悟出了:“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正是迈向这种境界的一条必由之路。抚慰青年:“我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挨骂最多的”上世纪80年代初,青年女作家张辛欣先后创作了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发表在《收获》上的就有《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世纪的梦》等作品。可是,1983年底她却遭到了严厉批评,一些报纸以整版的篇幅和醒目的标题批评张辛欣的“创作倾向”,给她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扣上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及“极端个人主义”的大帽子。当时还是学生的张辛欣,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巴老知道后,举自己为例对张辛欣说:“在中国作家中我大概是挨骂最多的一个,我从写作到现在,经常挨骂,我还是活到了现在……不要紧,不要有包袱,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