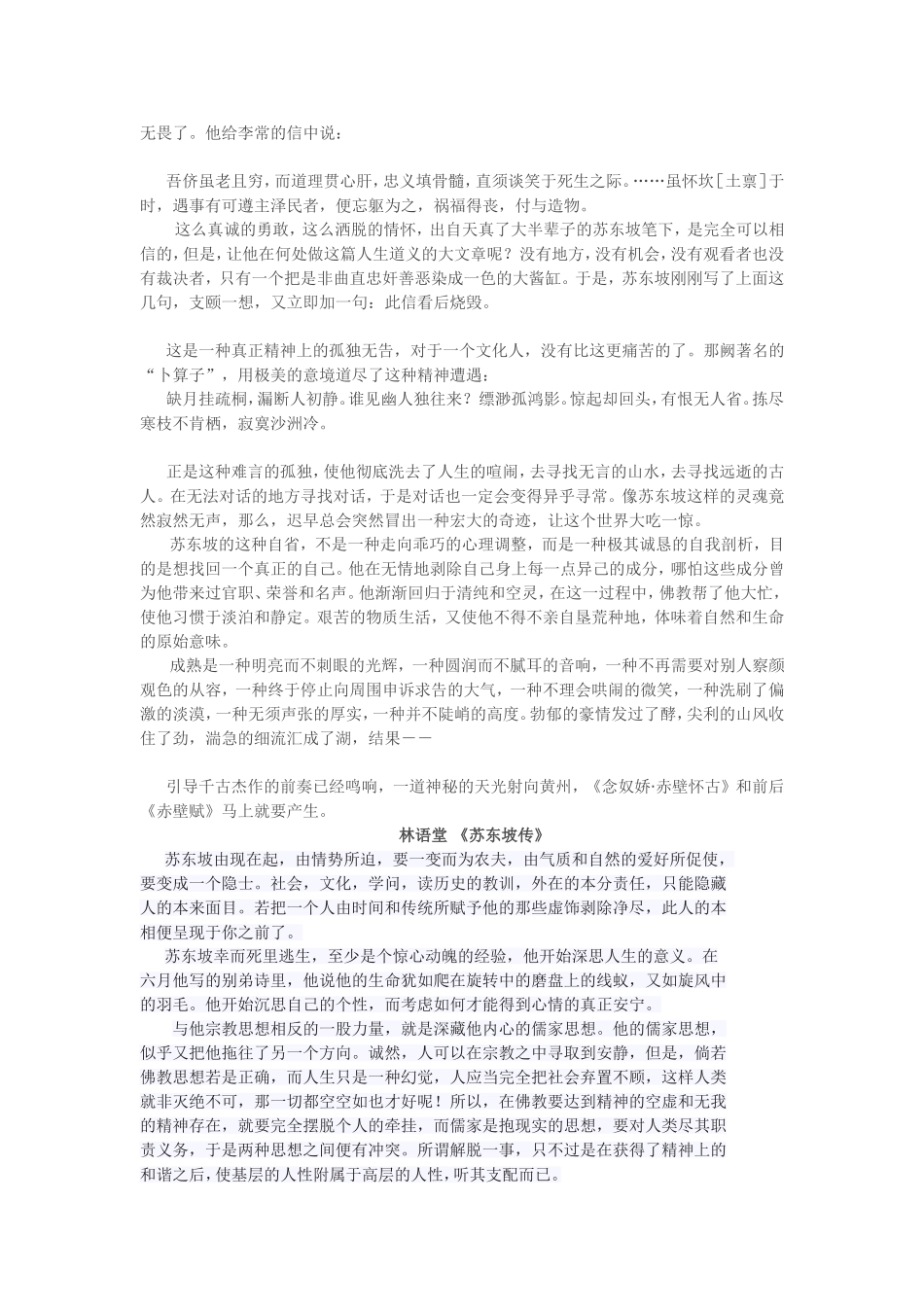沈从文:一个人的沙场“文革”伊始,德高望重的他陷入了非人的境地。批斗无数,每天还要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厕所。1969年,他又被下放到多雨泥泞的湖北咸宁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移居”咸宁后,没有组织归属,他光搬家就达6次之多。由区委阴暗的阁楼,搬进小学的泥巴房教室,再被打发到偏僻的乡村医务所……而他每天的任务则是看守菜园子,做猪倌。当时他已经67岁,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可他毫不在意。盛夏时节,荷花开了,朵朵亭亭玉立。他写信给自己的表侄黄永玉:“风雨中水淹了屋,我在屋里打个伞,很好玩啊!”“这里四周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看荷花……”脚下虽多泥泞,眼前却荷花正好。几句话,竟使那苦难的日子飘满了荷花的清香。他是文学巨匠沈从文。干校岁月里,仅凭记忆,他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皇皇巨著的补充材料。其间,他还赋诗、作文、写信,干了不少“文事”,不叫一日闲过。困顿来袭时,是什么让沈从文反败为胜?是直面磨难的态势与胸襟。其实,在与苦难的拉锯战中,人更多时候是在与自身斗争:战胜沮丧,战胜恐惧,战胜放弃……在这一个人的沙场里,只要你摒弃悲观,把困境放到生活的另一个坐标系里去称量,再从中寻求通往从容和成功的暗道,你就能完成在苦难中最华丽的一次转身。恰如《老人与海》中所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苏轼满分作文泡一杯清茶,翻开《东坡精选》,大江的涛声在我耳边回响,一个身影缓缓向我走来……多情造就了他的豪迈,豪迈造就了他的豁达,豁达造就了他风雨无阻的一生。苏轼似水,温柔多情。“点点是离人泪。”他毫不掩饰内心的伤感,甚至有时还会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经历。天人永隔的离别,刻骨铭心的思念,肝肠寸断的痛苦,宛若小溪般静静地流淌,一直流到天尽头。一位至情文人,不在乎“男儿流血不流泪”的名言,不理会“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劝谏,他诉说着他灵魂深处浅浅的相思,淡淡的哀愁。他大笔一挥,在纸上留下了自己的相思苦。苏轼似江,奔腾豪迈。他曾在波涛汹涌的赤壁下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正合他意。他不拘泥于小节,只爱如画的江山。他有博大的胸怀,冲天的豪气,造就磅礴的诗篇,气势好似一落千丈的瀑布,慷慨激昂。真是“人如其词,词如其人。”滔滔江水流不尽的是他的豪情壮志……可是生活总会有很多无奈,愿望不可能总会实现。苏轼一生风雨,一生坎坷。乌台诗案,不禁令人感叹:“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然而,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名字都在那里的人们心中留下烙印。世道扭曲如何?孤独一生又如何?“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淡淡的一笑,接受住所有的打击。“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他把豁达铺洒,让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似酒般爽快。“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把乐观宣扬,将被贬的痛苦转化为理性的思索,不让自己在名利场中迷失了方向……一旦进入政坛,卷入这污浊的洪流中,有思想的人便会难以立足。难得的是你当一身抱负,仕途不顺时,在辗转漂泊中,你仍能保持一颗清澈、豁达、豪迈的心。在中秋之夜吟“明月几时有”;在赤壁之畔作“一时多少豪杰”;在密州之林诵“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的生活是多么的充实。最让人佩服的是你超然物外,不计得失,能尽情享受自然赋予的山间明月和大江波涛,这又是怎样的心境?而我又何其有幸,能在千年之后细吟你的诗词,留下满口余香;能在悲观寂寞时,膜拜你的豁达,寻找一湾心中的清泉;能在失意落魄时与你对话,寻找一份面对挫折与困难的坦然和从容。合起书页,我闭上眼回味着。一个豪迈、豁达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哈哈哈哈……”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片段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