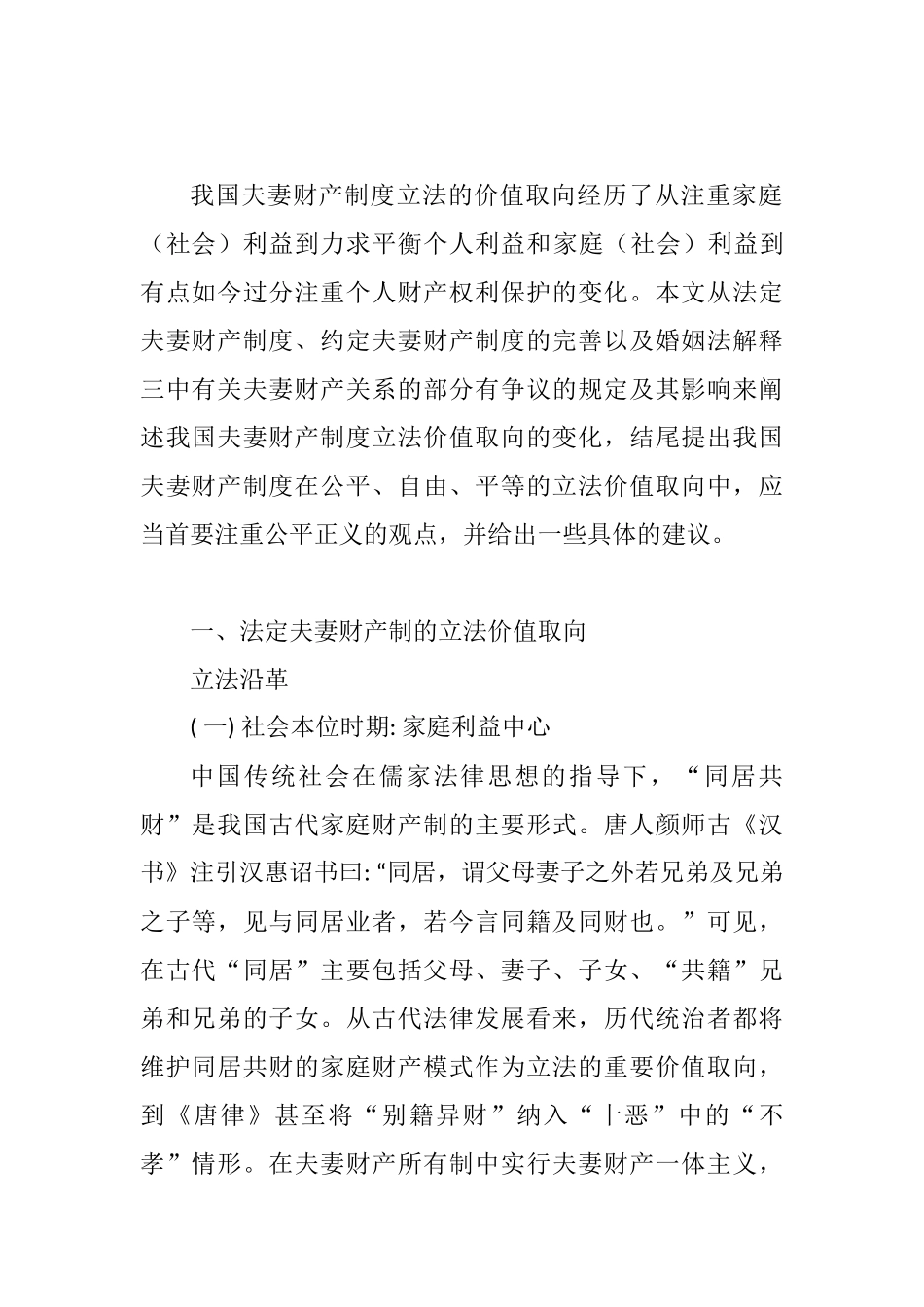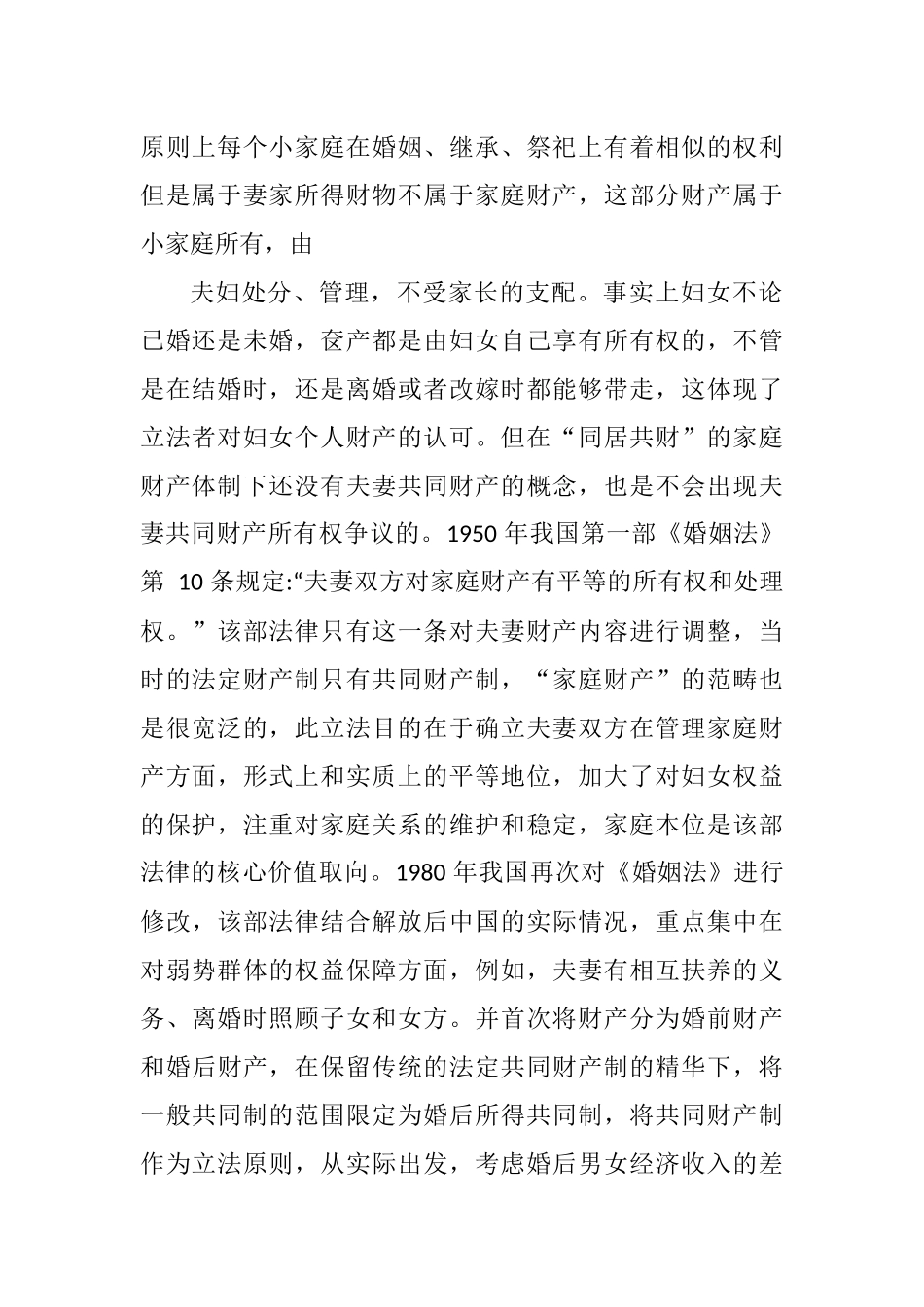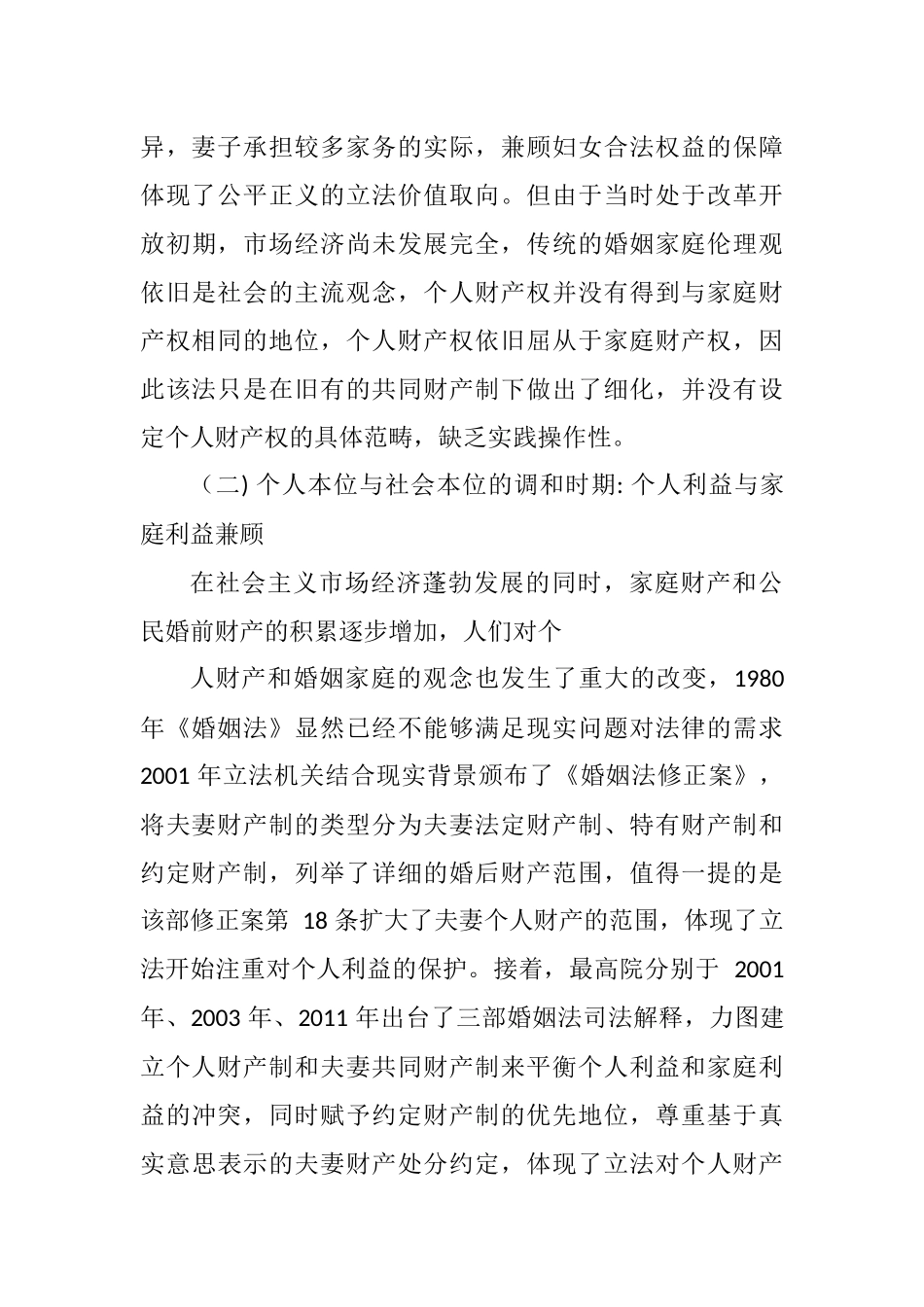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注重家庭(社会)利益到力求平衡个人利益和家庭(社会)利益到有点如今过分注重个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变化。本文从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约定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以及婚姻法解释三中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部分有争议的规定及其影响来阐述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立法价值取向的变化,结尾提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公平、自由、平等的立法价值取向中,应当首要注重公平正义的观点,并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一、法定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价值取向立法沿革(一)社会本位时期:家庭利益中心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家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同居共财”是我国古代家庭财产制的主要形式。唐人颜师古《汉书》注引汉惠诏书曰:“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可见,在古代“同居”主要包括父母、妻子、子女、“共籍”兄弟和兄弟的子女。从古代法律发展看来,历代统治者都将维护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模式作为立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到《唐律》甚至将“别籍异财”纳入“十恶”中的“不孝”情形。在夫妻财产所有制中实行夫妻财产一体主义,原则上每个小家庭在婚姻、继承、祭祀上有着相似的权利但是属于妻家所得财物不属于家庭财产,这部分财产属于小家庭所有,由夫妇处分、管理,不受家长的支配。事实上妇女不论已婚还是未婚,奁产都是由妇女自己享有所有权的,不管是在结婚时,还是离婚或者改嫁时都能够带走,这体现了立法者对妇女个人财产的认可。但在“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体制下还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也是不会出现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争议的。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该部法律只有这一条对夫妻财产内容进行调整,当时的法定财产制只有共同财产制,“家庭财产”的范畴也是很宽泛的,此立法目的在于确立夫妻双方在管理家庭财产方面,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平等地位,加大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注重对家庭关系的维护和稳定,家庭本位是该部法律的核心价值取向。1980年我国再次对《婚姻法》进行修改,该部法律结合解放后中国的实际情况,重点集中在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方面,例如,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离婚时照顾子女和女方。并首次将财产分为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在保留传统的法定共同财产制的精华下,将一般共同制的范围限定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将共同财产制作为立法原则,从实际出发,考虑婚后男女经济收入的差异,妻子承担较多家务的实际,兼顾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取向。但由于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尚未发展完全,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观依旧是社会的主流观念,个人财产权并没有得到与家庭财产权相同的地位,个人财产权依旧屈从于家庭财产权,因此该法只是在旧有的共同财产制下做出了细化,并没有设定个人财产权的具体范畴,缺乏实践操作性。(二)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调和时期: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兼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家庭财产和公民婚前财产的积累逐步增加,人们对个人财产和婚姻家庭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980年《婚姻法》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实问题对法律的需求2001年立法机关结合现实背景颁布了《婚姻法修正案》,将夫妻财产制的类型分为夫妻法定财产制、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列举了详细的婚后财产范围,值得一提的是该部修正案第18条扩大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体现了立法开始注重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接着,最高院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11年出台了三部婚姻法司法解释,力图建立个人财产制和夫妻共同财产制来平衡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冲突,同时赋予约定财产制的优先地位,尊重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夫妻财产处分约定,体现了立法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加强了实践操作性,我国夫妻财产制实现了从形式主义向实质主义的转变。(三)伦理价值的淡化时期:过分偏重财产利益2011年最高院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很多民众认为该立法使得“男人笑,女人愁”。此次司法解释就实践中出现的夫妻财产争议问题给出解决办法,主要围绕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和离婚时的财产分等问题展开,最高院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