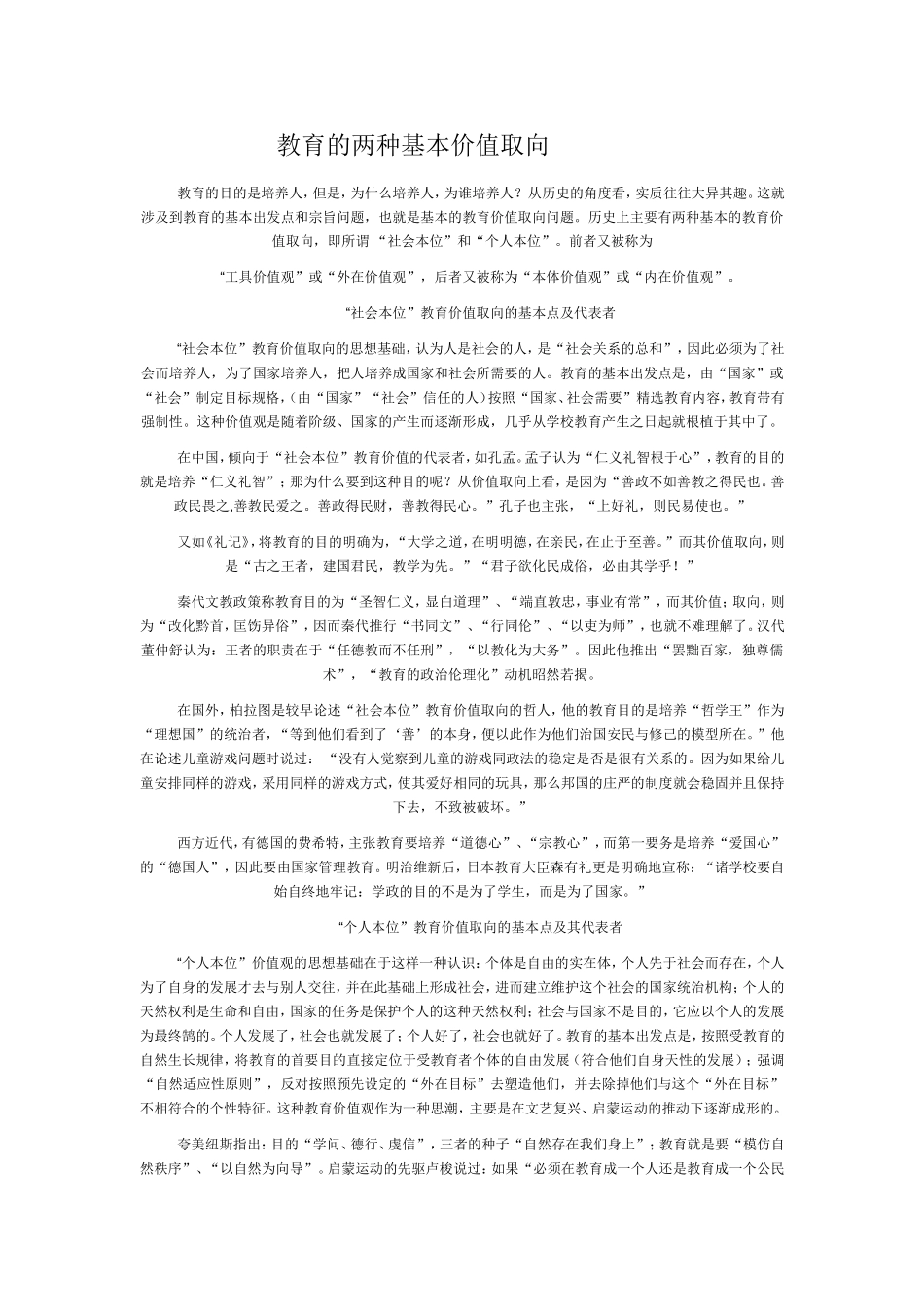教育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但是,为什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实质往往大异其趣。这就涉及到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宗旨问题,也就是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两种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即所谓“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前者又被称为“工具价值观”或“外在价值观”,后者又被称为“本体价值观”或“内在价值观”。“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点及代表者“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思想基础,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必须为了社会而培养人,为了国家培养人,把人培养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由“国家”或“社会”制定目标规格,(由“国家”“社会”信任的人)按照“国家、社会需要”精选教育内容,教育带有强制性。这种价值观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形成,几乎从学校教育产生之日起就根植于其中了。在中国,倾向于“社会本位”教育价值的代表者,如孔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仁义礼智”;那为什么要到这种目的呢?从价值取向上看,是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孔子也主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又如《礼记》,将教育的目的明确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其价值取向,则是“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其学乎!”秦代文教政策称教育目的为“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而其价值;取向,则为“改化黔首,匡饬异俗”,因而秦代推行“书同文”、“行同伦”、“以吏为师”,也就不难理解了。汉代董仲舒认为:王者的职责在于“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因此他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动机昭然若揭。在国外,柏拉图是较早论述“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哲人,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哲学王”作为“理想国”的统治者,“等到他们看到了‘善’的本身,便以此作为他们治国安民与修己的模型所在。”他在论述儿童游戏问题时说过:“没有人觉察到儿童的游戏同政法的稳定是否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给儿童安排同样的游戏,采用同样的游戏方式,使其爱好相同的玩具,那么邦国的庄严的制度就会稳固并且保持下去,不致被破坏。”西方近代,有德国的费希特,主张教育要培养“道德心”、“宗教心”,而第一要务是培养“爱国心”的“德国人”,因此要由国家管理教育。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大臣森有礼更是明确地宣称:“诸学校要自始自终地牢记:学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学生,而是为了国家。”“个人本位”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点及其代表者“个人本位”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在于这样一种认识:个体是自由的实在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为了自身的发展才去与别人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进而建立维护这个社会的国家统治机构;个人的天然权利是生命和自由,国家的任务是保护个人的这种天然权利;社会与国家不是目的,它应以个人的发展为最终鹄的。个人发展了,社会也就发展了;个人好了,社会也就好了。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按照受教育的自然生长规律,将教育的首要目的直接定位于受教育者个体的自由发展(符合他们自身天性的发展);强调“自然适应性原则”,反对按照预先设定的“外在目标”去塑造他们,并去除掉他们与这个“外在目标”不相符合的个性特征。这种教育价值观作为一种思潮,主要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推动下逐渐成形的。夸美纽斯指出:目的“学问、德行、虔信”,三者的种子“自然存在我们身上”;教育就是要“模仿自然秩序”、“以自然为向导”。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说过:如果“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从我的门下除去,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而要培养这种“自然人”,就需要实施“自由教育”。康德将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培养理性人和道德人,他最著名的名言之一是:“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穆勒曾经认为:“盖所恶于国家之教育者,彼将立一格焉,以陶铸一国,使务归于冥同,如一壠之禾,如一丘之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