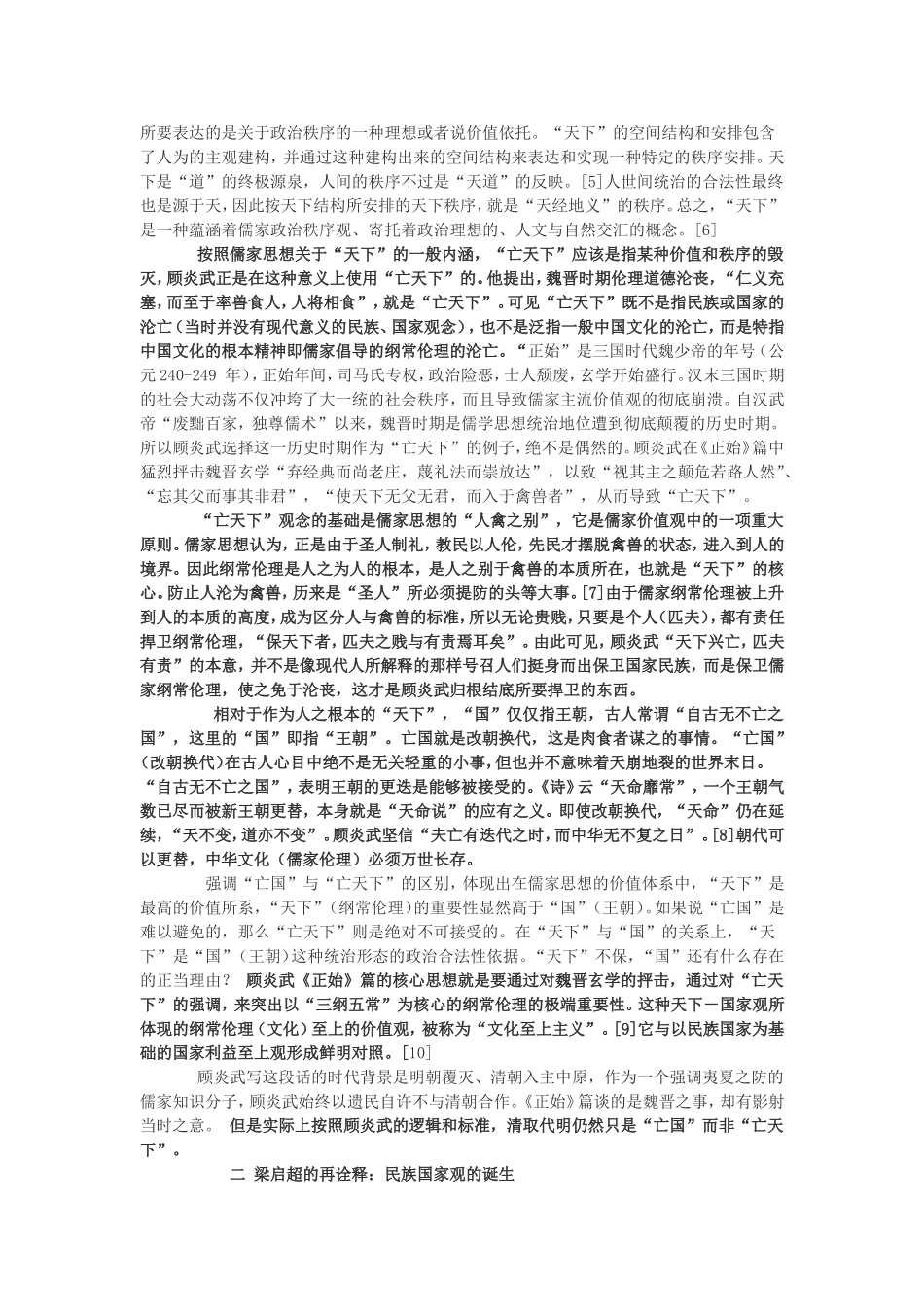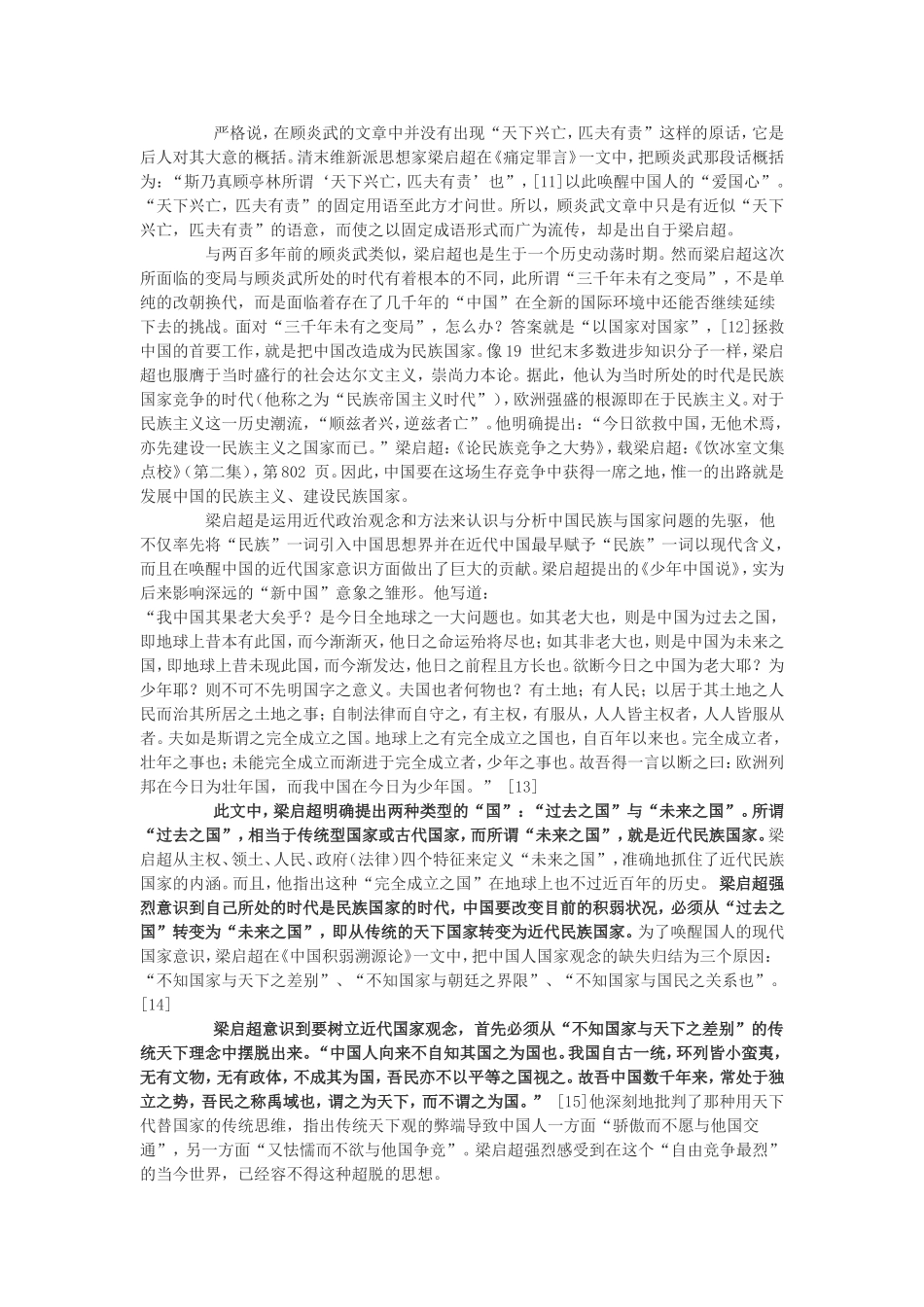“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内容提要】顾炎武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是捍卫儒家纲常伦理。梁启超在对这句话的运用中,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由此展现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中国被裹胁进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即体系对单元的塑造是这一转型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自身的传统内涵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路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延续性和统一得到保持。【关键词】天下;国家;民族国家;中国中国在东亚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了数千年,而且还造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朝贡体系。鸦片战争以降,朝贡体系在西方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下一步步走向解体。[1]随着体系的崩溃,作为体系核心的中国也发生了痛苦而深刻的变化,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实质就是中国存在方式的危机。中国从朝贡体系到被裹胁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的再定义过程。这个重新定义的过程表现为从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转变。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内部从思想意识到组织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它在思想观念上的体现是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演变,亦即从“文化至上主义”的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观的转变。[2]本文不是全面考察这一过程,而是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的本意、它在后人的引用中如何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以及这种新的含义透射出何种变迁这一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特点。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即体系对单元的塑造是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体系的塑造,中国自身的传统内涵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路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亡国与亡天下:文化至上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对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现代人一般这样理解该名言: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关心国家大事,它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汉语大词典》将之解释为“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这种现代诠释如此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以至于它的本意被忽视。[3]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典出《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偏于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从顾炎武的原文可以看出,他的本意在于区别“天下”与“国”。“天下”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在作为儒家人生理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平天下”是政治理想的最高目标。“天下”寄托着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它所要表达的是关于政治秩序的一种理想或者说价值依托。“天下”的空间结构和安排包含了人为的主观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出来的空间结构来表达和实现一种特定的秩序安排。天下是“道”的终极源泉,人间的秩序不过是“天道”的反映。[5]人世间统治的合法性最终也是源于天,因此按天下结构所安排的天下秩序,就是“天经地义”的秩序。总之,“天下”是一种蕴涵着儒家政治秩序观、寄托着政治理想的、人文与自然交汇的概念。[6]按照儒家思想关于“天下”的一般内涵,“亡天下”应该是指某种价值和秩序的毁灭,顾炎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亡天下”的。他提出,魏晋时期伦理道德沦丧,“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亡天下”。可见“亡天下”既不是指民族或国家的沦亡(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也不是泛指一般中国文化的沦亡,而是特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的沦亡。“正始”是三国时代魏少帝的年号(公元240-249年),正始年间,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士人颓废,玄学开始盛行。汉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