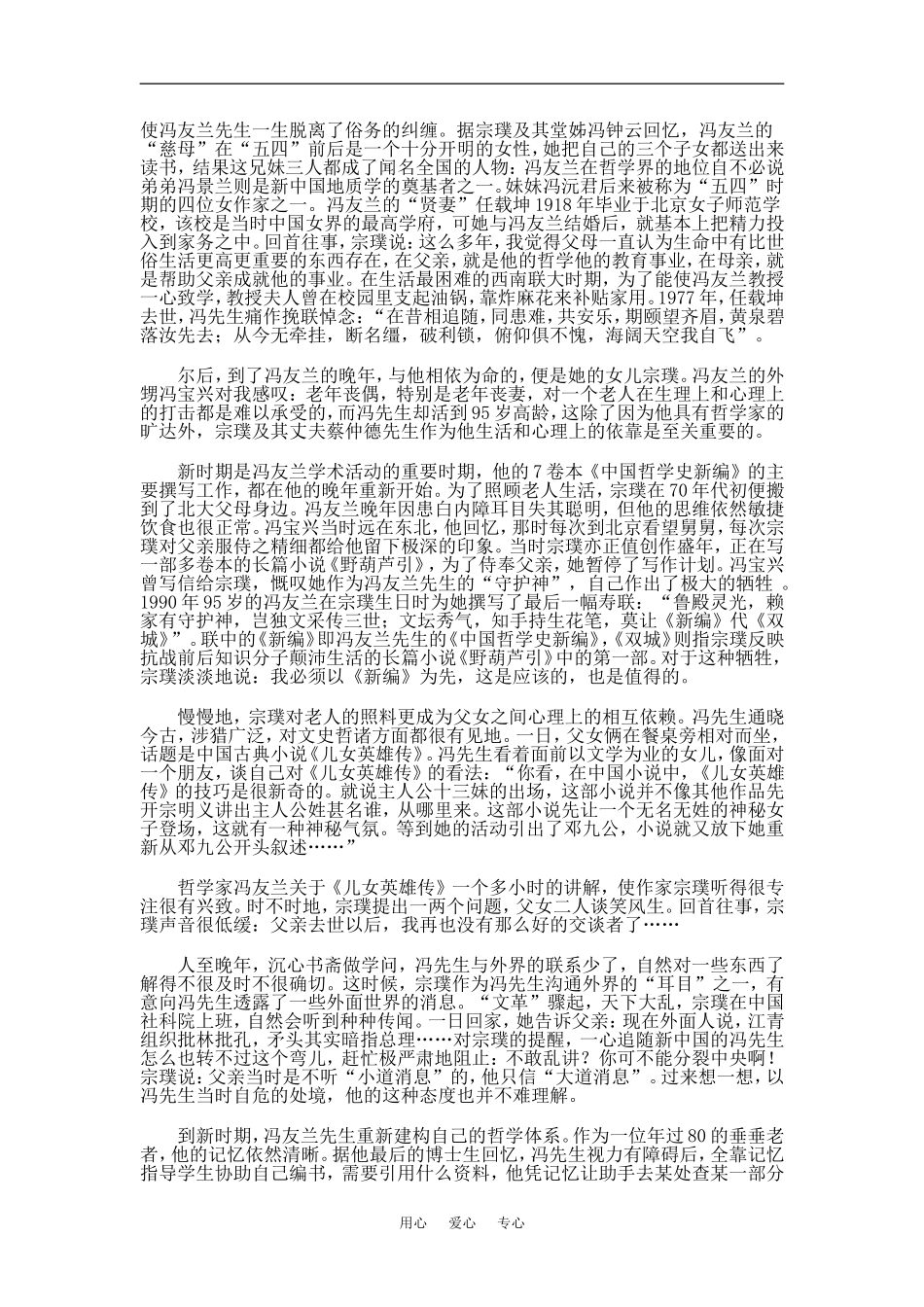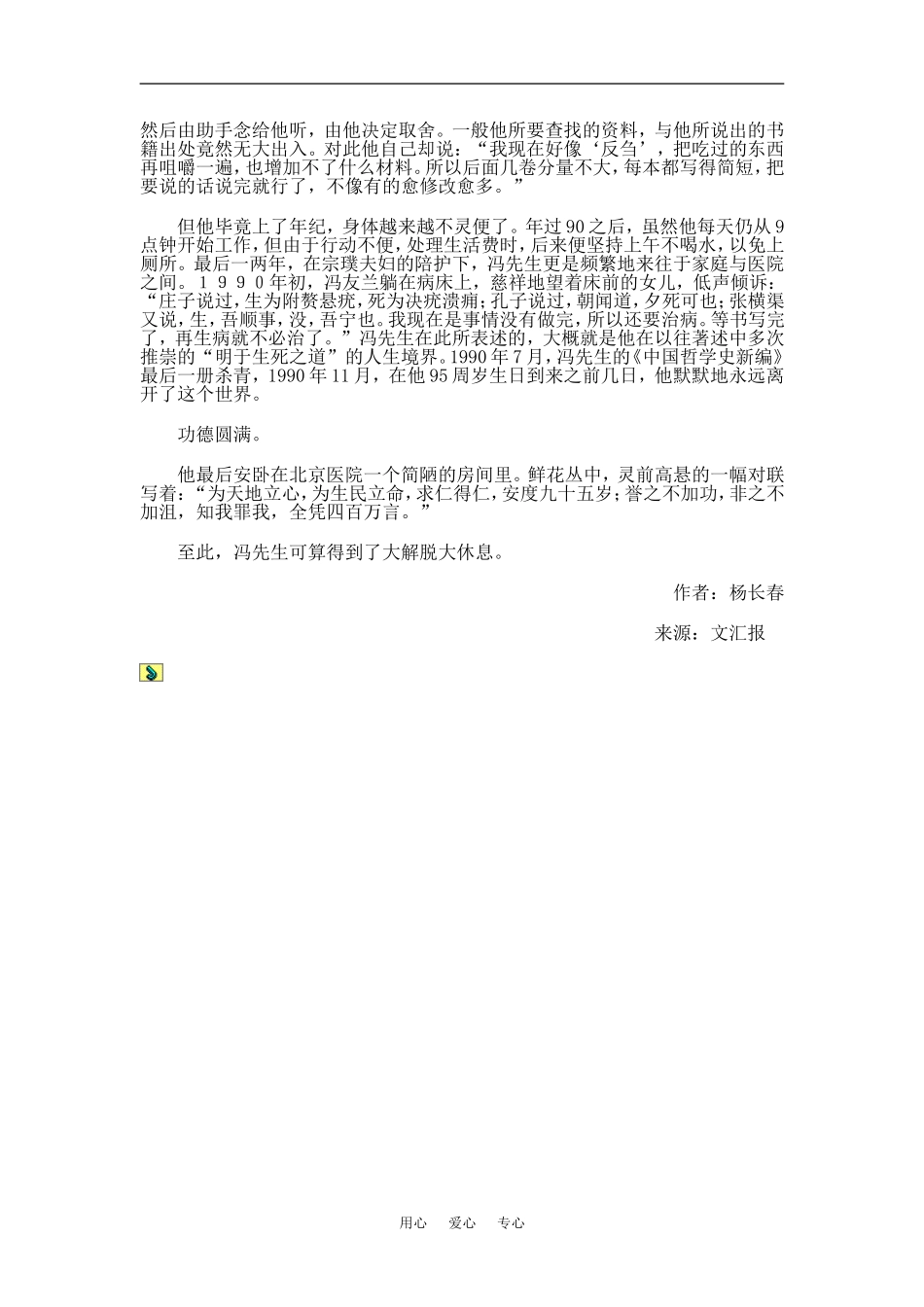俯仰不愧我自飞宗璞坐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客厅里,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父亲冯友兰留给她的印象时,面部表情不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怀念,看得出,这是一种温暖的依恋。“尚未上学,也就是五六岁吧,”宗璞回忆,极像自语,目光淡远。那时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当教授、文学院长。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先生。因为寓所邻近,两家过从甚密,宗璞和弟弟冯钟越以及梅校长的小女便常在一块嬉戏。小弟钟越同梅家小女谈笑甚欢,有意无意冷落了一旁的“小姐姐”。这不高兴被冯友兰看出来,平常不太过问家事的父亲便向宗璞招手:“你来你来!”宗璞来到父亲面前,父亲问了缘由,说:“我今天教你背一首诗。”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冯友兰一边教一边解释: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说,从别人身上,自己应该学习领悟一些东西。深奥的道理被父亲讲得很浅显很明晰,而同时深深吸引她的,还有父亲那抑扬顿挫的朗诵声,这声音激发了宗璞对古诗词的强烈兴趣。到上小学,宗璞已养成了一个极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上学离家时,先背书包来到父母床前,把刚刚学会的诗句对着父母再背一遍。以后姐姐如此,兄弟也如此,家中不自觉地就形成了那么一种气氛。这气氛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影响。宗璞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家都在北京,逢到开饭,长幼围餐桌而坐,冯友兰先生也从纷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夫人做出的可口饭菜,一边有声有色的讲述着时政文化历史哲学。所以,从餐桌旁孩子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营养宗璞留恋地说:那些内容,那种形式,想想似乎可以称作是“餐桌教育”。宗璞说,父亲在家里更注重“言传身教”,我们小的时候,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他在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他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他对子女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事业的执著。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便去跑滇缅公路,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下海”做生意,情况与现在很有些相似。冯先生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这首先得力于他夫人任载坤的扶持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1982年,冯友兰到母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宗璞陪同前往。在机场,87岁的冯友兰回首家事,曾颇有感慨地作打油诗一首: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年又得儿女孝,扶我云天万里飞。诗中提到的三个女性用心爱心专心使冯友兰先生一生脱离了俗务的纠缠。据宗璞及其堂姊冯钟云回忆,冯友兰的“慈母”在“五四”前后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女性,她把自己的三个子女都送出来读书,结果这兄妹三人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