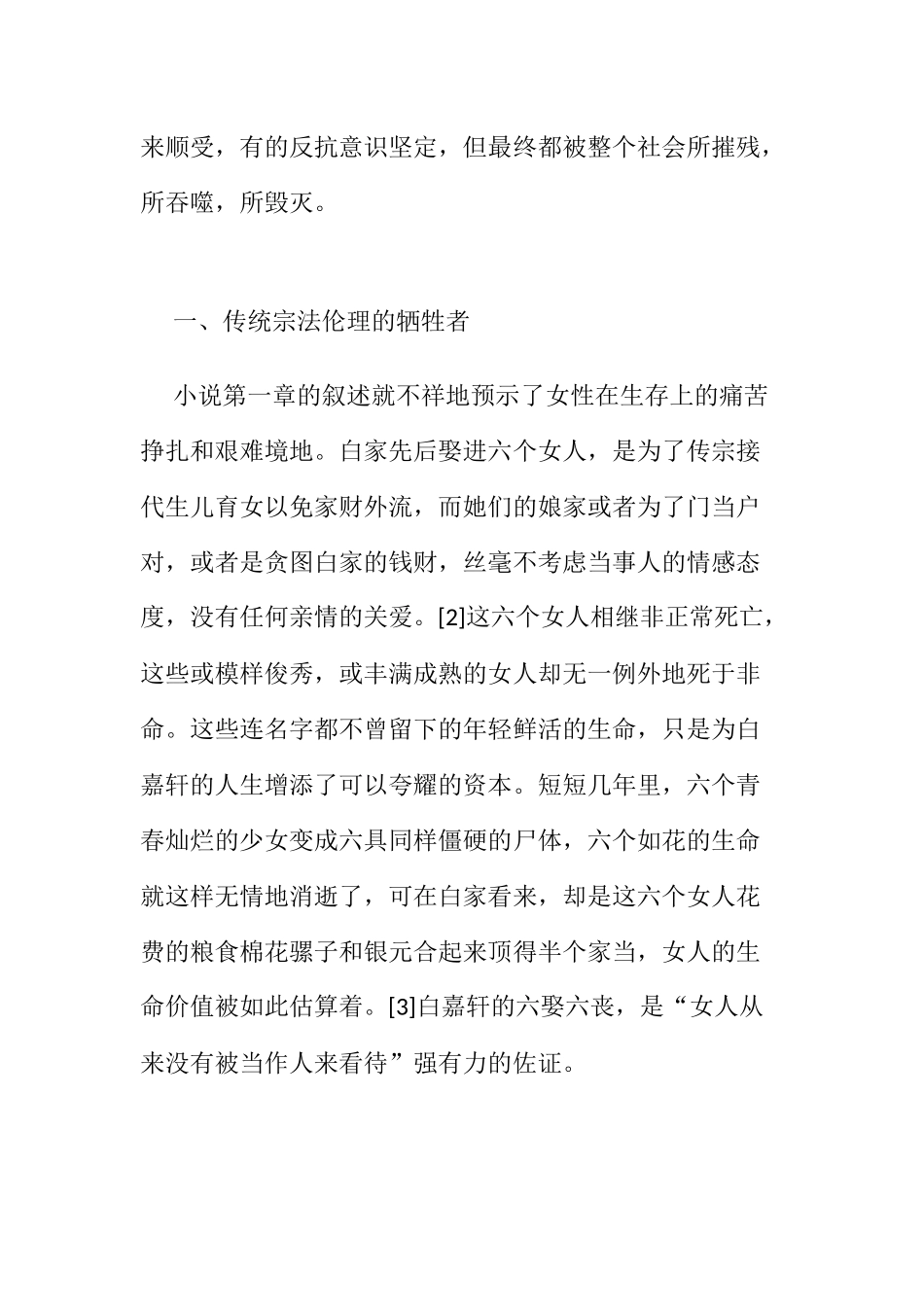摘要: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的成为宗法伦理的牺牲品,有的与宗法伦理进行对抗,有的则沦为宗法伦理的践行者,封建宗法制度是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道德礼教,婢妾制度,僵硬的伦理等像重重枷锁桎梏着她们的身心,使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倍受压迫和折磨,从而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关键词:《白鹿原》;宗法伦理;女性;悲剧命运“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开篇这句话,拥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魔法人物、情节、时间的重新整合,在简短的概括中充满张力像是浩瀚的海洋连通陆地的小塘清水,读者借此游入,渐渐地,陈忠实那汪洋恣肆的语言海洋,尽收观光者眼底。在《白鹿原》这篇巨作中,陈忠实不再束手束脚,他终于放开胆子,向诸多他所怀疑的、所欲打破的旧物发起进攻。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首先要敢于书写善与恶、好与坏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一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司汤达的《红与黑》;同时,他要不被任何标榜崇高的符号束缚,要将一个个人还原为“人”,无论是母亲、父亲革命家、道士、军人、小偷,首先,他们都是生而为人;再者,他要敢于动用自己所有可挖掘的生活经验,并将其提炼入自己的文学王国。《白鹿原》体现了陈忠实作为优秀小说家的这三个特质。但《白鹿原》不单纯拘泥于家族史诗小说,曾有人戏谑过王全安版的《白鹿原》是《田小娥传》。这不能怪罪于王全安的理解有误,而是陈忠实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给女性赋予了太多不同的色彩,多到人们自然的认为陈忠实对女性形象是充满了崇拜。虽然作为一个男性作家,陈忠实写作过程中难免带有男性色彩,但有时反而他男性视角下塑造的女性既兼具了女性美又充满了悲剧美。《白鹿原》塑造了生活在男权文化下面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无论是白嘉轩周围的女子,还是小娥,鹿冷氏,小翠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她们要么是传宗接代供男人渲泄的工具,要么是家族争斗的牺牲品,要么是革命内部左倾思潮的受害对象,要么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有的逆来顺受,有的反抗意识坚定,但最终都被整个社会所摧残,所吞噬,所毁灭。一、传统宗法伦理的牺牲者小说第一章的叙述就不祥地预示了女性在生存上的痛苦挣扎和艰难境地。白家先后娶进六个女人,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以免家财外流,而她们的娘家或者为了门当户对,或者是贪图白家的钱财,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情感态度,没有任何亲情的关爱。[2]这六个女人相继非正常死亡,这些或模样俊秀,或丰满成熟的女人却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这些连名字都不曾留下的年轻鲜活的生命,只是为白嘉轩的人生增添了可以夸耀的资本。短短几年里,六个青春灿烂的少女变成六具同样僵硬的尸体,六个如花的生命就这样无情地消逝了,可在白家看来,却是这六个女人花费的粮食棉花骡子和银元合起来顶得半个家当,女人的生命价值被如此估算着。[3]白嘉轩的六娶六丧,是“女人从来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强有力的佐证。鹿家大儿媳,原上名医冷先生的大女儿,她的婚姻只不过是冷先生为了在白鹿原站稳脚跟的一个筹码,对丈夫的所有印象只有公公的三个巴掌打出来的新婚之夜。婚后一年,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在鹿家于极度的失望和令人恐惧的猜测中度日,她的内心是无比孤寂、痛苦的。常年的守活寡使她心灰意冷,偶尔来到娘家,想寻求一丝安慰,得到的却是冷先生冷着脸的训诫,她一脸忧郁,却什么也不敢说。她渴望过正常人的有情爱的生活,但她不幸而生于那个时代,在封建婚姻、伦理道德的重重束缚下,女性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被野蛮剥夺。在无望的等待中,公公的一次酒后失德令她昏暗的天空透出些许亮色,以封建伦理道德的礼教规范自己的她慌乱无措,陷于理与欲的矛盾挣扎却不免心存渴望,但鹿子霖用一撮麦草羞辱得她无地自容,灵魂出窍,“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同时她的幻想也被彻底粉碎,生存意识被彻底摧毁,原本脆弱的神经在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后终于崩溃,得了淫疯病。她的公公将她囚禁,思谋着如何摆脱自己的嫌疑;她的父亲冷先生果然冷得了得,根本不追问女儿发疯的原因,在他看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