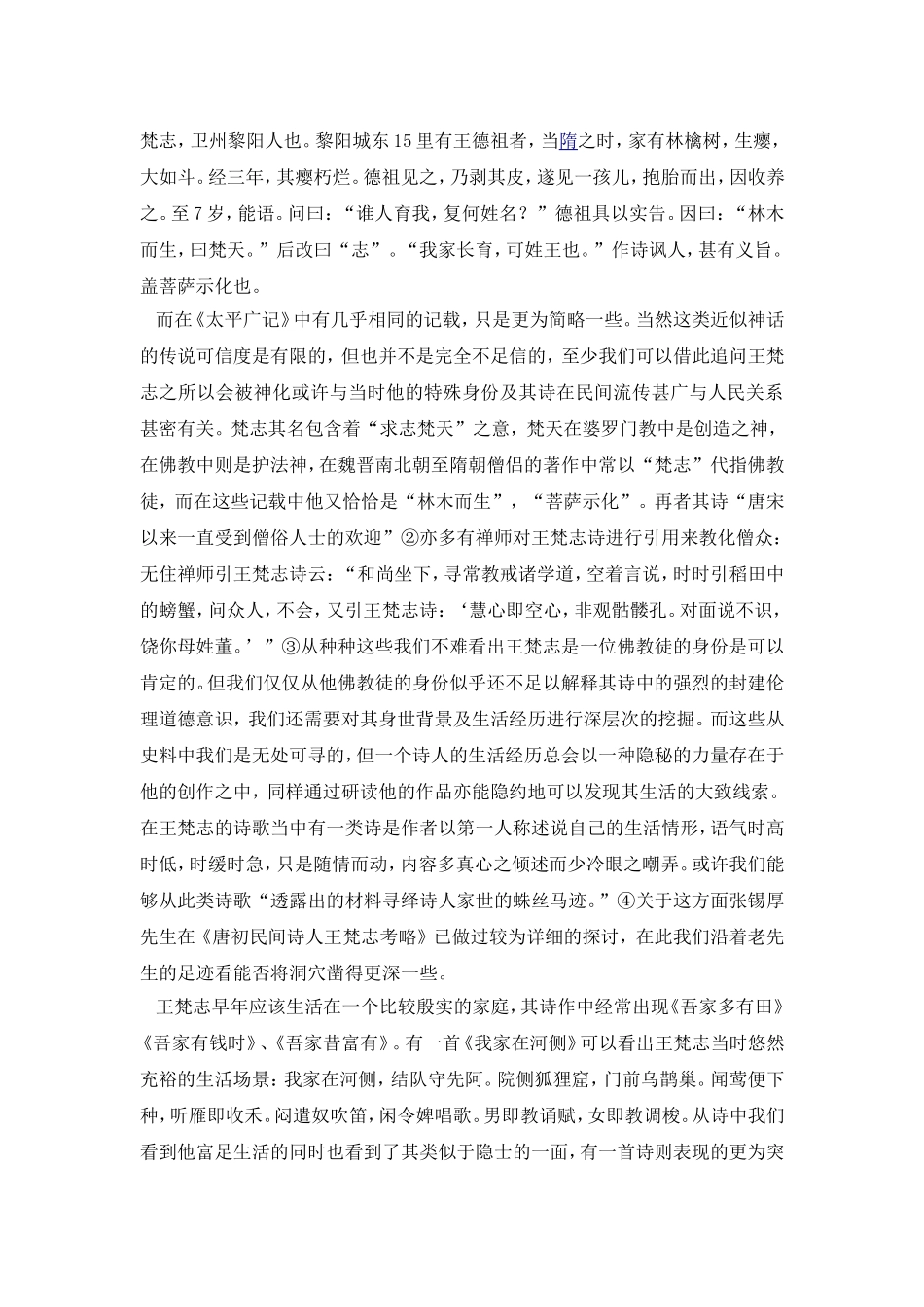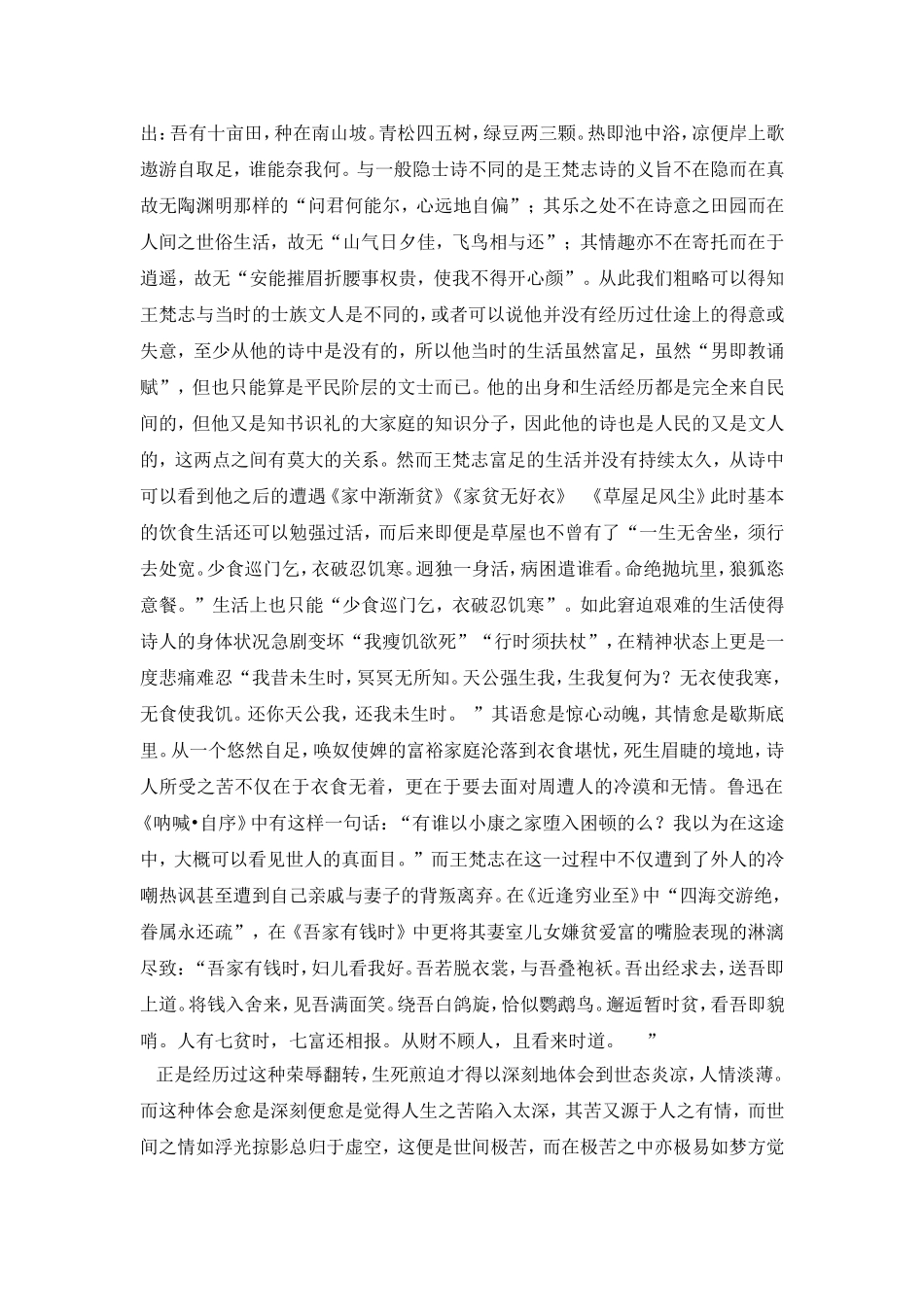论王梵志诗中的苦与空【摘要】:王梵志诗的驯世倾向在学术界获得一致认同,但就其驯世背后所循之义理,所达之旨意,是佛法抑或封建伦理道德,学者们之间存在很大争议。笔者主要从诗人是佛教徒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其独特的经历入手,然后从诗的内容上发现主要有两大主题即:苦于空。其说人生之苦并不在“刺世明道”而实在归空。最后从及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演变,也即是与儒家思想相互斗争相互融合来进一步解释王梵志诗中为什么出现很多关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现象,得出封建伦理道德亦是他宣扬佛法苦空的一件外衣而已。【关键词】:王梵志驯世倾向义旨苦空佛教的传播文学史往往又是一部文学发现史,其中不免有一些奇异的贝壳被遗忘在历史的沙滩上,然而岁月的潮汐又总会宿命般地将其再次推向岸边。王梵志无疑便是如此,自20世纪初敦煌石室之门打开,王梵志的诗集手稿得以重见天日,便在顷刻间备受关注。而当人们回头向历史中去寻找的时候才发现,这位作品在当时广为流传并影响西部边陲的人物仅仅只在一些野史丛谈及几个宋人笔记里出现过,《全唐诗》里也竟无其一言半字。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在唐宋时期如此被推崇,并在民间造成的无与伦比的影响,以至于其人都被民众所神化。关于其诗一直被学者们认为“王梵志那样的诗和通念上的唐诗很难相称,是一个特异的存在。”①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其语言的“俗”与“辣”,更在于其思想的驳杂,甚至有些地方看上去是不可调和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矛盾便是王梵志在驯世的过程中依据的是佛法之“无我苦空”、“因缘祸福”,而其内容又多涉及封建伦理道德中的“忠、孝、仁、义、礼、智、信”以及“刺世明道”。故此便有人认为其诗中所引佛法只是手段并非目的,甚至进而将他与传统文士的“忧患世道”、“为民而歌”相提并论。然若仔细研读其诗便可发现是有失偏颇的,至少对诗人的特殊身份有些忽略,对其诗的内质缺乏更深刻的解读,还有对佛教在隋唐时期的传播演变情况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本文便从以上诸方面对王梵志诗的思想宗旨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一)王梵志其人关于王梵志的身世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所供我们翻阅查找的文献资料甚少而又多见于野史丛谈,内容显得荒诞不经。冯翊《桂苑丛谈。史遗》中记载: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15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剥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7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而在《太平广记》中有几乎相同的记载,只是更为简略一些。当然这类近似神话的传说可信度是有限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足信的,至少我们可以借此追问王梵志之所以会被神化或许与当时他的特殊身份及其诗在民间流传甚广与人民关系甚密有关。梵志其名包含着“求志梵天”之意,梵天在婆罗门教中是创造之神,在佛教中则是护法神,在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僧侣的著作中常以“梵志”代指佛教徒,而在这些记载中他又恰恰是“林木而生”,“菩萨示化”。再者其诗“唐宋以来一直受到僧俗人士的欢迎”②亦多有禅师对王梵志诗进行引用来教化僧众:无住禅师引王梵志诗云:“和尚坐下,寻常教戒诸学道,空着言说,时时引稻田中的螃蟹,问众人,不会,又引王梵志诗:‘慧心即空心,非观骷髅孔。对面说不识,饶你母姓董。’”③从种种这些我们不难看出王梵志是一位佛教徒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但我们仅仅从他佛教徒的身份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其诗中的强烈的封建伦理道德意识,我们还需要对其身世背景及生活经历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而这些从史料中我们是无处可寻的,但一个诗人的生活经历总会以一种隐秘的力量存在于他的创作之中,同样通过研读他的作品亦能隐约地可以发现其生活的大致线索。在王梵志的诗歌当中有一类诗是作者以第一人称述说自己的生活情形,语气时高时低,时缓时急,只是随情而动,内容多真心之倾述而少冷眼之嘲弄。或许我们能够从此类诗歌“透露出的材料寻绎诗人家世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