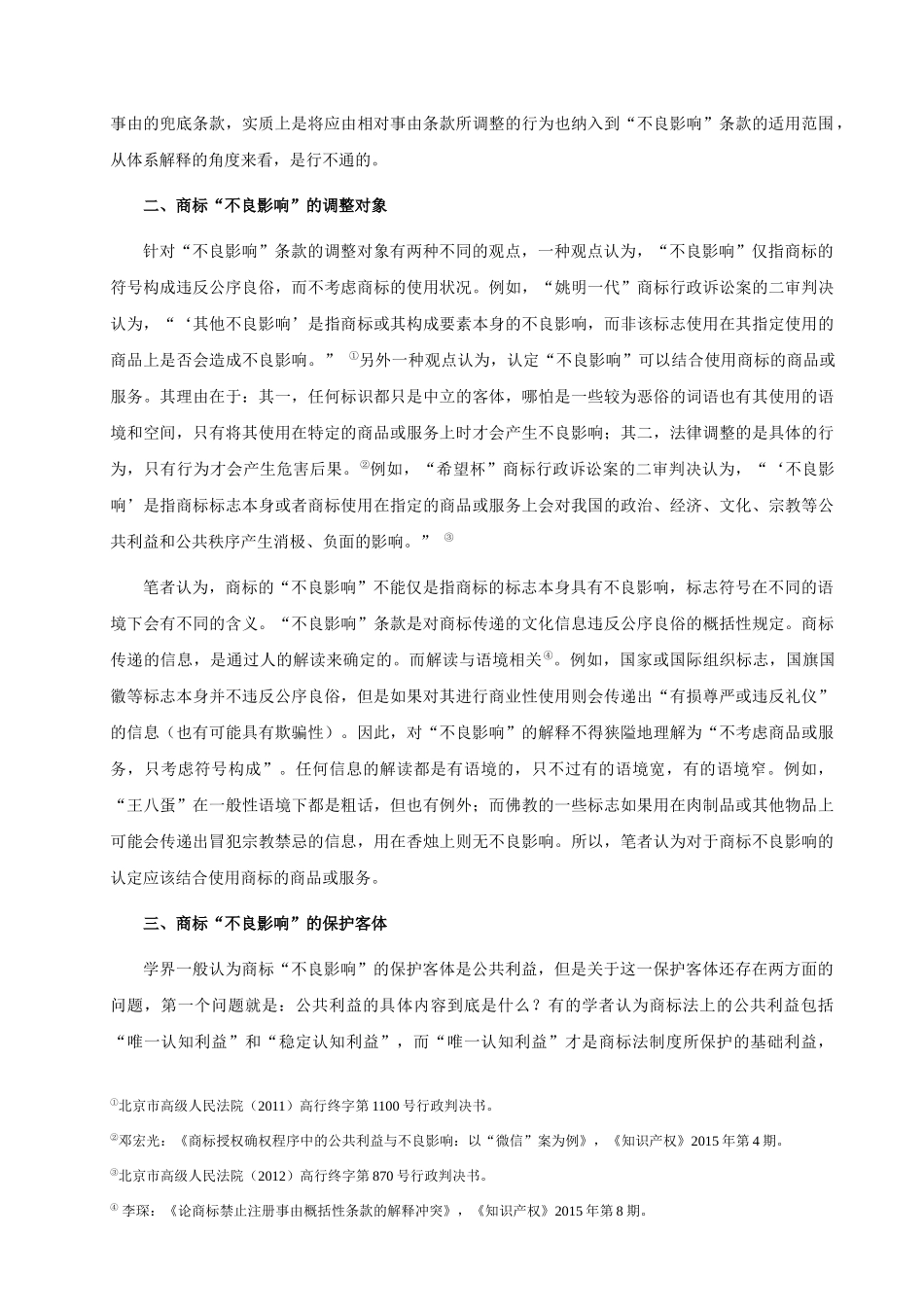关于论商标“不良影响”之认定的文献综述2015年“微信”商标案的一审判决,援引“不良影响”条款,认为创博亚太公司在先申请的“微信”商标具有《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规定的“不良影响”因此不能被核准注册。①上述判决引发了人们对于“不良影响”条款的激烈讨论,对此判决,很多学者认为不应当适用“不良影响”条款禁止“微信”商标的核准注册。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本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商标“不良影响”的认定是一个在实践中比较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商标不良影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论文34篇,其中杂志论文27篇,硕士论文7篇。另外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共收集到相关裁判文书7篇,兹将研究文献综述如下:一、“不良影响”条款性质的研究“不良影响”条款的定位是关于“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的兜底条款还是第10条第1款第(8)项中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并列、与其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学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②: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单纯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兜底条款,专门针对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相类似的情形。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的兜底条款,对于类似于第10条第1款中规定的禁用标识,而其他款项无法适用时,可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行不通的,如果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的兜底条款,那么应当单独设立第(9)项来规定“不良影响”条款,而非将其规定在第(8)项之中。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不予注册或使用的绝对事由的兜底条款,只要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害了公共利益,并且在其他的绝对事由条款均无法适用时,可适用“不良影响”条款。对于这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这样定位将会导致商标不良影响的范围就过于宽泛,绝对事由应当是对商标选择、使用、注册的限制和例外,虽然每个条款的规定均会设有一定的弹性和裁量空间,但适用的范围不宜过宽,也不能过于不确定。第四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是商标不予注册或使用的所有事由的兜底条款,在其他条款均无法适用的情况下,即可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有的学者从从条文框架上进行反驳,“不良影响”条款应当属于商标禁止注册或使用的绝对事由的范畴,这种观点将其当作不予注册或使用的所有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1538号行政判决书。②周云川著:《商标授权确权诉讼:规则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事由的兜底条款,实质上是将应由相对事由条款所调整的行为也纳入到“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范围,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是行不通的。二、商标“不良影响”的调整对象针对“不良影响”条款的调整对象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良影响”仅指商标的符号构成违反公序良俗,而不考虑商标的使用状况。例如,“姚明一代”商标行政诉讼案的二审判决认为,“‘其他不良影响’是指商标或其构成要素本身的不良影响,而非该标志使用在其指定使用的商品上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①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认定“不良影响”可以结合使用商标的商品或服务。其理由在于:其一,任何标识都只是中立的客体,哪怕是一些较为恶俗的词语也有其使用的语境和空间,只有将其使用在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上时才会产生不良影响;其二,法律调整的是具体的行为,只有行为才会产生危害后果。②例如,“希望杯”商标行政诉讼案的二审判决认为,“‘不良影响’是指商标标志本身或者商标使用在指定的商品或服务上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③笔者认为,商标的“不良影响”不能仅是指商标的标志本身具有不良影响,标志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含义。“不良影响”条款是对商标传递的文化信息违反公序良俗的概括性规定。商标传递的信息,是通过人的解读来确定的。而解读与语境相关④。例如,国家或国际组织标志,国旗国徽等标志本身并不违反公序良俗,但是如果对其进行商业性使用则会传递出“有损尊严或违反礼仪”的信息(也有可能具有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