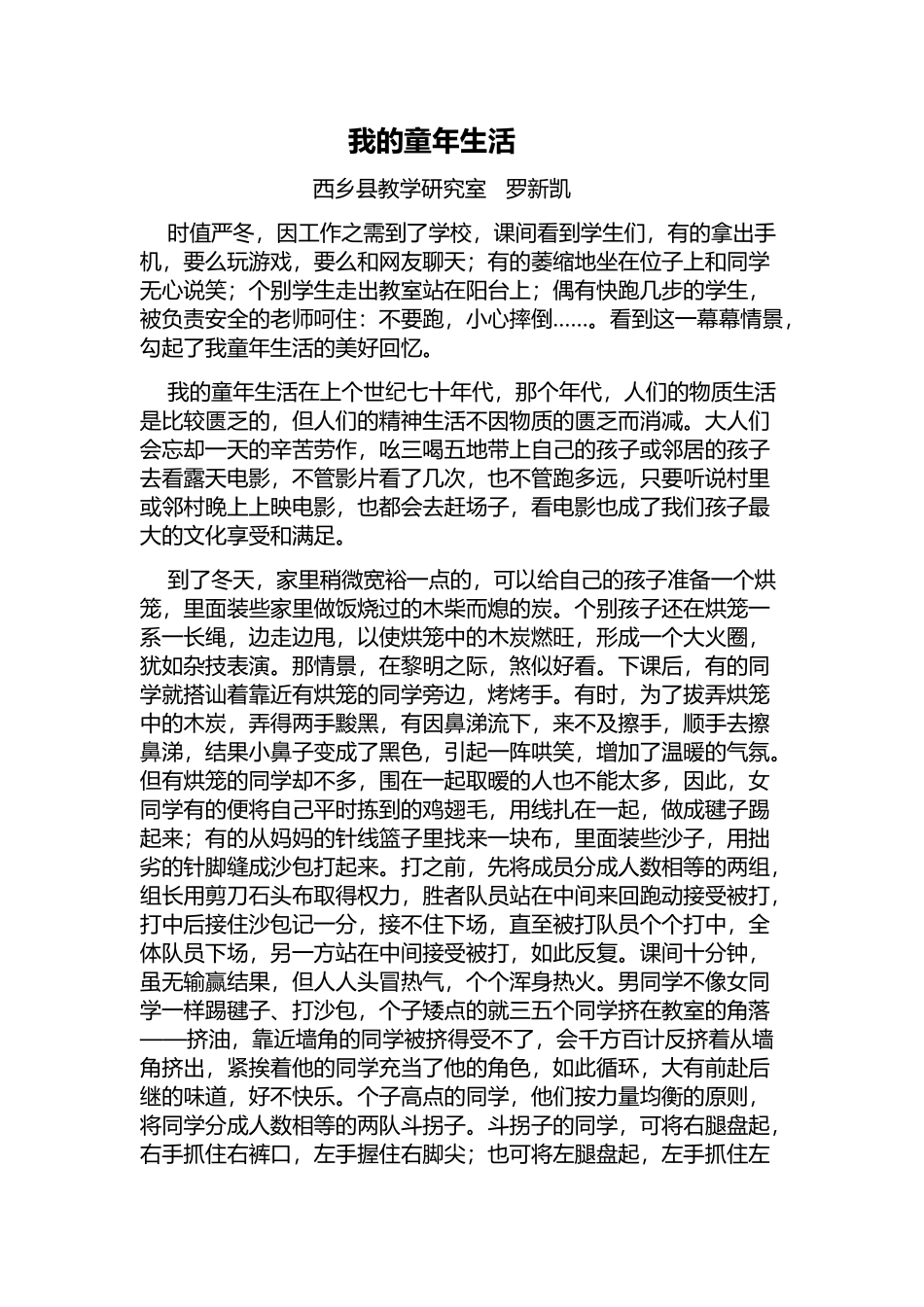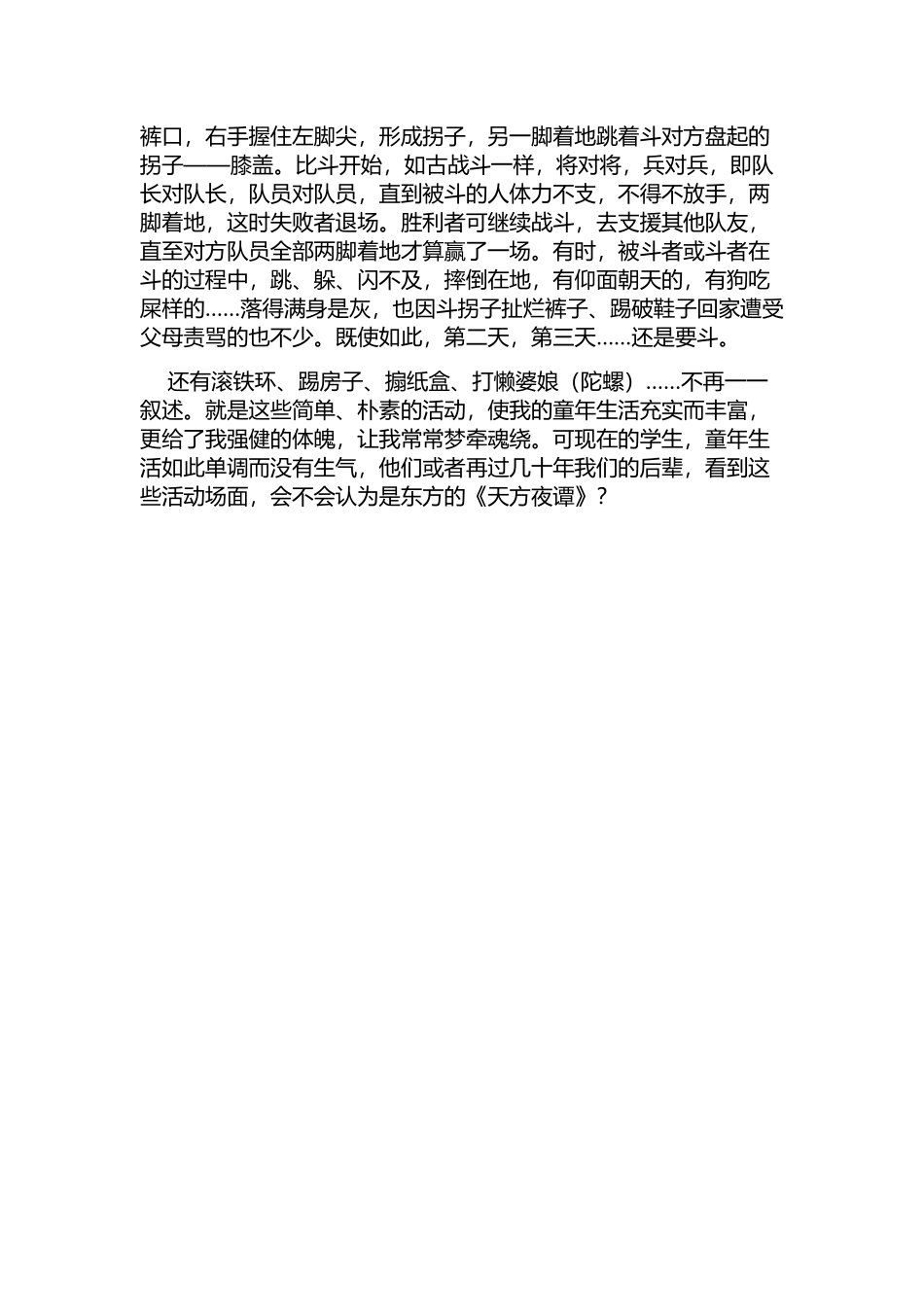我的童年生活西乡县教学研究室罗新凯时值严冬,因工作之需到了学校,课间看到学生们,有的拿出手机,要么玩游戏,要么和网友聊天;有的萎缩地坐在位子上和同学无心说笑;个别学生走出教室站在阳台上;偶有快跑几步的学生,被负责安全的老师呵住:不要跑,小心摔倒……。看到这一幕幕情景,勾起了我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我的童年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是比较匮乏的,但人们的精神生活不因物质的匮乏而消减。大人们会忘却一天的辛苦劳作,吆三喝五地带上自己的孩子或邻居的孩子去看露天电影,不管影片看了几次,也不管跑多远,只要听说村里或邻村晚上上映电影,也都会去赶场子,看电影也成了我们孩子最大的文化享受和满足。到了冬天,家里稍微宽裕一点的,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一个烘笼,里面装些家里做饭烧过的木柴而熄的炭。个别孩子还在烘笼一系一长绳,边走边甩,以使烘笼中的木炭燃旺,形成一个大火圈,犹如杂技表演。那情景,在黎明之际,煞似好看。下课后,有的同学就搭讪着靠近有烘笼的同学旁边,烤烤手。有时,为了拔弄烘笼中的木炭,弄得两手黢黑,有因鼻涕流下,来不及擦手,顺手去擦鼻涕,结果小鼻子变成了黑色,引起一阵哄笑,增加了温暖的气氛。但有烘笼的同学却不多,围在一起取暧的人也不能太多,因此,女同学有的便将自己平时拣到的鸡翅毛,用线扎在一起,做成毽子踢起来;有的从妈妈的针线篮子里找来一块布,里面装些沙子,用拙劣的针脚缝成沙包打起来。打之前,先将成员分成人数相等的两组,组长用剪刀石头布取得权力,胜者队员站在中间来回跑动接受被打,打中后接住沙包记一分,接不住下场,直至被打队员个个打中,全体队员下场,另一方站在中间接受被打,如此反复。课间十分钟,虽无输赢结果,但人人头冒热气,个个浑身热火。男同学不像女同学一样踢毽子、打沙包,个子矮点的就三五个同学挤在教室的角落——挤油,靠近墙角的同学被挤得受不了,会千方百计反挤着从墙角挤出,紧挨着他的同学充当了他的角色,如此循环,大有前赴后继的味道,好不快乐。个子高点的同学,他们按力量均衡的原则,将同学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斗拐子。斗拐子的同学,可将右腿盘起,右手抓住右裤口,左手握住右脚尖;也可将左腿盘起,左手抓住左裤口,右手握住左脚尖,形成拐子,另一脚着地跳着斗对方盘起的拐子——膝盖。比斗开始,如古战斗一样,将对将,兵对兵,即队长对队长,队员对队员,直到被斗的人体力不支,不得不放手,两脚着地,这时失败者退场。胜利者可继续战斗,去支援其他队友,直至对方队员全部两脚着地才算赢了一场。有时,被斗者或斗者在斗的过程中,跳、躲、闪不及,摔倒在地,有仰面朝天的,有狗吃屎样的……落得满身是灰,也因斗拐子扯烂裤子、踢破鞋子回家遭受父母责骂的也不少。既使如此,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要斗。还有滚铁环、踢房子、搧纸盒、打懒婆娘(陀螺)……不再一一叙述。就是这些简单、朴素的活动,使我的童年生活充实而丰富,更给了我强健的体魄,让我常常梦牵魂绕。可现在的学生,童年生活如此单调而没有生气,他们或者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辈,看到这些活动场面,会不会认为是东方的《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