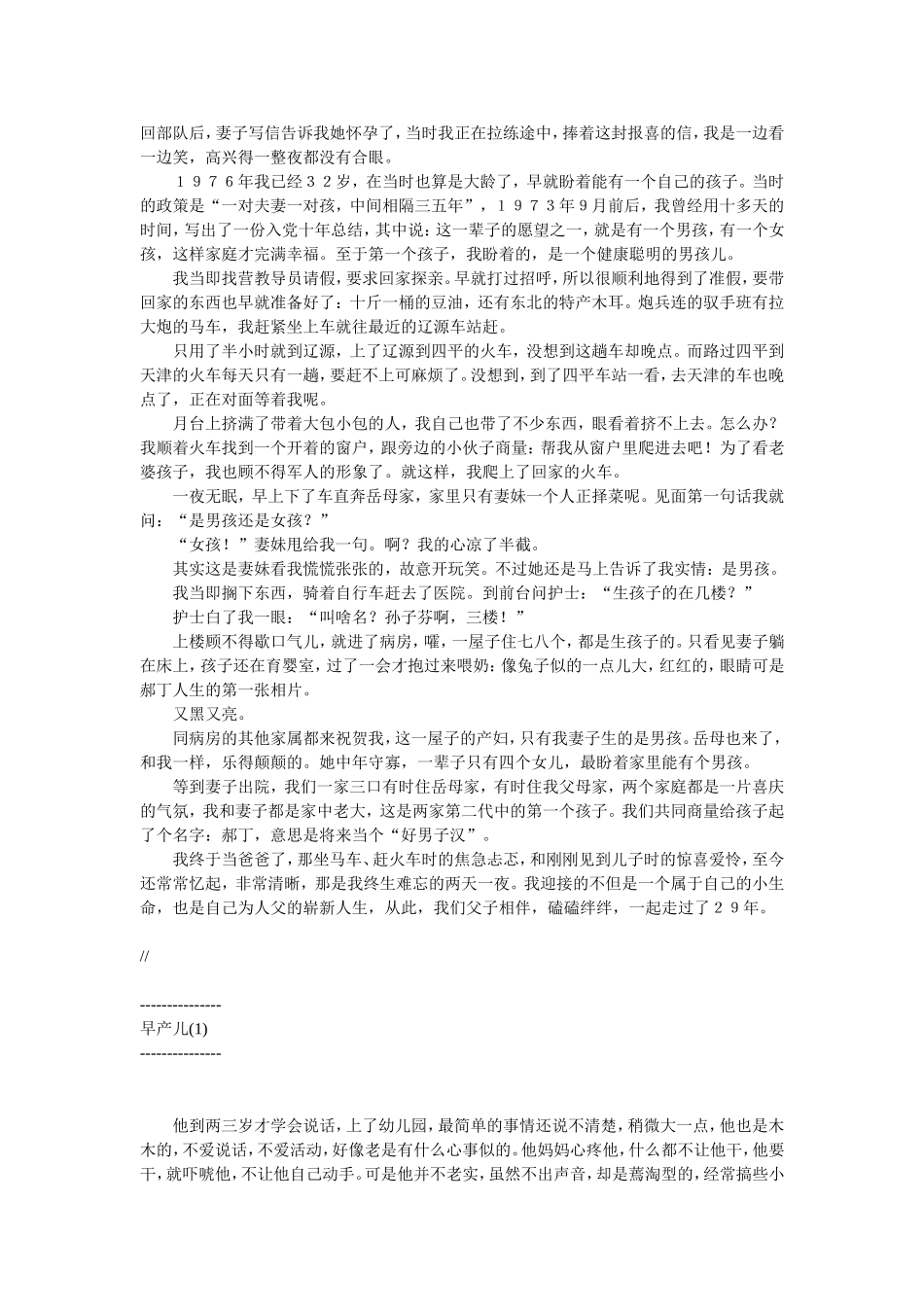《父子协议》****************第一章协议的由来***************我终于当爸爸了,那坐马车、赶火车时的焦急忐忑,和刚刚见到儿子时的惊喜爱怜,至今还常常忆起,非常清晰,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一夜。我迎接的不但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命,也是自己为人父的崭新人生,从此,我们父子相伴,磕磕绊绊,一起走过了29年。---------------引子:一份沉甸甸的协议---------------我,郝麦收,在儿子极不争气的20岁年龄,为了让他走向自立,被迫无奈与他签订了白纸黑字的“亲子双向自立协议”——郝丁承担的责任: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费用;自力谋业,自己创业;自力结婚成家;自己培育子女。郝麦收、孙子芬承担的责任: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签约议人:父代:郝麦收孙子芬子代:郝丁签协议时间:1996年9月18日从此,我家不再拥有安宁。我的家庭,本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在我55岁之前,从没想过我家的故事竟引起那么多媒体的关注,引起那么多争议,而直到我过了花甲之年,才下决心把这些故事写成书。我家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三口人组成稳定的等边结构——我,人称“郝教授”,父亲和丈夫,1944年生,18岁参军,1986年转业,曾在沈阳军区现代管理学院任正团级教员,转业后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专攻老年问题研究,并创办天津市老年婚姻研究所、天津市老年再婚见证处和天津市麦收婚姻介绍所,2004年退休,仍担任天津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我的妻子孙子芬:1949年生,长期从事企业政工工作,曾担任天津某工厂党支部书记,1997年退休,现负责麦收婚姻介绍所的日常事务。我的儿子郝丁:1976年生于天津,1996年中专毕业后被我逼向社会,几经磨难与波折后,由一个“不爱惜东西”、“动手能力差”、“没有自制力”、“不负责任”、“不知深浅,胡作非为”的独生子,变成了一个“可以战胜苦难,享受苦难”,敢说自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最棒”的成熟青年。表面看来,我家的角色分工和定位是清晰而传统的:我是家中的顶梁柱和决策人,在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在内是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对妻儿尽管心有柔情,却很少流露;我的妻子则是勤快、贤惠、慈祥的母亲,擅长理家,对丈夫心甘情愿地辅佐,对儿子无微不至地关心;而儿子郝丁呢,则是一个在城市家庭里长大的普通青年,性格温和,略显内向,现在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有一个甜蜜的女友,正准备结婚成家。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9年前发生的一场地震,却把我家的每个人都抛出了原有的位置,并且几乎是彻底地改变了我家的内部关系,父亲和儿子、父亲和母亲、母亲和儿子,这等边三角形的每一边都遭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而地震的震源,就在由我所发起的一场亲子革命的实验,即开头出现的“亲子双向自立协议”,虽然是一张白纸黑字的纸,但在我们三个人心中却仿佛有千斤重。从那时到现在,表面上的震动仍然时有发生,而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波澜更是几乎从来没有消失过,每个人都总是在围绕着这个协议,思考、行动和评估。到现在,仿佛暂时尘埃落定,但我们是否真的重建了自己的家庭,今后的生活是否能就此平稳?我仍然不敢肯定。甚至,我还预言,这份协议将继续左右我的家庭生活,直到郝丁走进中年,而我和妻子成为真正的老年人。尽管外界批评我“太残酷”、“不是一个好爸爸”、“拿自己的儿子当实验品”,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想看到一个自强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无能的小皇帝。虽然这个亲子革命实验只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却仍然具有足够的社会意义。现在,中国独生子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一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大难题是亲子比例的变革,当时就有一种感慨,千难万难,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生活中的难事变成了亲子制度的变革,千难万难,双向自立成了天下第一难,在亲子双向依赖文化的笼罩下,少数人高举契约文明的旗帜,左突右杀,终于为亲子双向自立打开了通道,也为国人开拓了视野,指明了方向。在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