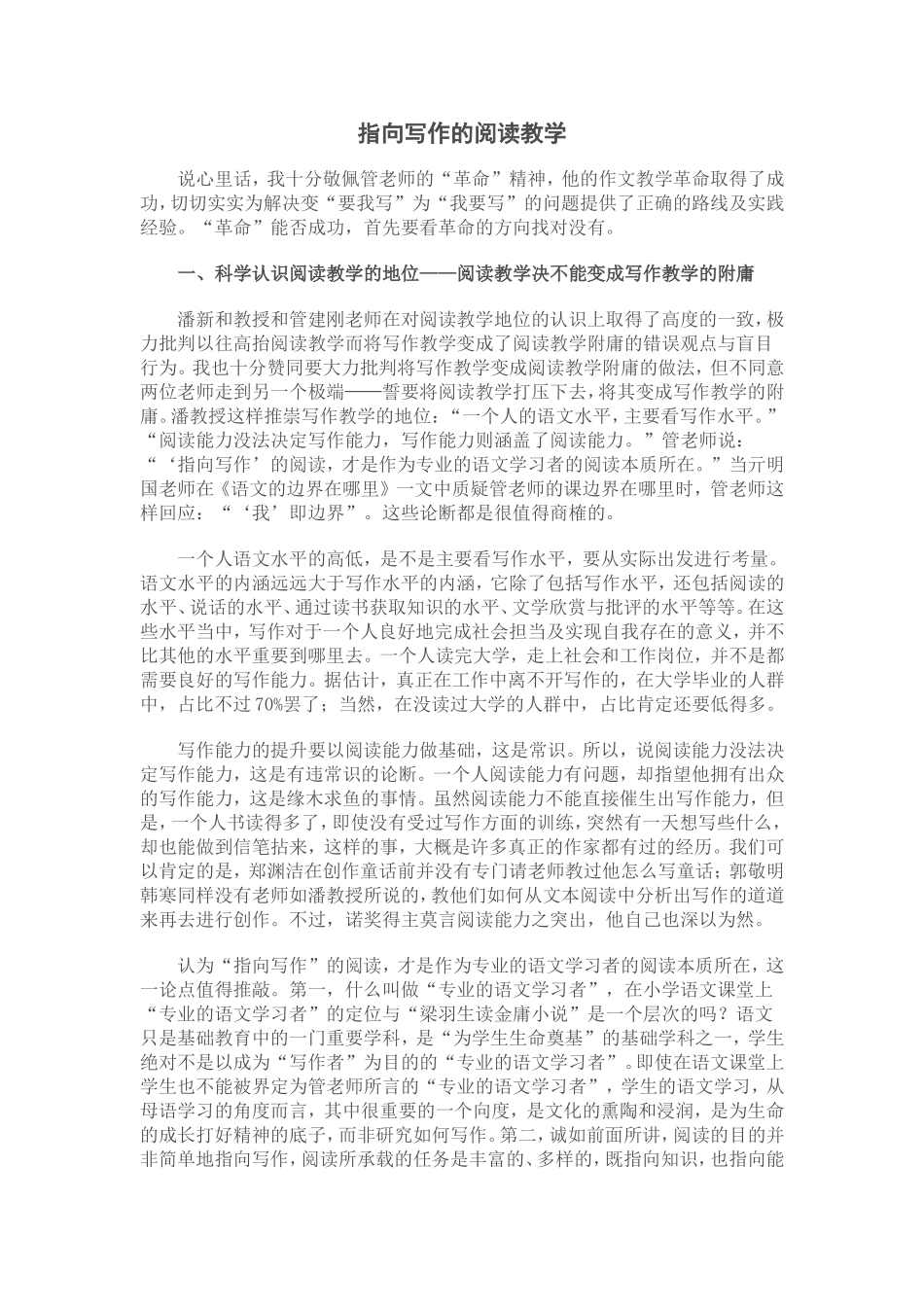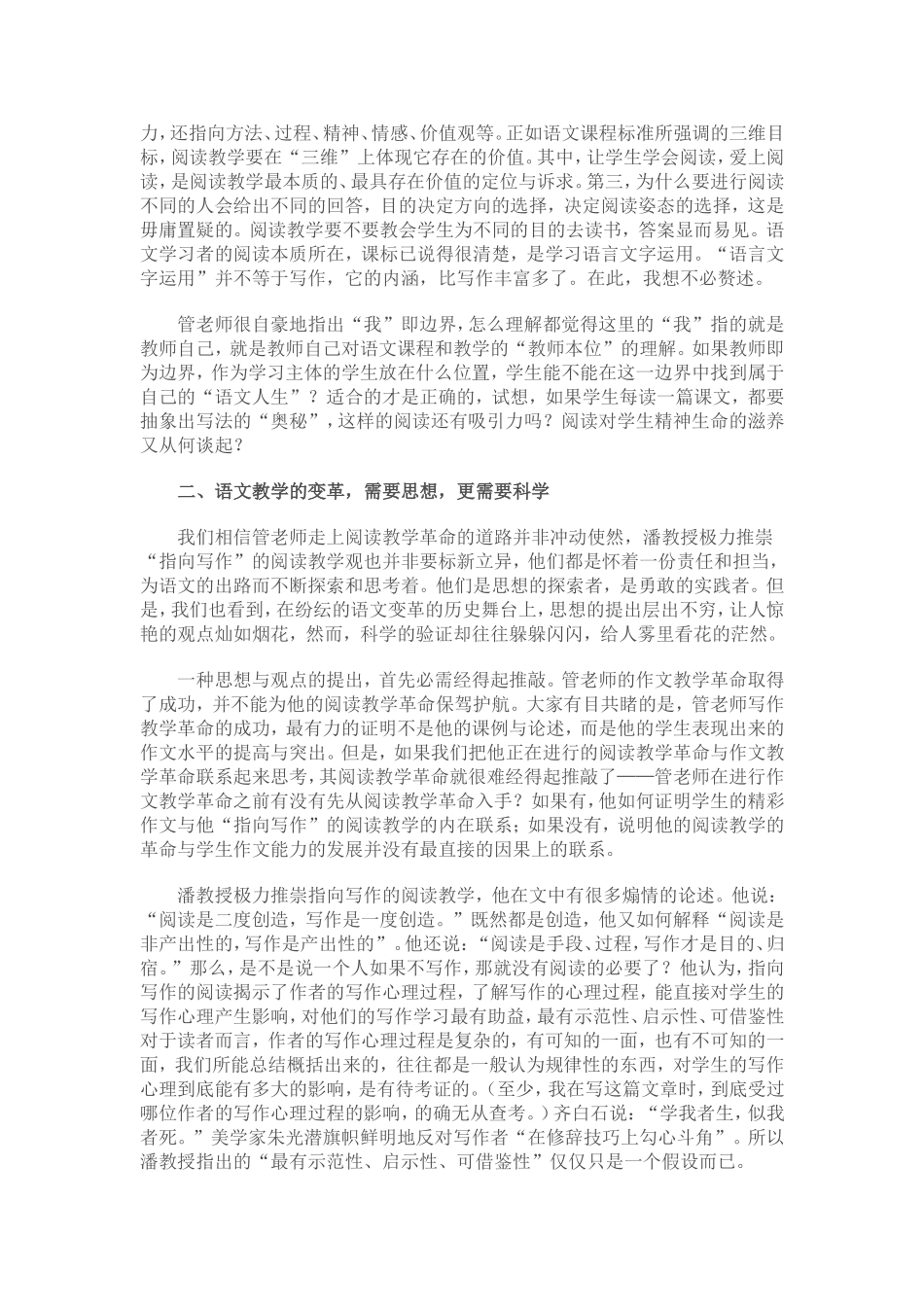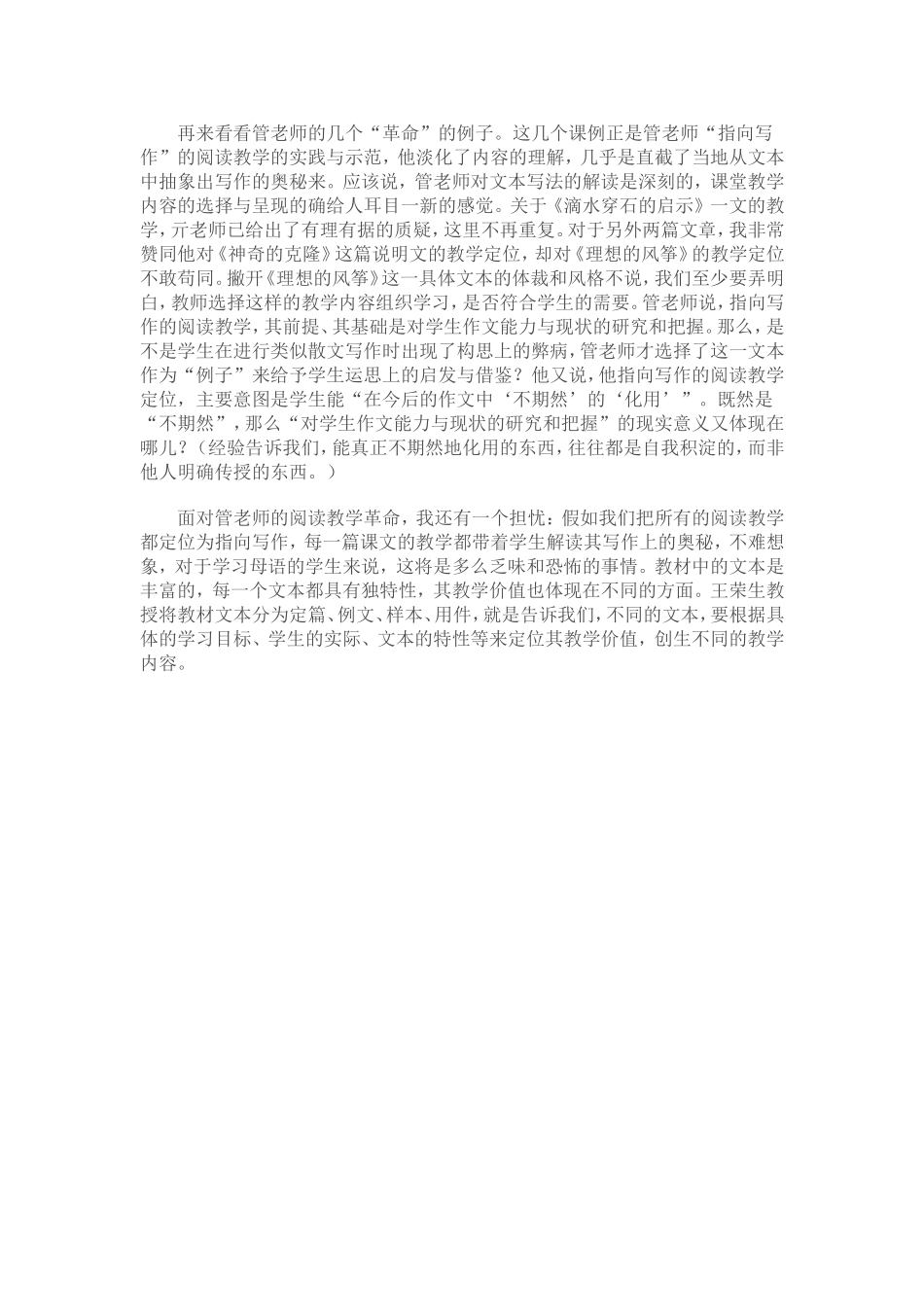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说心里话,我十分敬佩管老师的“革命”精神,他的作文教学革命取得了成功,切切实实为解决变“要我写”为“我要写”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路线及实践经验。“革命”能否成功,首先要看革命的方向找对没有。一、科学认识阅读教学的地位——阅读教学决不能变成写作教学的附庸潘新和教授和管建刚老师在对阅读教学地位的认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极力批判以往高抬阅读教学而将写作教学变成了阅读教学附庸的错误观点与盲目行为。我也十分赞同要大力批判将写作教学变成阅读教学附庸的做法,但不同意两位老师走到另一个极端——誓要将阅读教学打压下去,将其变成写作教学的附庸。潘教授这样推崇写作教学的地位:“一个人的语文水平,主要看写作水平。”“阅读能力没法决定写作能力,写作能力则涵盖了阅读能力。”管老师说:“‘指向写作’的阅读,才是作为专业的语文学习者的阅读本质所在。”当亓明国老师在《语文的边界在哪里》一文中质疑管老师的课边界在哪里时,管老师这样回应:“‘我’即边界”。这些论断都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是不是主要看写作水平,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考量。语文水平的内涵远远大于写作水平的内涵,它除了包括写作水平,还包括阅读的水平、说话的水平、通过读书获取知识的水平、文学欣赏与批评的水平等等。在这些水平当中,写作对于一个人良好地完成社会担当及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并不比其他的水平重要到哪里去。一个人读完大学,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并不是都需要良好的写作能力。据估计,真正在工作中离不开写作的,在大学毕业的人群中,占比不过70%罢了;当然,在没读过大学的人群中,占比肯定还要低得多。写作能力的提升要以阅读能力做基础,这是常识。所以,说阅读能力没法决定写作能力,这是有违常识的论断。一个人阅读能力有问题,却指望他拥有出众的写作能力,这是缘木求鱼的事情。虽然阅读能力不能直接催生出写作能力,但是,一个人书读得多了,即使没有受过写作方面的训练,突然有一天想写些什么,却也能做到信笔拈来,这样的事,大概是许多真正的作家都有过的经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郑渊洁在创作童话前并没有专门请老师教过他怎么写童话;郭敬明韩寒同样没有老师如潘教授所说的,教他们如何从文本阅读中分析出写作的道道来再去进行创作。不过,诺奖得主莫言阅读能力之突出,他自己也深以为然。认为“指向写作”的阅读,才是作为专业的语文学习者的阅读本质所在,这一论点值得推敲。第一,什么叫做“专业的语文学习者”,在小学语文课堂上“专业的语文学习者”的定位与“梁羽生读金庸小说”是一个层次的吗?语文只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为学生生命奠基”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生绝对不是以成为“写作者”为目的的“专业的语文学习者”。即使在语文课堂上学生也不能被界定为管老师所言的“专业的语文学习者”,学生的语文学习,从母语学习的角度而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向度,是文化的熏陶和浸润,是为生命的成长打好精神的底子,而非研究如何写作。第二,诚如前面所讲,阅读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指向写作,阅读所承载的任务是丰富的、多样的,既指向知识,也指向能力,还指向方法、过程、精神、情感、价值观等。正如语文课程标准所强调的三维目标,阅读教学要在“三维”上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其中,让学生学会阅读,爱上阅读,是阅读教学最本质的、最具存在价值的定位与诉求。第三,为什么要进行阅读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目的决定方向的选择,决定阅读姿态的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阅读教学要不要教会学生为不同的目的去读书,答案显而易见。语文学习者的阅读本质所在,课标已说得很清楚,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语言文字运用”并不等于写作,它的内涵,比写作丰富多了。在此,我想不必赘述。管老师很自豪地指出“我”即边界,怎么理解都觉得这里的“我”指的就是教师自己,就是教师自己对语文课程和教学的“教师本位”的理解。如果教师即为边界,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放在什么位置,学生能不能在这一边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语文人生”?适合的才是正确的,试想,如果学生每读一篇课文,都要抽象出写法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