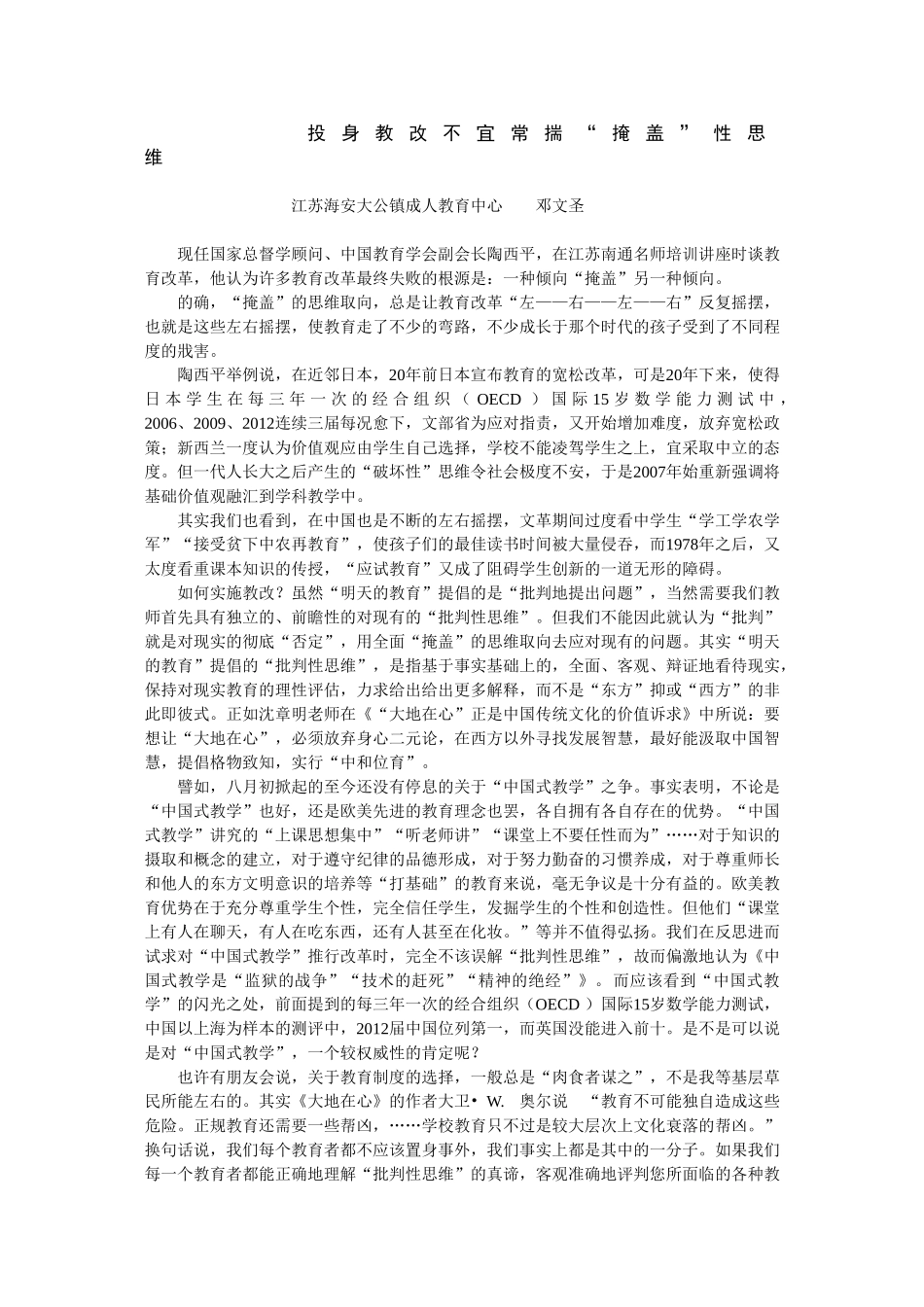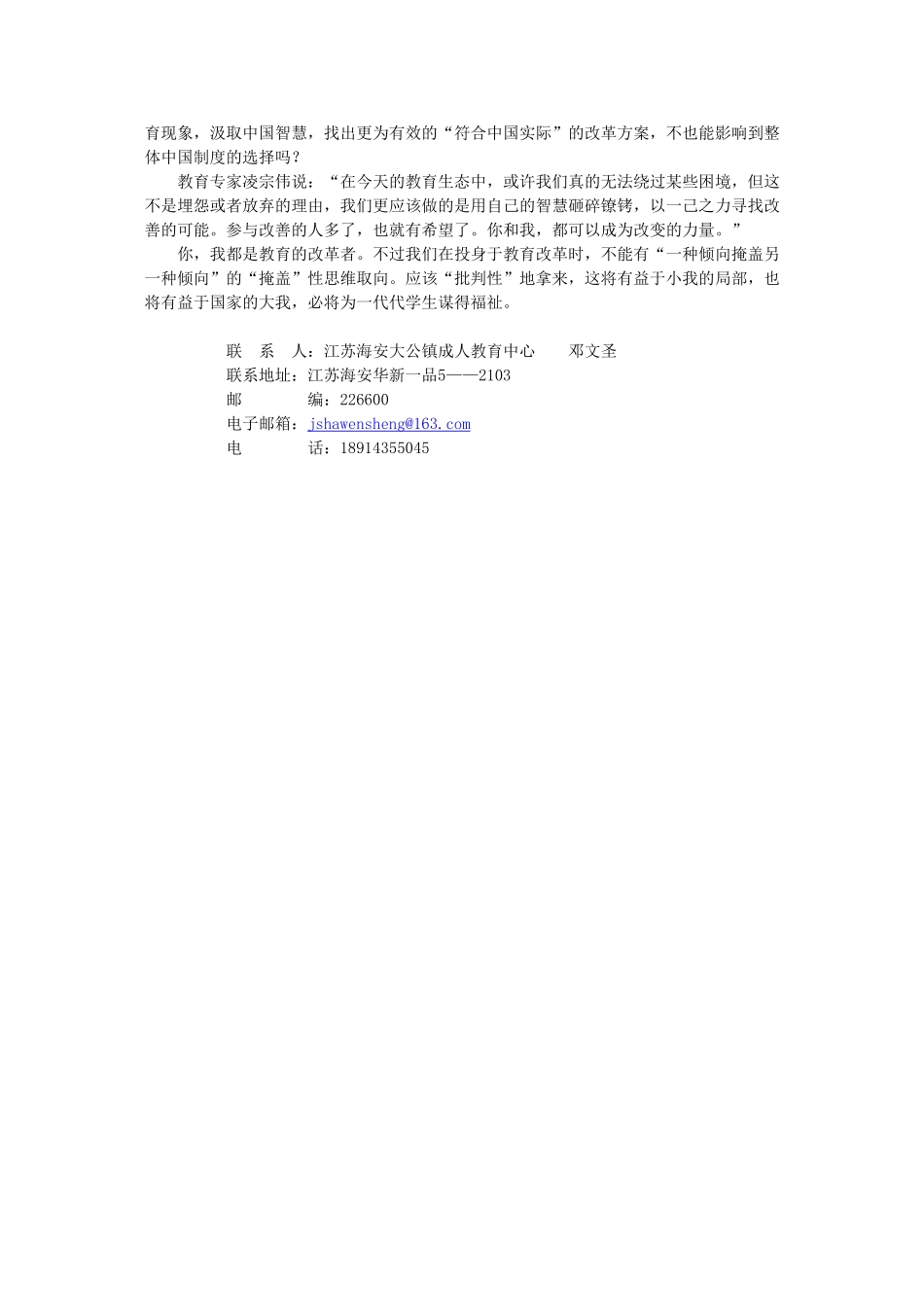投身教改不宜常揣“掩盖”性思维江苏海安大公镇成人教育中心邓文圣现任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在江苏南通名师培训讲座时谈教育改革,他认为许多教育改革最终失败的根源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确,“掩盖”的思维取向,总是让教育改革“左——右——左——右”反复摇摆,也就是这些左右摇摆,使教育走了不少的弯路,不少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孩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戕害。陶西平举例说,在近邻日本,20年前日本宣布教育的宽松改革,可是20年下来,使得日本学生在每三年一次的经合组织(OECD)国际15岁数学能力测试中,2006、2009、2012连续三届每况愈下,文部省为应对指责,又开始增加难度,放弃宽松政策;新西兰一度认为价值观应由学生自己选择,学校不能凌驾学生之上,宜采取中立的态度。但一代人长大之后产生的“破坏性”思维令社会极度不安,于是2007年始重新强调将基础价值观融汇到学科教学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中国也是不断的左右摇摆,文革期间过度看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孩子们的最佳读书时间被大量侵吞,而1978年之后,又太度看重课本知识的传授,“应试教育”又成了阻碍学生创新的一道无形的障碍。如何实施教改?虽然“明天的教育”提倡的是“批判地提出问题”,当然需要我们教师首先具有独立的、前瞻性的对现有的“批判性思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批判”就是对现实的彻底“否定”,用全面“掩盖”的思维取向去应对现有的问题。其实“明天的教育”提倡的“批判性思维”,是指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现实,保持对现实教育的理性评估,力求给出给出更多解释,而不是“东方”抑或“西方”的非此即彼式。正如沈章明老师在《“大地在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中所说:要想让“大地在心”,必须放弃身心二元论,在西方以外寻找发展智慧,最好能汲取中国智慧,提倡格物致知,实行“中和位育”。譬如,八月初掀起的至今还没有停息的关于“中国式教学”之争。事实表明,不论是“中国式教学”也好,还是欧美先进的教育理念也罢,各自拥有各自存在的优势。“中国式教学”讲究的“上课思想集中”“听老师讲”“课堂上不要任性而为”……对于知识的摄取和概念的建立,对于遵守纪律的品德形成,对于努力勤奋的习惯养成,对于尊重师长和他人的东方文明意识的培养等“打基础”的教育来说,毫无争议是十分有益的。欧美教育优势在于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完全信任学生,发掘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但他们“课堂上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等并不值得弘扬。我们在反思进而试求对“中国式教学”推行改革时,完全不该误解“批判性思维”,故而偏激地认为《中国式教学是“监狱的战争”“技术的赶死”“精神的绝经”》。而应该看到“中国式教学”的闪光之处,前面提到的每三年一次的经合组织(OECD)国际15岁数学能力测试,中国以上海为样本的测评中,2012届中国位列第一,而英国没能进入前十。是不是可以说是对“中国式教学”,一个较权威性的肯定呢?也许有朋友会说,关于教育制度的选择,一般总是“肉食者谋之”,不是我等基层草民所能左右的。其实《大地在心》的作者大卫•W.奥尔说“教育不可能独自造成这些危险。正规教育还需要一些帮凶,……学校教育只不过是较大层次上文化衰落的帮凶。”换句话说,我们每个教育者都不应该置身事外,我们事实上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每一个教育者都能正确地理解“批判性思维”的真谛,客观准确地评判您所面临的各种教育现象,汲取中国智慧,找出更为有效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方案,不也能影响到整体中国制度的选择吗?教育专家凌宗伟说:“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或许我们真的无法绕过某些困境,但这不是埋怨或者放弃的理由,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砸碎镣铐,以一己之力寻找改善的可能。参与改善的人多了,也就有希望了。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你,我都是教育的改革者。不过我们在投身于教育改革时,不能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掩盖”性思维取向。应该“批判性”地拿来,这将有益于小我的局部,也将有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