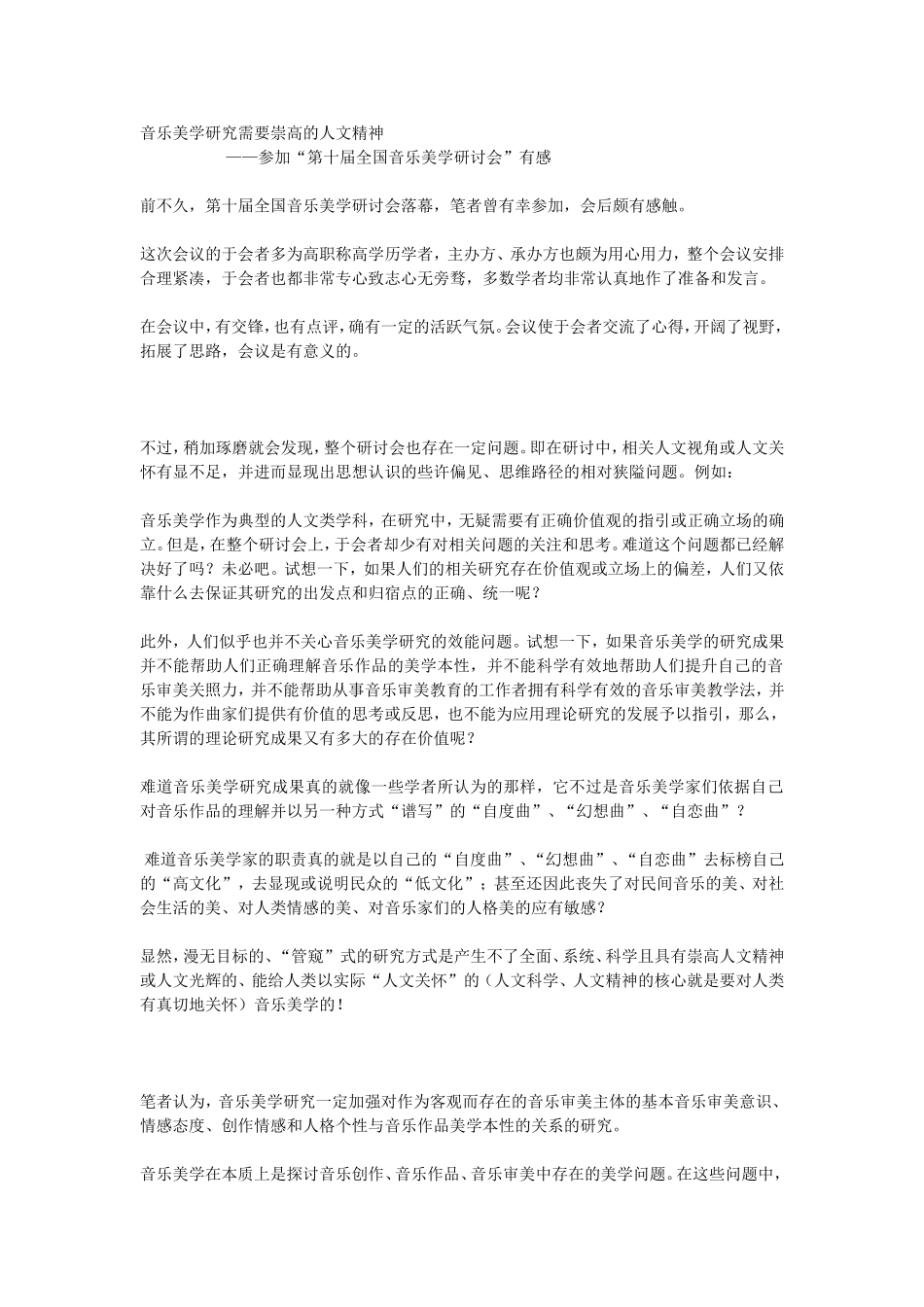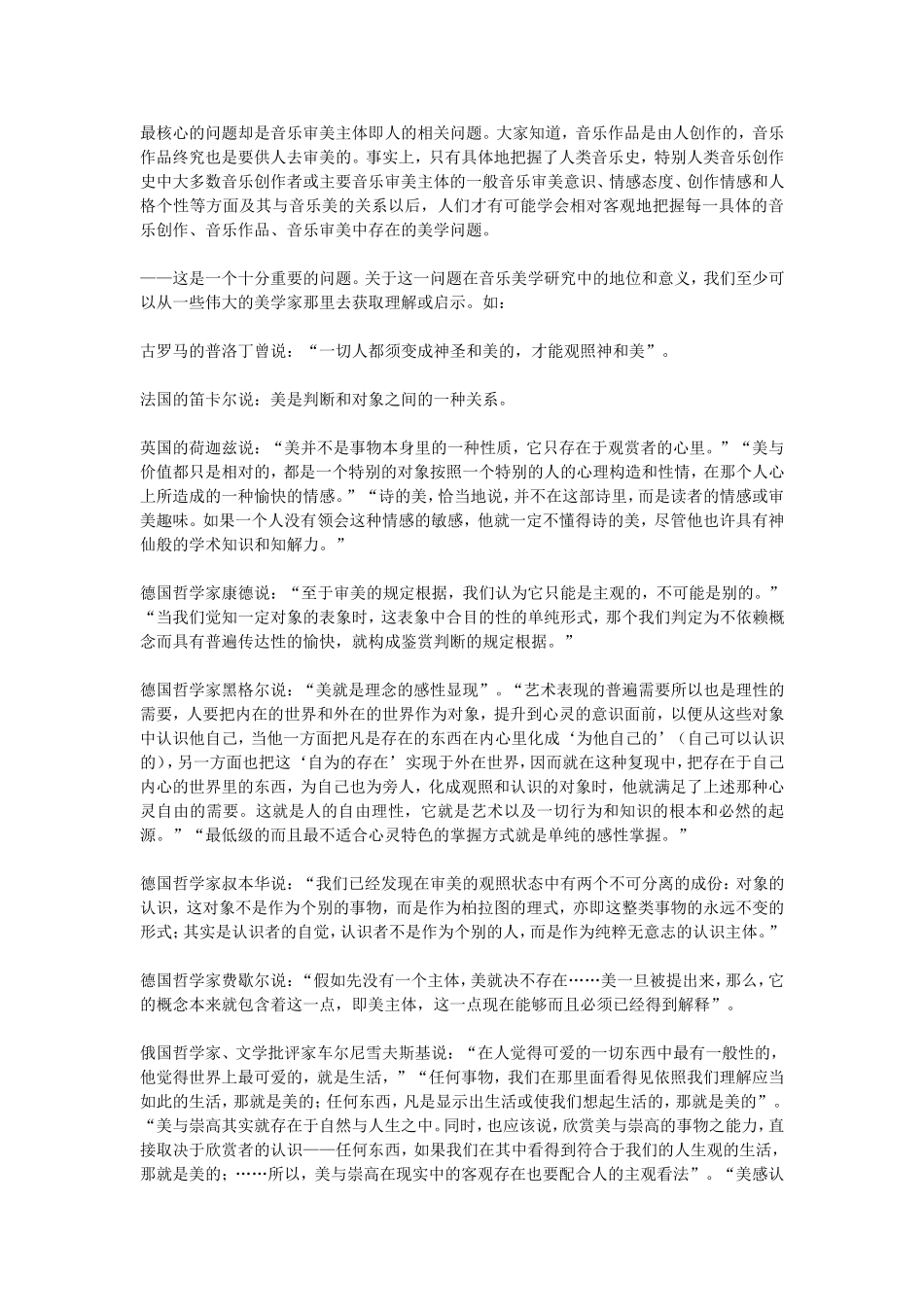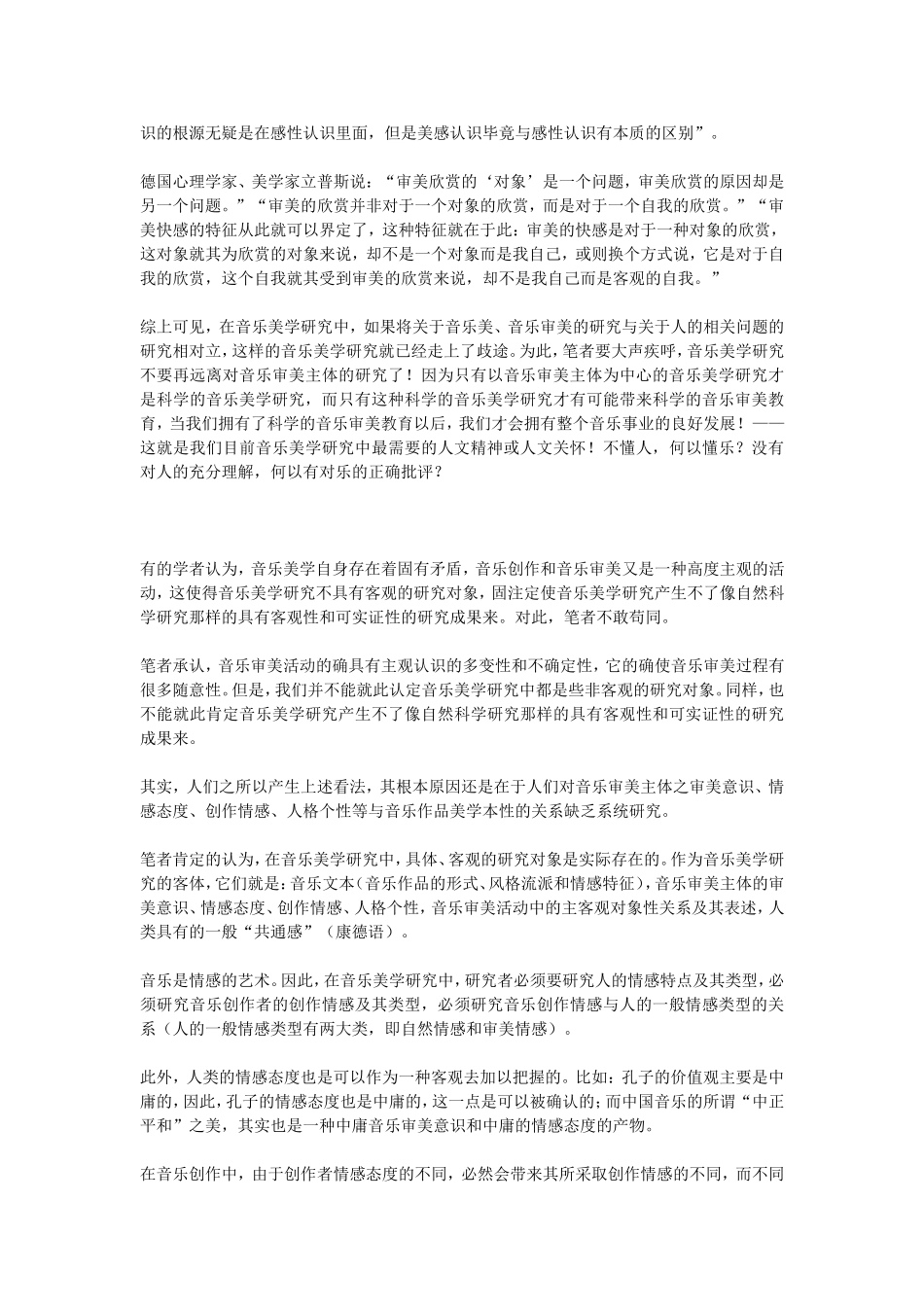音乐美学研究需要崇高的人文精神——参加“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研讨会”有感前不久,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研讨会落幕,笔者曾有幸参加,会后颇有感触。这次会议的于会者多为高职称高学历学者,主办方、承办方也颇为用心用力,整个会议安排合理紧凑,于会者也都非常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多数学者均非常认真地作了准备和发言。在会议中,有交锋,也有点评,确有一定的活跃气氛。会议使于会者交流了心得,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会议是有意义的。不过,稍加琢磨就会发现,整个研讨会也存在一定问题。即在研讨中,相关人文视角或人文关怀有显不足,并进而显现出思想认识的些许偏见、思维路径的相对狭隘问题。例如:音乐美学作为典型的人文类学科,在研究中,无疑需要有正确价值观的指引或正确立场的确立。但是,在整个研讨会上,于会者却少有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难道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好了吗?未必吧。试想一下,如果人们的相关研究存在价值观或立场上的偏差,人们又依靠什么去保证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正确、统一呢?此外,人们似乎也并不关心音乐美学研究的效能问题。试想一下,如果音乐美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音乐作品的美学本性,并不能科学有效地帮助人们提升自己的音乐审美关照力,并不能帮助从事音乐审美教育的工作者拥有科学有效的音乐审美教学法,并不能为作曲家们提供有价值的思考或反思,也不能为应用理论研究的发展予以指引,那么,其所谓的理论研究成果又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呢?难道音乐美学研究成果真的就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不过是音乐美学家们依据自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并以另一种方式“谱写”的“自度曲”、“幻想曲”、“自恋曲”?难道音乐美学家的职责真的就是以自己的“自度曲”、“幻想曲”、“自恋曲”去标榜自己的“高文化”,去显现或说明民众的“低文化”;甚至还因此丧失了对民间音乐的美、对社会生活的美、对人类情感的美、对音乐家们的人格美的应有敏感?显然,漫无目标的、“管窥”式的研究方式是产生不了全面、系统、科学且具有崇高人文精神或人文光辉的、能给人类以实际“人文关怀”的(人文科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要对人类有真切地关怀)音乐美学的!笔者认为,音乐美学研究一定加强对作为客观而存在的音乐审美主体的基本音乐审美意识、情感态度、创作情感和人格个性与音乐作品美学本性的关系的研究。音乐美学在本质上是探讨音乐创作、音乐作品、音乐审美中存在的美学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却是音乐审美主体即人的相关问题。大家知道,音乐作品是由人创作的,音乐作品终究也是要供人去审美的。事实上,只有具体地把握了人类音乐史,特别人类音乐创作史中大多数音乐创作者或主要音乐审美主体的一般音乐审美意识、情感态度、创作情感和人格个性等方面及其与音乐美的关系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学会相对客观地把握每一具体的音乐创作、音乐作品、音乐审美中存在的美学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音乐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伟大的美学家那里去获取理解或启示。如:古罗马的普洛丁曾说:“一切人都须变成神圣和美的,才能观照神和美”。法国的笛卡尔说:美是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英国的荷迦兹说:“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美与价值都只是相对的,都是一个特别的对象按照一个特别的人的心理构造和性情,在那个人心上所造成的一种愉快的情感。”“诗的美,恰当地说,并不在这部诗里,而是读者的情感或审美趣味。如果一个人没有领会这种情感的敏感,他就一定不懂得诗的美,尽管他也许具有神仙般的学术知识和知解力。”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至于审美的规定根据,我们认为它只能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别的。”“当我们觉知一定对象的表象时,这表象中合目的性的单纯形式,那个我们判定为不依赖概念而具有普遍传达性的愉快,就构成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