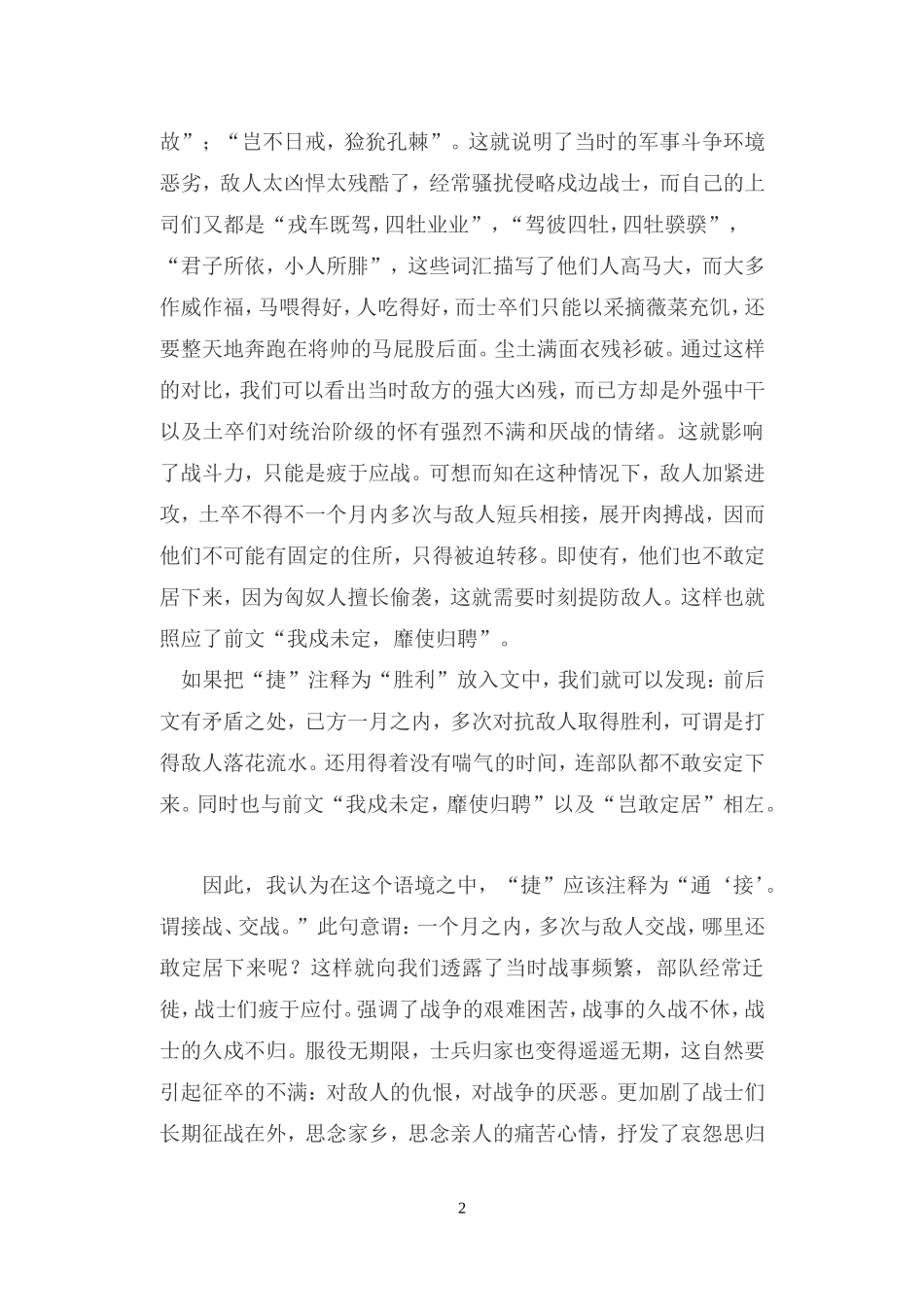这样注释对吗?——《采薇》一处注释商榷王卫锋《采薇》一文,其中“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一句中的“捷”的注释为“胜”。而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种注释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在此提出以供大家指正。王力在其《古代汉语字典》中讲到“捷”的意义时,其中一项“胜利”就是以“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为例。而郭锡良等人编著的《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一版)在其注释为“通‘接’,交接”(第372页);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在其注释为“接,谓接战,交战”(上编第一册第29页);《中国文学名作欣赏》(谢昭新主编,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在其注释为“通‘接’,即交战”(第19页)。在《吴越春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即捷末”,后来元朝的徐天祜为此书作了考证和注解,“捷”应作“接”,即“接住竹梢”(参考网上资料)。与语文教材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也是把那一句话翻译成为:“一个月的交战就有几轮”。面对众多注释,孰优孰劣?一时难以定论。不过古人在读诗读经时,一再倡导“诗无达诂”、“以意逆志”之法,到现在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此我认为要给予这个字一个好的注释,最好把它放入整篇文章的大环境之中,这样或许就明朗的多了。文中的主人公征战在外,长期同敌人作战,不得回家,心中充满了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的渴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文中给予了交待,主要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1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这就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斗争环境恶劣,敌人太凶悍太残酷了,经常骚扰侵略戍边战士,而自己的上司们又都是“戎车既驾,四牡业业”,“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些词汇描写了他们人高马大,而大多作威作福,马喂得好,人吃得好,而士卒们只能以采摘薇菜充饥,还要整天地奔跑在将帅的马屁股后面。尘土满面衣残衫破。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敌方的强大凶残,而已方却是外强中干以及土卒们对统治阶级的怀有强烈不满和厌战的情绪。这就影响了战斗力,只能是疲于应战。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加紧进攻,土卒不得不一个月内多次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因而他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住所,只得被迫转移。即使有,他们也不敢定居下来,因为匈奴人擅长偷袭,这就需要时刻提防敌人。这样也就照应了前文“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如果把“捷”注释为“胜利”放入文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前后文有矛盾之处,已方一月之内,多次对抗敌人取得胜利,可谓是打得敌人落花流水。还用得着没有喘气的时间,连部队都不敢安定下来。同时也与前文“我戍未定,靡使归聘”以及“岂敢定居”相左。因此,我认为在这个语境之中,“捷”应该注释为“通‘接’。谓接战、交战。”此句意谓:一个月之内,多次与敌人交战,哪里还敢定居下来呢?这样就向我们透露了当时战事频繁,部队经常迁徙,战士们疲于应付。强调了战争的艰难困苦,战事的久战不休,战士的久戍不归。服役无期限,士兵归家也变得遥遥无期,这自然要引起征卒的不满:对敌人的仇恨,对战争的厌恶。更加剧了战士们长期征战在外,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痛苦心情,抒发了哀怨思归2的情感。从而与全文的感情基调相吻合。中国人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从古到今,有之。其中在古代诗歌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本文就是通过对士兵们不断地与敌人交战,在戍边单调困苦的生活中,思念故国家园的方式来谴责战争,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因此把笔者认为,“捷”作为“与‘接’相通,“交接”解时,可以更好地理解全文主旨。(本文发表于《考试报》高一语文版总第1157期)赤子之心式的自言自语——重读《我为什么而活着》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而活着?我将要到哪里去?”这也是人类对自身存在进行地永恒追问。作为“20世纪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的罗素,对这个永恒的命题也进行了探讨,并向世人发出了历史上的最强音,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篇永垂不朽的“人生宣言”—《我为什么而活着》。人类历史上好多大哲学家,都是单纯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