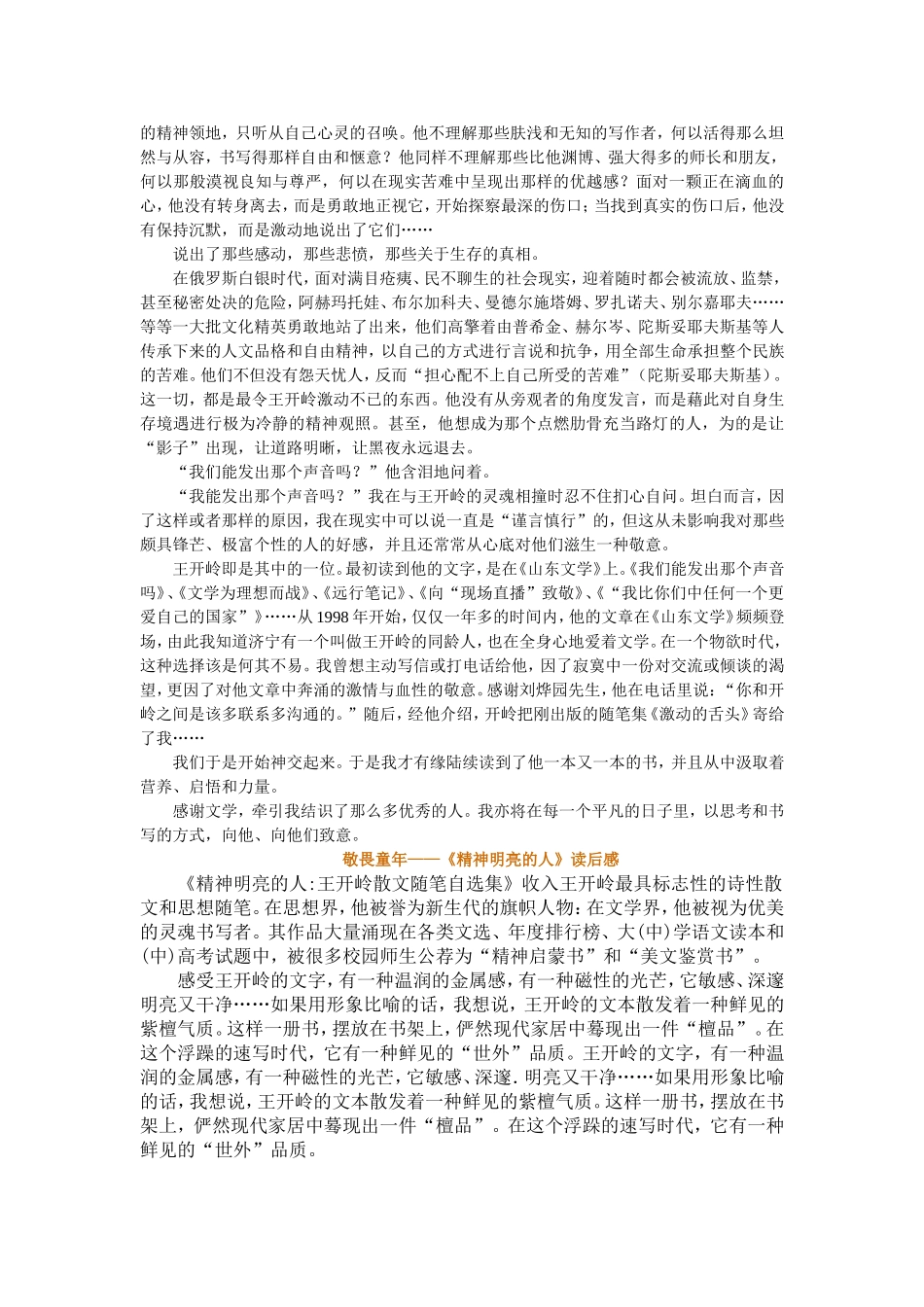循着那样的声音——王开岭思想随笔读札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一直把写作视为不甘沉沦于庸常生活的一种自救方式,是此岸向彼岸的泅渡。所以我固执地以为,写作的快乐更多地是指一种内在体验,尤其是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它其实仅仅是一种更为真实的个体存在方式。我努力去做了,平静地生活,安静地写作,与世无争,心安理得。直到王开岭在我视域中出现,这种所谓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他说,“在上帝缺席的年代,艺术家是这样一群履行‘神职’的人——面对狼藉的生存,他必须哭泣。然而他必须停下哭泣,必须在夜的中央祭上理想的蜡烛。擎举着,颤巍着,照亮黑衣上的‘十字’,然后用它照亮……这是一道仪式。更像一种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是可敬的。因其民间身份的卑微与注定的孤独伤痛而愈发可敬。”一个绝决的、不够“安分”的年轻人,在对自我灵魂反复进行拷问的同时,亦向庞大的令人窒息的现实秩序表示了质疑和抗争——他关心的是,“我们可曾真正生活过?真正有力地心跳过?”这样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渗透在他所写下的每一篇文章之中:对陌生的“外省人”的悲悯,对“高大而又拄着拐杖”的歌德的叹惋,对慷慨赴死的荆轲的缅怀,对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的敬重,对周永臣“一个人的遭遇”的诘问,对捍卫人类尊严和良知的顾准的感激……在一片喧嚣和浮躁之中,我看到了那张充满忧愤的脸。一张年轻的、含泪的脸。一个可以视之为“兄长”的人。“哭泣是因为灵魂的难度与真实,是精神严肃和强烈震动的结果。一个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是无法抑制住哭泣的。”必须这样。只能这样。现实就那么存在着,无需证明或掩饰。王开岭开始独自作战,他的价值指向,始终都在瞄准良知、正义和尊严。这些本属常识范畴的东西,之所以被他频频提起,正是因了世人对它们的日渐疏远和淡忘。王开岭对此表现出了深深的不满和忧虑,他以自己的激情赋予这些“词语”以血性,用自己的青春助延它们的生命,从而感召更多人的生命。他一次次含泪捧起那些散落在浩淼历史长河中的珍贵精神片断,企望以此唤醒人们关于爱与良知的记忆。正如福克纳所说的,“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王开岭用心去做了。时下很多所谓的宽容和超脱,常常是以思想的苍白和品格的软弱为背景的。在这样的境况中,王开岭无畏的抗争、啼血的呐喊,也就显得格外突兀。于是可以想象,那些毫无精神性的訾议,断章取义的评判,甚至粗暴的责难,将会怎样地接踵而至。他独自承受着,没有放弃继续言说的权利。在这个人们时常被物欲折腾得筋疲力尽,而对良知与尊严漠然视之的年代,王开岭自觉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之所以在苦苦支撑生存的隙间,挤出一点灵魂的胆汁,那是因为我觉得生命要有尊严,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否则,即对不起生命和生存。”虽然他自知“那些障碍在等着我,那些因阴暗而结实无比的墙在等着我”,但他坚信,“来自理想的厄运正深深满足着我,打击我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记得博尔赫斯说过,一切阅读都暗示着一次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一次同谋。读王开岭的文章,我时常想象着他在那些不眠深夜里的神情。或许,对于那些所谓历尽沧桑的人而言,会从他的抗争中听出某种“颤音”,可是在一个拒绝浮躁和麻木,固守良知和正义的人看来,它确是振奋人心的——因为正是这种抗争与诘问,体现了一种将个人、哪怕是再微弱的个人的尊严凌驾于庞大的现存秩序之上的冲动。这份冲动的价值,在于它让强大的现实不禁为之一震,让激动的人们更为长久地激动着,同时,它也为另一种可能创造了可能。它的价值,更多地在于行动和姿态。当人们沉浸在安逸里而日渐冷漠、麻木之时,王开岭们必然地出现了,一种抗争的姿态必然地出现了。斯巴达·西隆曾经说过,莫让你的舌头抢先于你的思考。王开岭的抽屉文字首次结集出版时,他为之命名《激动的舌头》,这显然是有着别样涵义的。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有着独立自治的精神领地,只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