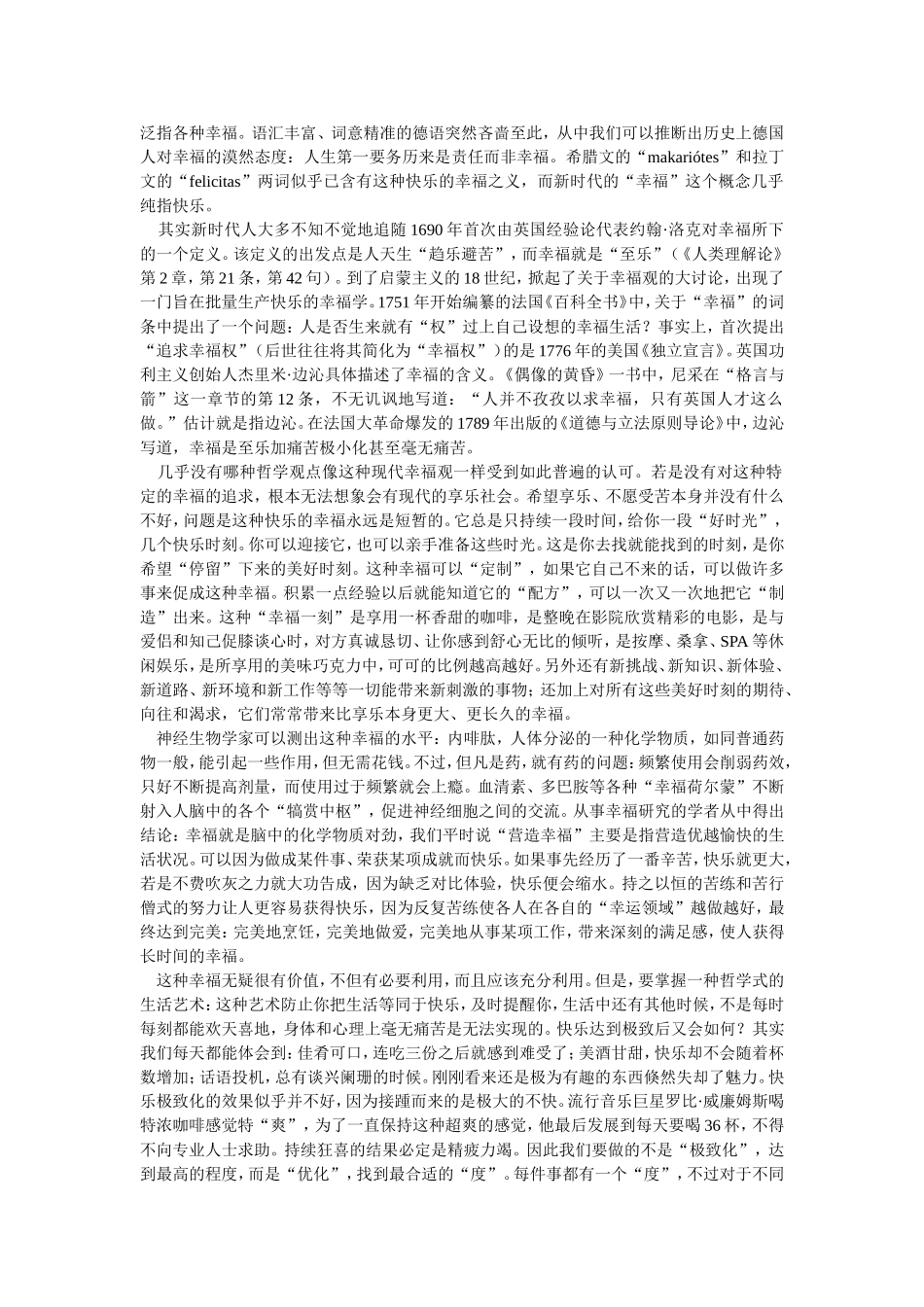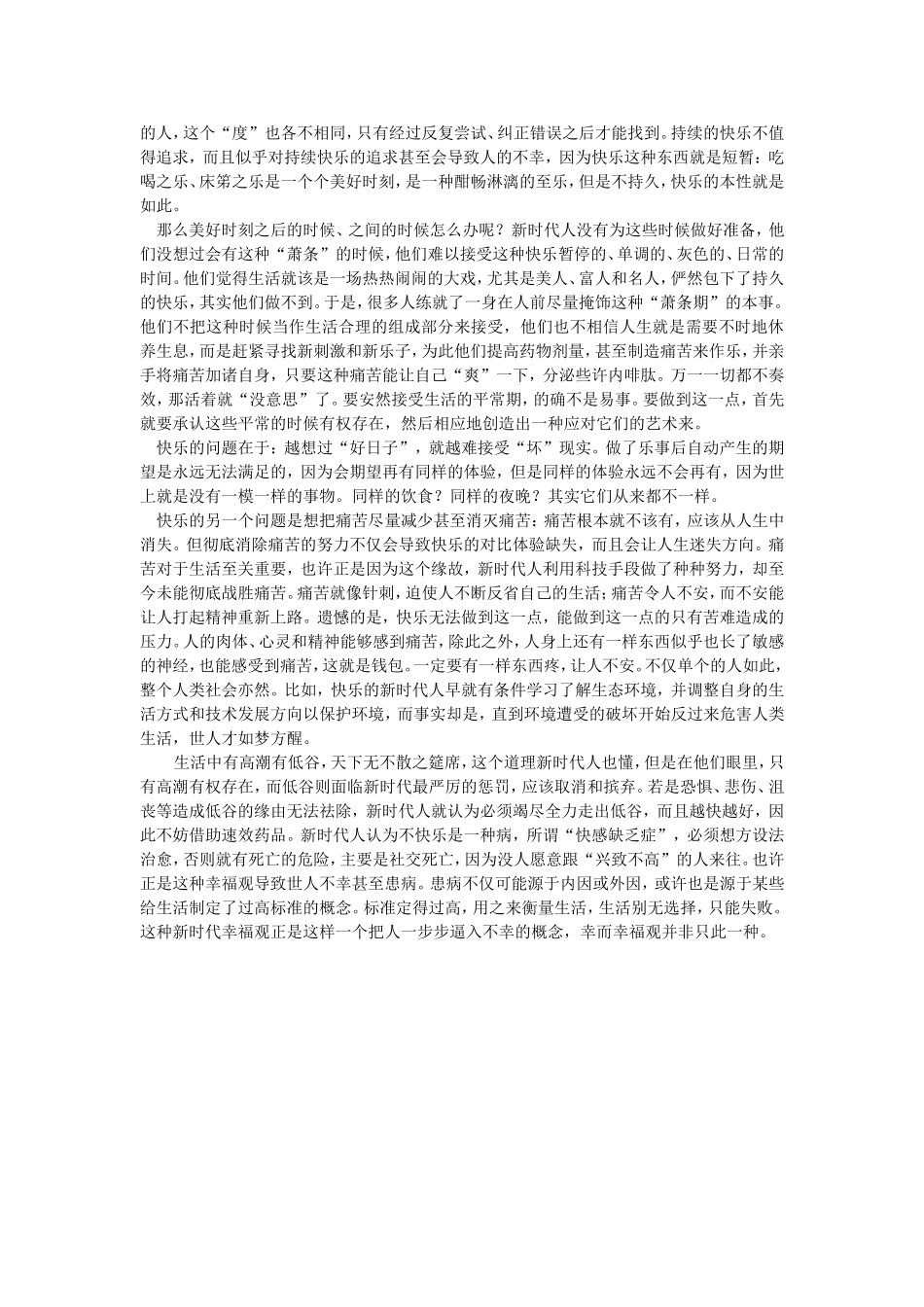关于幸福的断想作者:威廉.施密德【关于作者】威廉·施密德1953年出生于德国比伦豪森,是一位哲学教授,同时还在瑞士的一所医院担任哲学心灵抚慰师。本文摘自他撰写的《幸福》一书。该书去年在德国出版,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小册,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关于幸福的讨论甚至成为一个社会话题。据悉,上海译文出版社已购得《幸福》中文版权,将于2012年年初翻译出版。好运第一种幸福是人生不断发生的“好运”,即正巧获得向往的东西或是有利的结局。现代德语泛指“幸福”的“Glück”一词源于中古高地德语的“运(gelücke)”。“运”在中世纪指某个巧合,不过原意不单指好的,也指坏的巧合。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把这种包括双重含义的“运”敬为神明,希腊文叫“T伥chē”,拉丁文叫“Fortuna”,法语和英语里演变成了“fortune”。后来这种“运”逐步演变,直到现代社会才完全变成单指好的、人所向往的巧合和机缘,只留下了正面含义。祝某人走“运”就是祝其得到好的巧合,“这回你又走运了”等于说“这回的巧合对你有利”。如果在结果不利甚至很糟时说这话,就是指巧合没有更糟真是走“运”,是“不幸中之大幸”。最糟糕的情况里都蕴含着正面因素。一个人的出生或许就是巧合,正如此后经历的众多事情。这些幸与不幸的巧合有否“意义”,是否预设,答案至今未能找到,估计将来也不会出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那么谁来定这个“命”呢?毕竟,无论幸与不幸,各种巧合常常呈现惊人的规律,俨然在依照某个计划进行。比如一两桩幸事仿佛会产生一种动力,往往引来更多的好事。反之,一次不走运,就会接二连三地“招来晦气”,似乎巧合的发生遵循一种“秋千规律”,一个巧合轻轻一推,人生就像荡秋千一般顺势上下,使当事人每回都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好运”最大的特点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求的只是世人的应对态度:我们既可以开放自己,接受一次相遇、一段经历和一个信息,也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既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或是生活的外界条件上布好罗网等待巧合来投,也可以筑好铜墙铁壁,让巧合一一跌落。世人真的可以封闭自己,不让自己遭遇任何不好的巧合吗?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就曾说过:“世上所有不幸均因人不待在自己家中。”而另一个选择是开放自己,主动地关注、敏锐地感觉到并抓住有利时机,加之平时为迎接良机做足准备。举一英语格言为例:“好运等于机遇加准备。”准备就绪了,就只需等待机遇的耐心和当机遇不来或不如意时的坚忍态度。这种开放态度似乎有助于促使好运到来:好运爱去欢迎它的地方,不愿听到说它“来得不是时候”的怨言。好运仿佛也有生命,能准确地感知哪里期待它,哪里嫌弃它。我们不妨对好运采取攻势,挠挠它的痒痒,即使求不到,也要给它一个机会:希望遇到某人、经历某事或是得到某个信息的人不妨把心愿与人分享,比如跟网友聊聊,心想事成的概率会比把希望深锁心中大幅上升。从不摸彩的人自然永无机会中奖,不过即便一举中了大奖,也远不意味着真能用好它:一次意外的好运不会自动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好运虽然可以改善生活的外在条件,却会削弱我们内心改善生活的意志。因此时间可能最终证明一次好运竟是厄运,而厄运或许倒是好运。不管怎么样,对于新时代的人来说,比好运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幸福。快乐新时代人具体追求的幸福大的包括生活安定、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事业有成、情趣丰富、兴致勃勃。也就是说:一切公认的好事。重点追求的是“快乐”,万一出现“不快”,就要尽快摆脱这种讨厌的干扰。“快乐”,英语叫“happiness”,法语叫“bonheur”。而德语中却只有一个名词“Glück”泛指各种幸福。语汇丰富、词意精准的德语突然吝啬至此,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历史上德国人对幸福的漠然态度:人生第一要务历来是责任而非幸福。希腊文的“makariótes”和拉丁文的“felicitas”两词似乎已含有这种快乐的幸福之义,而新时代的“幸福”这个概念几乎纯指快乐。其实新时代人大多不知不觉地追随1690年首次由英国经验论代表约翰·洛克对幸福所下的一个定义。该定义的出发点是人天生“趋乐避苦”,而幸福就是“至乐”(《人类理解论》第2章,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