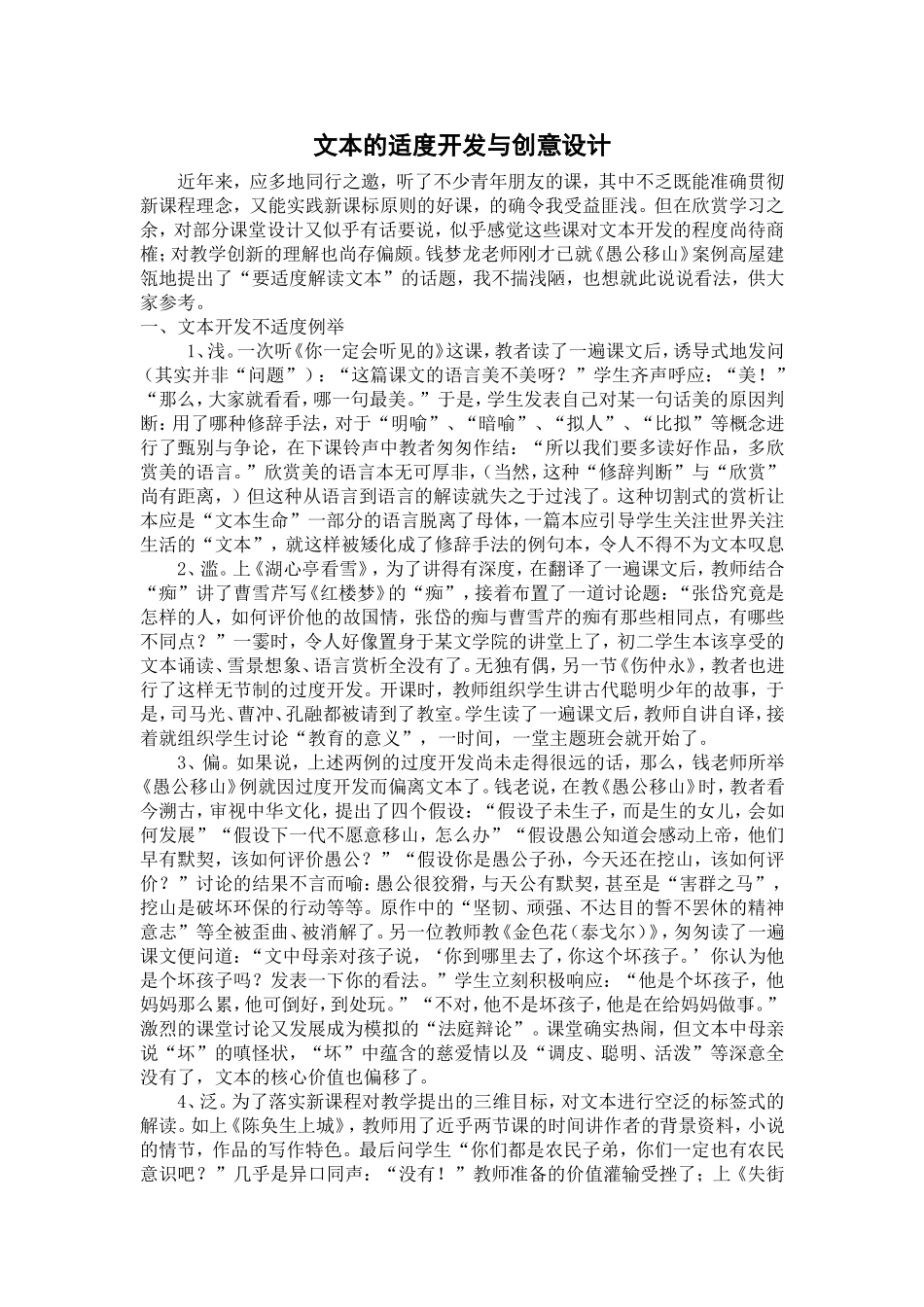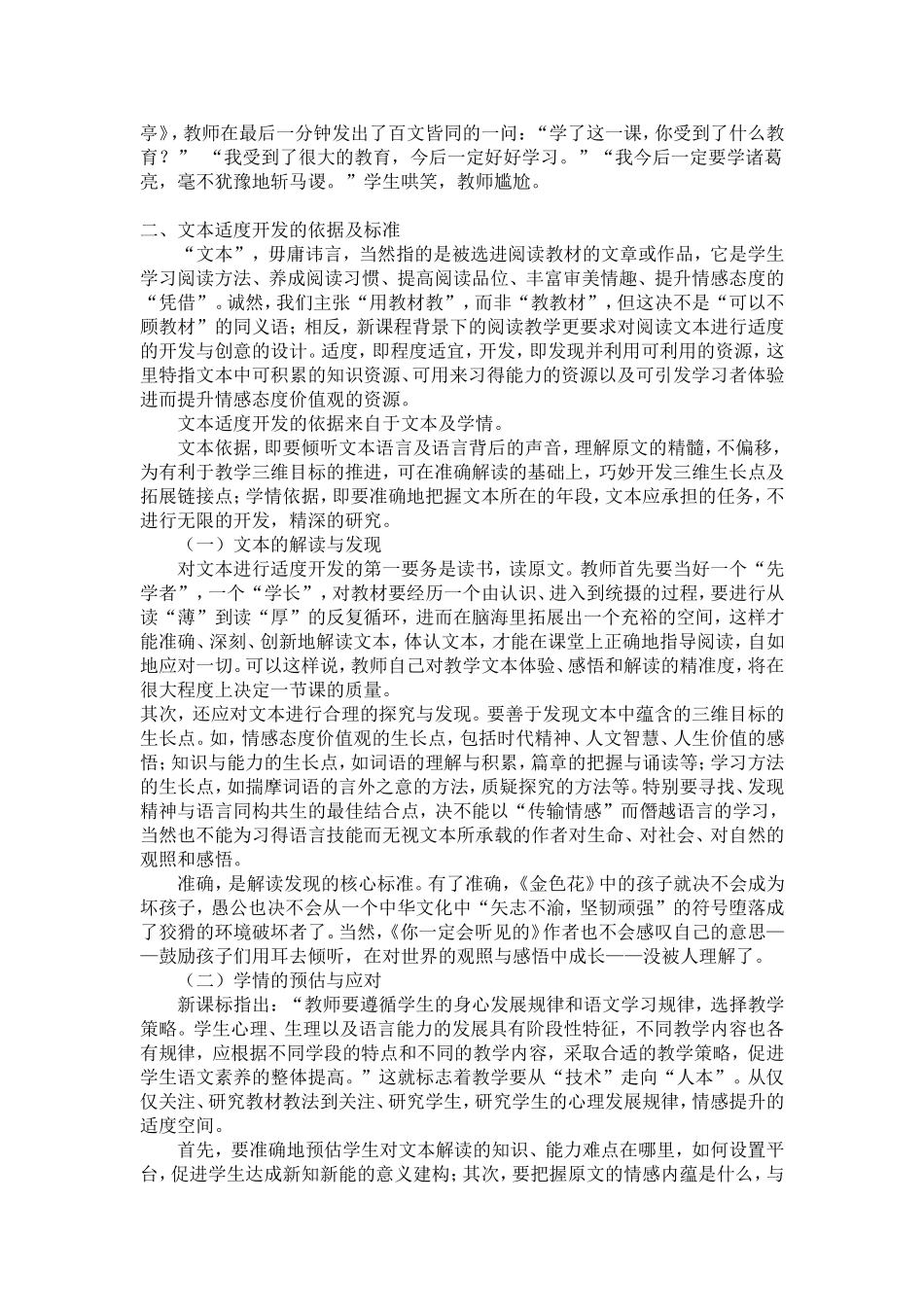文本的适度开发与创意设计近年来,应多地同行之邀,听了不少青年朋友的课,其中不乏既能准确贯彻新课程理念,又能实践新课标原则的好课,的确令我受益匪浅。但在欣赏学习之余,对部分课堂设计又似乎有话要说,似乎感觉这些课对文本开发的程度尚待商榷;对教学创新的理解也尚存偏颇。钱梦龙老师刚才已就《愚公移山》案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要适度解读文本”的话题,我不揣浅陋,也想就此说说看法,供大家参考。一、文本开发不适度例举1、浅。一次听《你一定会听见的》这课,教者读了一遍课文后,诱导式地发问(其实并非“问题”):“这篇课文的语言美不美呀?”学生齐声呼应:“美!”“那么,大家就看看,哪一句最美。”于是,学生发表自己对某一句话美的原因判断:用了哪种修辞手法,对于“明喻”、“暗喻”、“拟人”、“比拟”等概念进行了甄别与争论,在下课铃声中教者匆匆作结:“所以我们要多读好作品,多欣赏美的语言。”欣赏美的语言本无可厚非,(当然,这种“修辞判断”与“欣赏”尚有距离,)但这种从语言到语言的解读就失之于过浅了。这种切割式的赏析让本应是“文本生命”一部分的语言脱离了母体,一篇本应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关注生活的“文本”,就这样被矮化成了修辞手法的例句本,令人不得不为文本叹息2、滥。上《湖心亭看雪》,为了讲得有深度,在翻译了一遍课文后,教师结合“痴”讲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痴”,接着布置了一道讨论题:“张岱究竟是怎样的人,如何评价他的故国情,张岱的痴与曹雪芹的痴有那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一霎时,令人好像置身于某文学院的讲堂上了,初二学生本该享受的文本诵读、雪景想象、语言赏析全没有了。无独有偶,另一节《伤仲永》,教者也进行了这样无节制的过度开发。开课时,教师组织学生讲古代聪明少年的故事,于是,司马光、曹冲、孔融都被请到了教室。学生读了一遍课文后,教师自讲自译,接着就组织学生讨论“教育的意义”,一时间,一堂主题班会就开始了。3、偏。如果说,上述两例的过度开发尚未走得很远的话,那么,钱老师所举《愚公移山》例就因过度开发而偏离文本了。钱老说,在教《愚公移山》时,教者看今溯古,审视中华文化,提出了四个假设:“假设子未生子,而是生的女儿,会如何发展”“假设下一代不愿意移山,怎么办”“假设愚公知道会感动上帝,他们早有默契,该如何评价愚公?”“假设你是愚公子孙,今天还在挖山,该如何评价?”讨论的结果不言而喻:愚公很狡猾,与天公有默契,甚至是“害群之马”,挖山是破坏环保的行动等等。原作中的“坚韧、顽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意志”等全被歪曲、被消解了。另一位教师教《金色花(泰戈尔)》,匆匆读了一遍课文便问道:“文中母亲对孩子说,‘你到哪里去了,你这个坏孩子。’你认为他是个坏孩子吗?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学生立刻积极响应:“他是个坏孩子,他妈妈那么累,他可倒好,到处玩。”“不对,他不是坏孩子,他是在给妈妈做事。”激烈的课堂讨论又发展成为模拟的“法庭辩论”。课堂确实热闹,但文本中母亲说“坏”的嗔怪状,“坏”中蕴含的慈爱情以及“调皮、聪明、活泼”等深意全没有了,文本的核心价值也偏移了。4、泛。为了落实新课程对教学提出的三维目标,对文本进行空泛的标签式的解读。如上《陈奂生上城》,教师用了近乎两节课的时间讲作者的背景资料,小说的情节,作品的写作特色。最后问学生“你们都是农民子弟,你们一定也有农民意识吧?”几乎是异口同声:“没有!”教师准备的价值灌输受挫了;上《失街亭》,教师在最后一分钟发出了百文皆同的一问:“学了这一课,你受到了什么教育?”“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我今后一定要学诸葛亮,毫不犹豫地斩马谡。”学生哄笑,教师尴尬。二、文本适度开发的依据及标准“文本”,毋庸讳言,当然指的是被选进阅读教材的文章或作品,它是学生学习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品位、丰富审美情趣、提升情感态度的“凭借”。诚然,我们主张“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但这决不是“可以不顾教材”的同义语;相反,新课程背景下的阅读教学更要求对阅读文本进行适度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