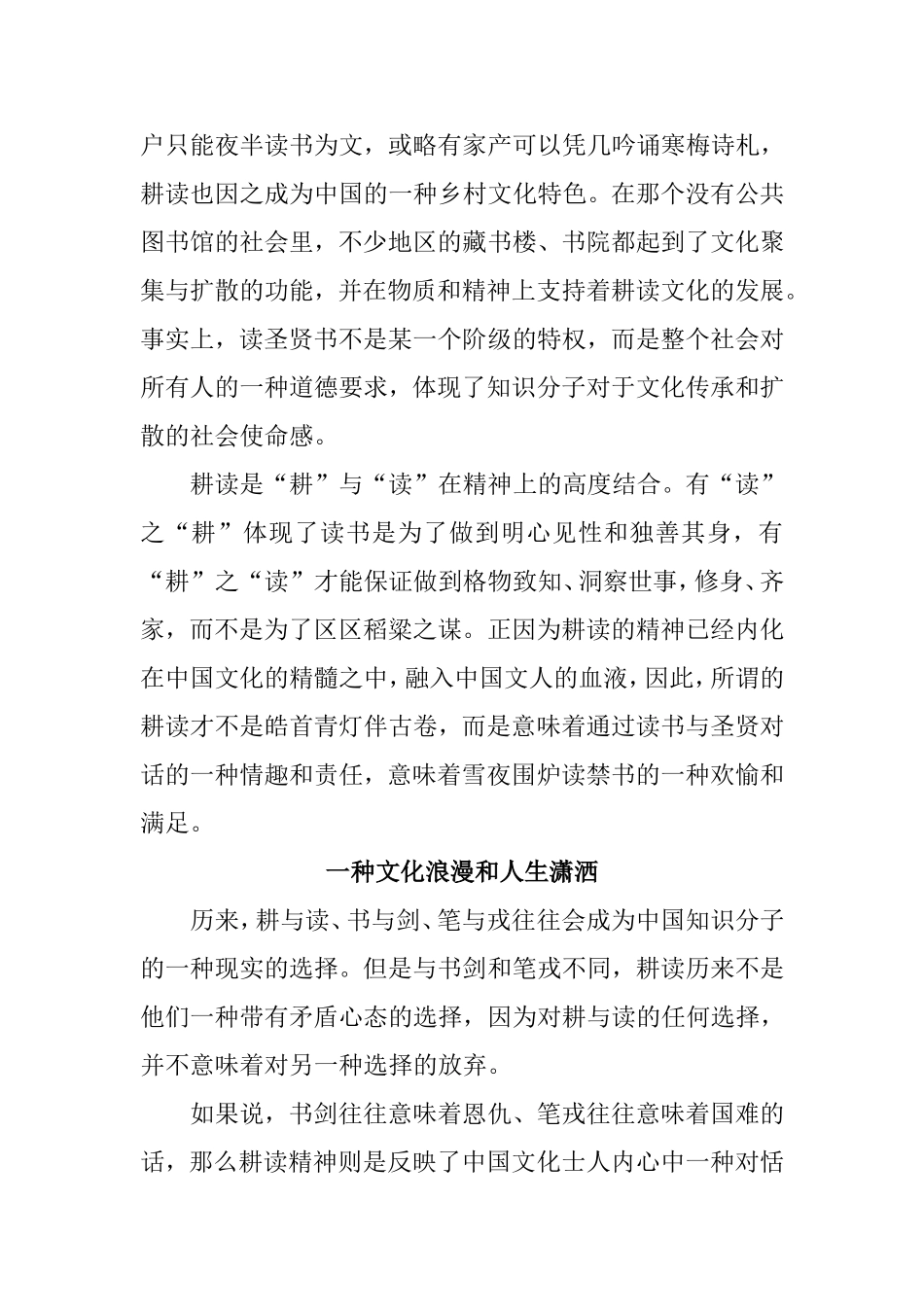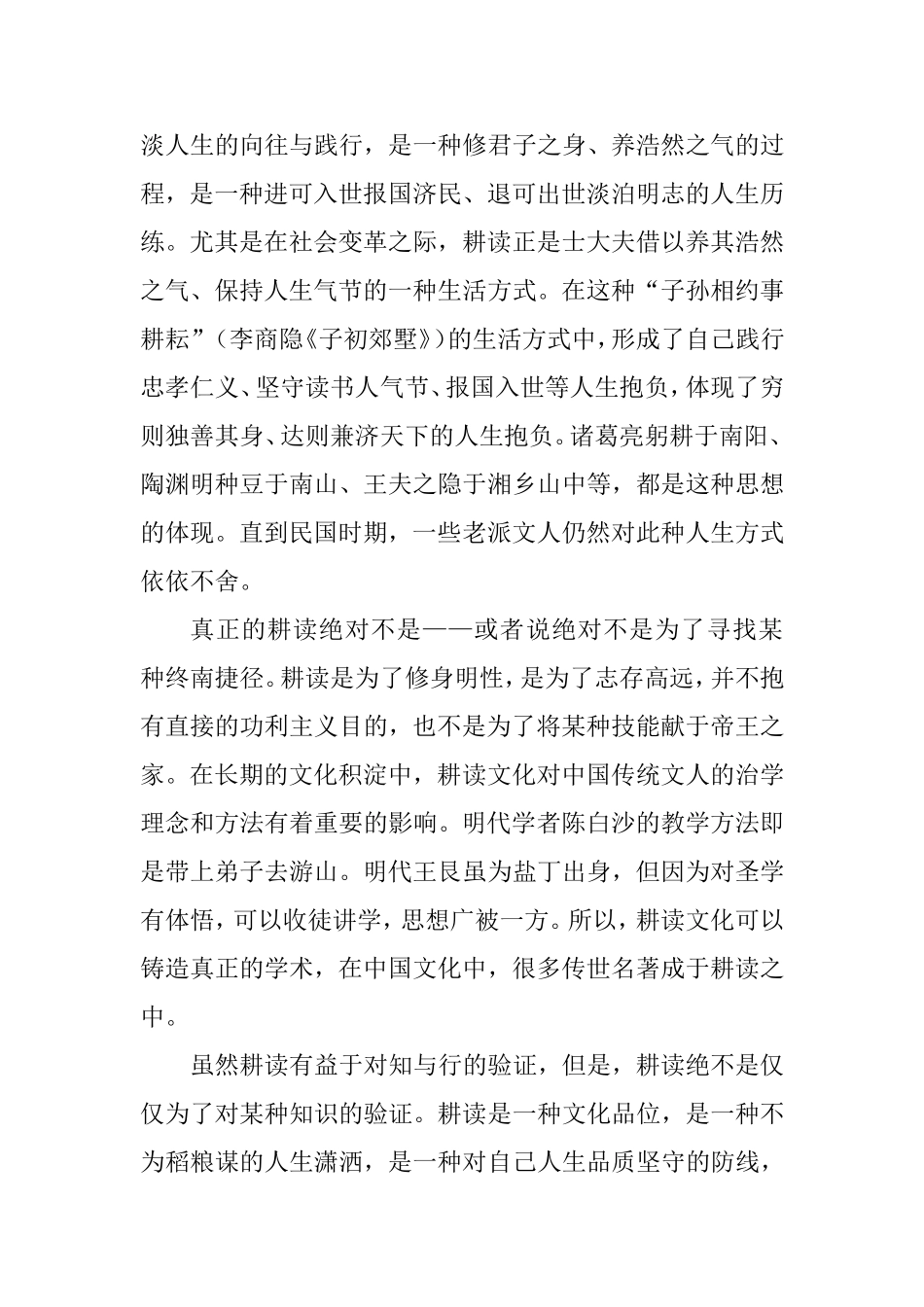“耕读”,数字时代的文化浪漫历史上,读书不仅是知识分子获得进阶修身的重要途径,也一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得以实现和传承的一种方式。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而言,读书更是一种使命。在本质上,所谓的“读书”即是读圣贤之书,并由之而发明本心,体认天理,以完善自身的道德构建,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由于这种读书使命的实施和传承都是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之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耕读文化,培育了内涵丰富的耕读精神。一种中国式的乡村文化耕读,简单地说即是将农忙耕种与农闲读书结合起来。“耕读”并称始于何时,现难以肯定,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有悠久的历史。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和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中国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代生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有家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到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有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体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独善其身,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而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文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味着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意味着雪夜围炉读禁书的一种欢愉和满足。一种文化浪漫和人生潇洒历来,耕与读、书与剑、笔与戎往往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是与书剑和笔戎不同,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选择的放弃。如果说,书剑往往意味着恩仇、笔戎往往意味着国难的话,那么耕读精神则是反映了中国文化士人内心中一种对恬淡人生的向往与践行,是一种修君子之身、养浩然之气的过程,是一种进可入世报国济民、退可出世淡泊明志的人生历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之际,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李商隐《子初郊墅》)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真正的耕读绝对不是——或者说绝对不是为了寻找某种终南捷径。耕读是为了修身明性,是为了志存高远,并不抱有直接的功利主义目的,也不是为了将某种技能献于帝王之家。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去游山。明代王艮虽为盐丁出身,但因为对圣学有体悟,可以收徒讲学,思想广被一方。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虽然耕读有益于对知与行的验证,但是,耕读绝不是仅仅为了对某种知识的验证。耕读是一种文化品位,是一种不为稻粮谋的人生潇洒,是一种对自己人生品质坚守的防线,这正是“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扬雄《法言·学行》)所以“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思想也被融入读书的精神和旨趣之中,是耕读者对传统的家国天下理想的一种具体践行。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耕读都是与经典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