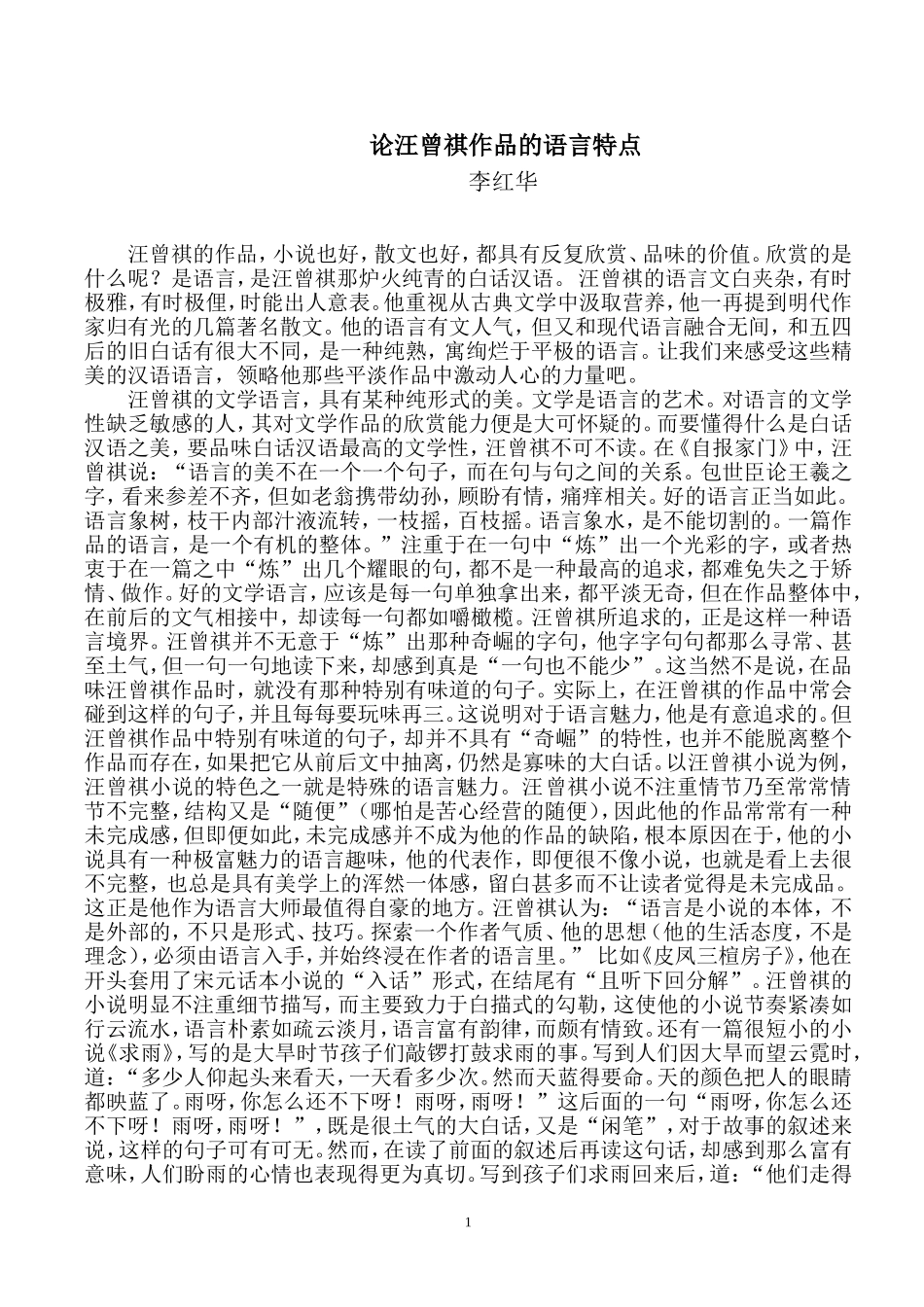论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点李红华汪曾祺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具有反复欣赏、品味的价值。欣赏的是什么呢?是语言,是汪曾祺那炉火纯青的白话汉语。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著名散文。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和五四后的旧白话有很大不同,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让我们来感受这些精美的汉语语言,领略他那些平淡作品中激动人心的力量吧。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纯形式的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便是大可怀疑的。而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象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于在一句中“炼”出一个光彩的字,或者热衷于在一篇之中“炼”出几个耀眼的句,都不是一种最高的追求,都难免失之于矫情、做作。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读每一句都如嚼橄榄。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境界。汪曾祺并不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地读下来,却感到真是“一句也不能少”。这当然不是说,在品味汪曾祺作品时,就没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实际上,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常会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且每每要玩味再三。这说明对于语言魅力,他是有意追求的。但汪曾祺作品中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却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并不能脱离整个作品而存在,如果把它从前后文中抽离,仍然是寡味的大白话。以汪曾祺小说为例,汪曾祺小说的特色之一就是特殊的语言魅力。汪曾祺小说不注重情节乃至常常情节不完整,结构又是“随便”(哪怕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种未完成感,但即便如此,未完成感并不成为他的作品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极富魅力的语言趣味,他的代表作,即便很不像小说,也就是看上去很不完整,也总是具有美学上的浑然一体感,留白甚多而不让读者觉得是未完成品。这正是他作为语言大师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汪曾祺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比如《皮凤三楦房子》,他在开头套用了宋元话本小说的“入话”形式,在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汪曾祺的小说明显不注重细节描写,而主要致力于白描式的勾勒,这使他的小说节奏紧凑如行云流水,语言朴素如疏云淡月,语言富有韵律,而颇有情致。还有一篇很短小的小说《求雨》,写的是大旱时节孩子们敲锣打鼓求雨的事。写到人们因大旱而望云霓时,道:“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这后面的一句“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既是很土气的大白话,又是“闲笔”,对于故事的叙述来说,这样的句子可有可无。然而,在读了前面的叙述后再读这句话,却感到那么富有意味,人们盼雨的心情也表现得更为真切。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道:“他们走得1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这最后的一句“一睡就睡着了”,是纯粹的口语,仿佛随时能从野老村妪口中听到,但放在这里,却又若有神助,令人回味不已。用“新鲜而单纯”来评价汪曾祺的语言,也极合适。具有新鲜而单纯的口语美,可谓是汪曾祺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整个新文学史上,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在《陈泥鳅》这篇小说中,汪曾祺这样写陈泥鳅:“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