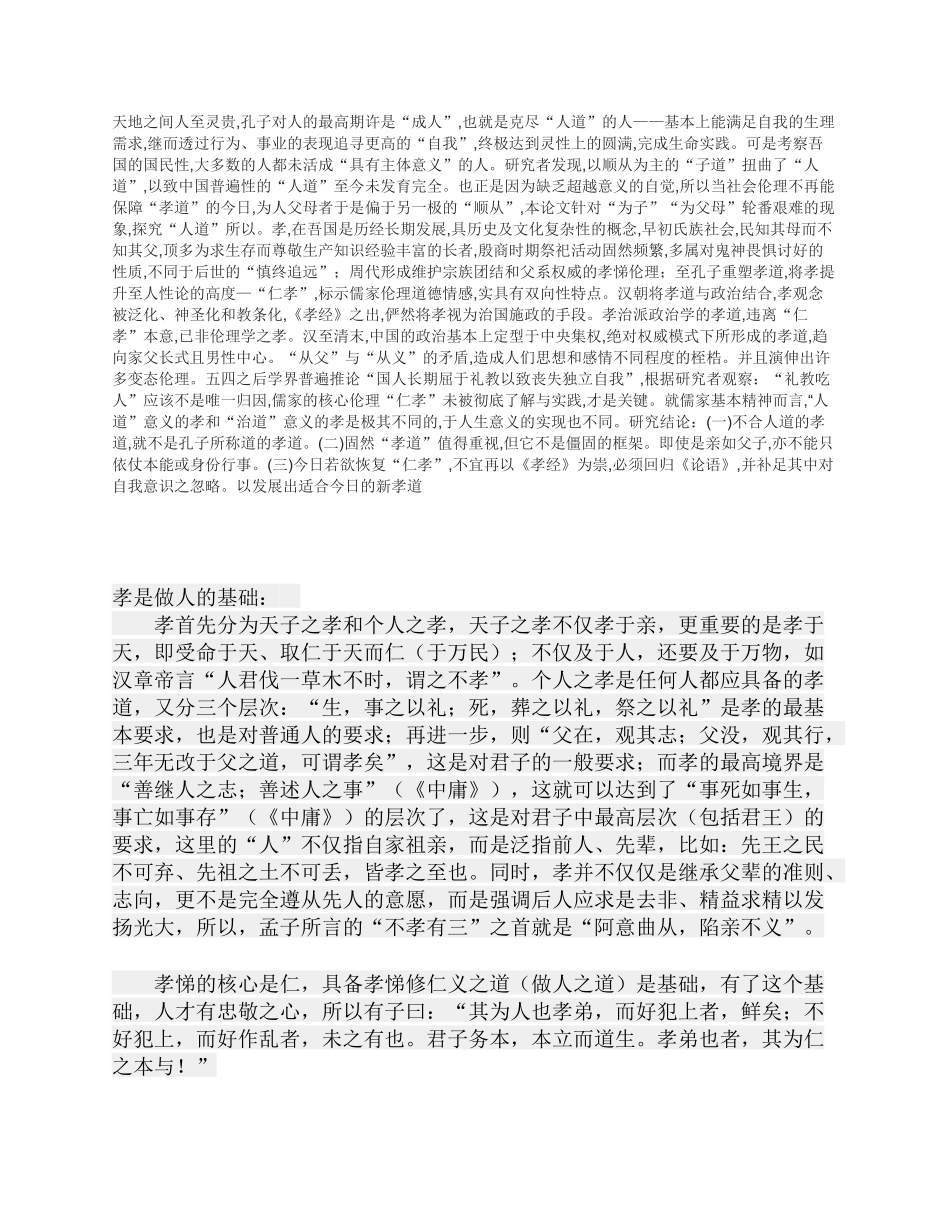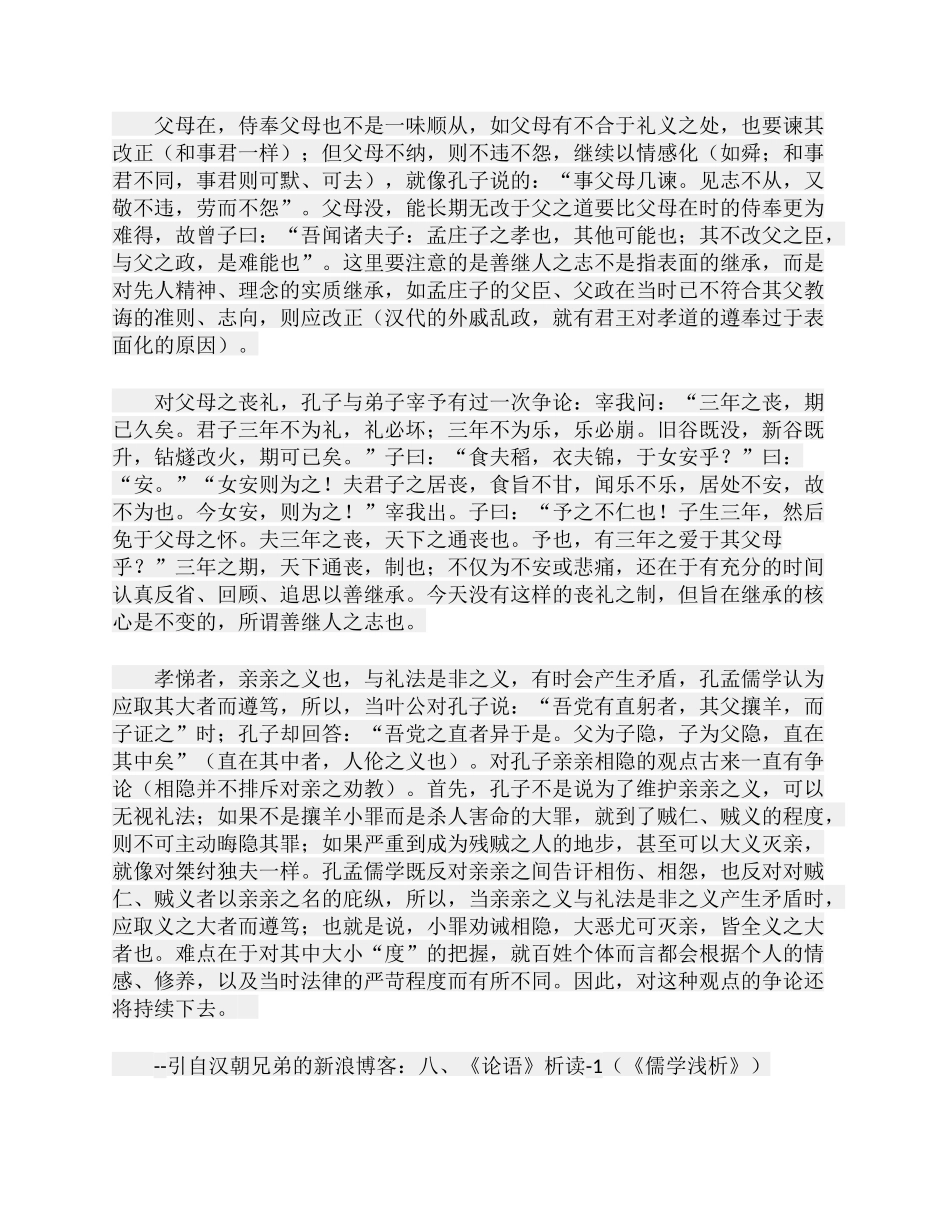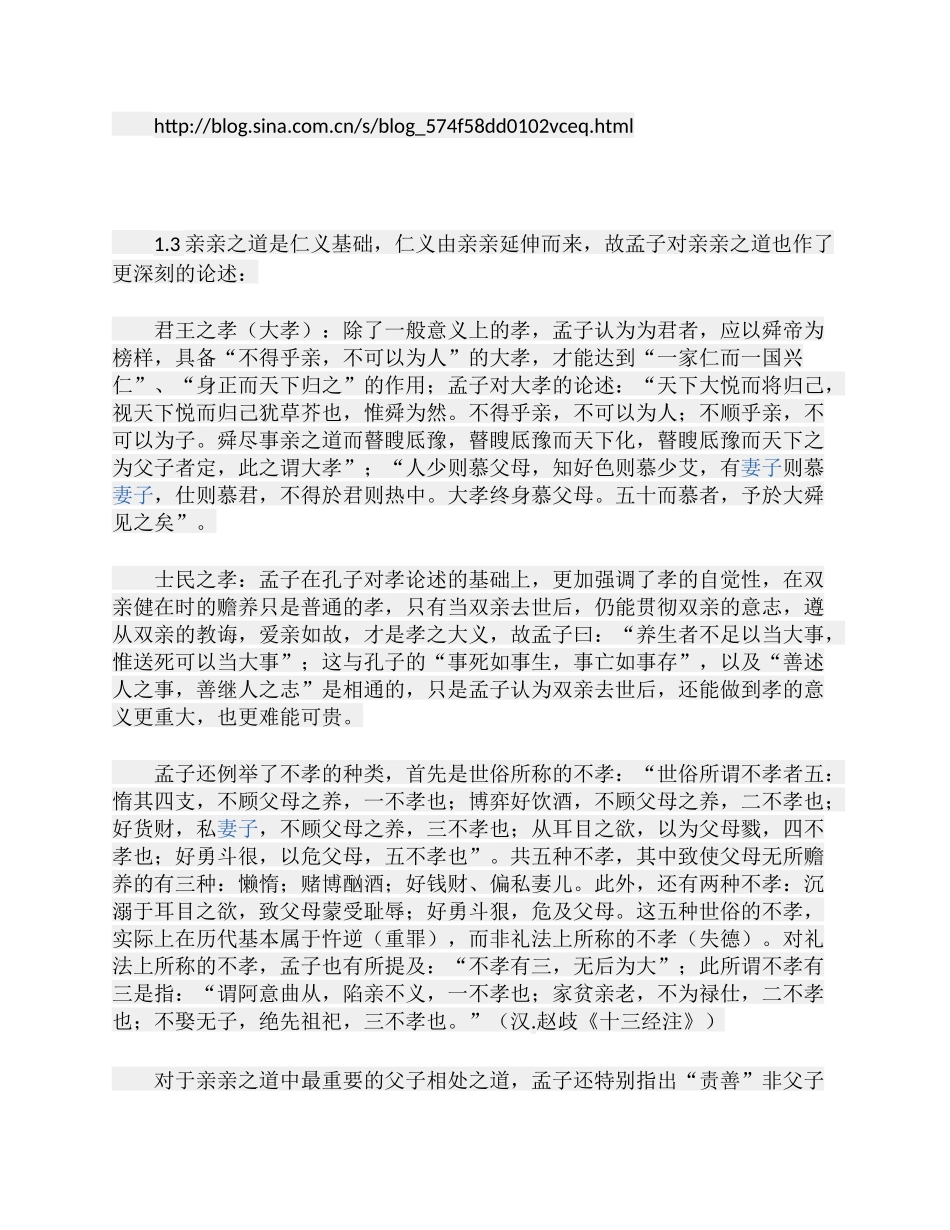天地之间人至灵贵,孔子对人的最高期许是“成人”,也就是克尽“人道”的人——基本上能满足自我的生理需求,继而透过行为、事业的表现追寻更高的“自我”,终极达到灵性上的圆满,完成生命实践。可是考察吾国的国民性,大多数的人都未活成“具有主体意义”的人。研究者发现,以顺从为主的“子道”扭曲了“人道”,以致中国普遍性的“人道”至今未发育完全。也正是因为缺乏超越意义的自觉,所以当社会伦理不再能保障“孝道”的今日,为人父母者于是偏于另一极的“顺从”,本论文针对“为子”“为父母”轮番艰难的现象,探究“人道”所以。孝,在吾国是历经长期发展,具历史及文化复杂性的概念,早初氏族社会,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顶多为求生存而尊敬生产知识经验丰富的长者,殷商时期祭祀活动固然频繁,多属对鬼神畏惧讨好的性质,不同于后世的“慎终追远”;周代形成维护宗族团结和父系权威的孝悌伦理;至孔子重塑孝道,将孝提升至人性论的高度—“仁孝”,标示儒家伦理道德情感,实具有双向性特点。汉朝将孝道与政治结合,孝观念被泛化、神圣化和教条化,《孝经》之出,俨然将孝视为治国施政的手段。孝治派政治学的孝道,违离“仁孝”本意,已非伦理学之孝。汉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基本上定型于中央集权,绝对权威模式下所形成的孝道,趋向家父长式且男性中心。“从父”与“从义”的矛盾,造成人们思想和感情不同程度的桎梏。并且演伸出许多变态伦理。五四之后学界普遍推论“国人长期屈于礼教以致丧失独立自我”,根据研究者观察:“礼教吃人”应该不是唯一归因,儒家的核心伦理“仁孝”未被彻底了解与实践,才是关键。就儒家基本精神而言,“人道”意义的孝和“治道”意义的孝是极其不同的,于人生意义的实现也不同。研究结论:(一)不合人道的孝道,就不是孔子所称道的孝道。(二)固然“孝道”值得重视,但它不是僵固的框架。即使是亲如父子,亦不能只依仗本能或身份行事。(三)今日若欲恢复“仁孝”,不宜再以《孝经》为崇,必须回归《论语》,并补足其中对自我意识之忽略。以发展出适合今日的新孝道孝是做人的基础:孝首先分为天子之孝和个人之孝,天子之孝不仅孝于亲,更重要的是孝于天,即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于万民);不仅及于人,还要及于万物,如汉章帝言“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个人之孝是任何人都应具备的孝道,又分三个层次:“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孝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再进一步,则“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对君子的一般要求;而孝的最高境界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这就可以达到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的层次了,这是对君子中最高层次(包括君王)的要求,这里的“人”不仅指自家祖亲,而是泛指前人、先辈,比如:先王之民不可弃、先祖之土不可丢,皆孝之至也。同时,孝并不仅仅是继承父辈的准则、志向,更不是完全遵从先人的意愿,而是强调后人应求是去非、精益求精以发扬光大,所以,孟子所言的“不孝有三”之首就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孝悌的核心是仁,具备孝悌修仁义之道(做人之道)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人才有忠敬之心,所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父母在,侍奉父母也不是一味顺从,如父母有不合于礼义之处,也要谏其改正(和事君一样);但父母不纳,则不违不怨,继续以情感化(如舜;和事君不同,事君则可默、可去),就像孔子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没,能长期无改于父之道要比父母在时的侍奉更为难得,故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这里要注意的是善继人之志不是指表面的继承,而是对先人精神、理念的实质继承,如孟庄子的父臣、父政在当时已不符合其父教诲的准则、志向,则应改正(汉代的外戚乱政,就有君王对孝道的遵奉过于表面化的原因)。对父母之丧礼,孔子与弟子宰予有过一次争论: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