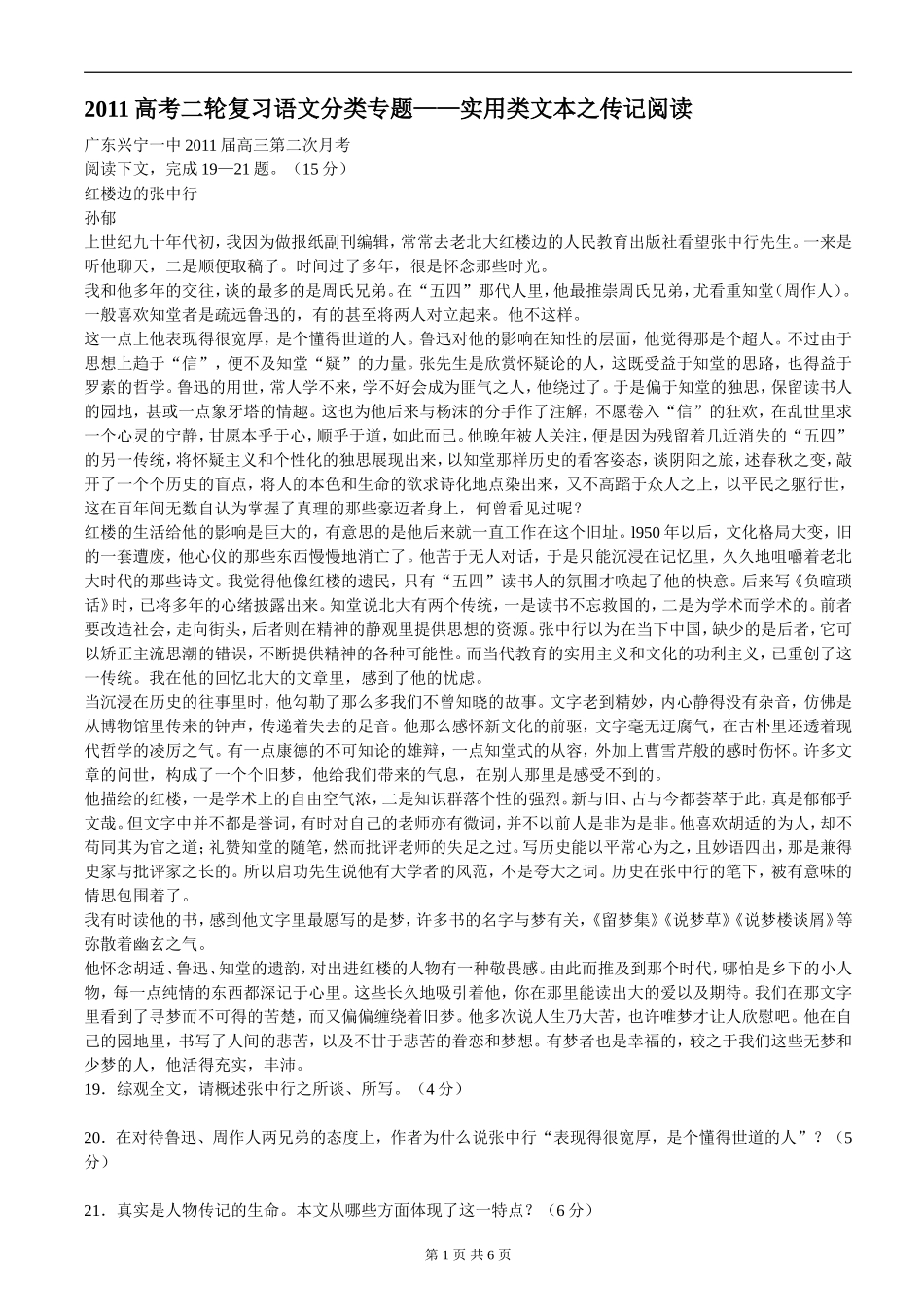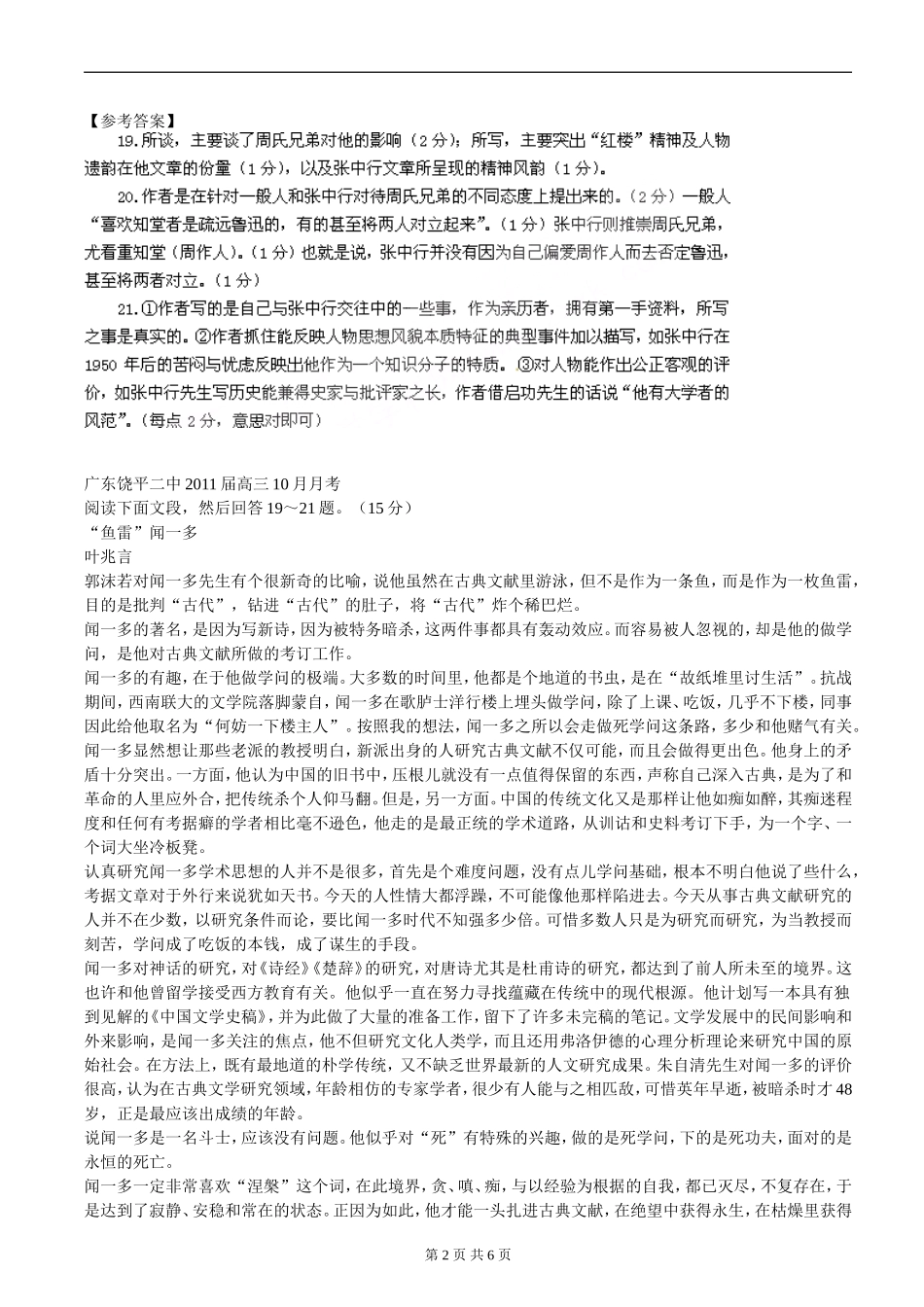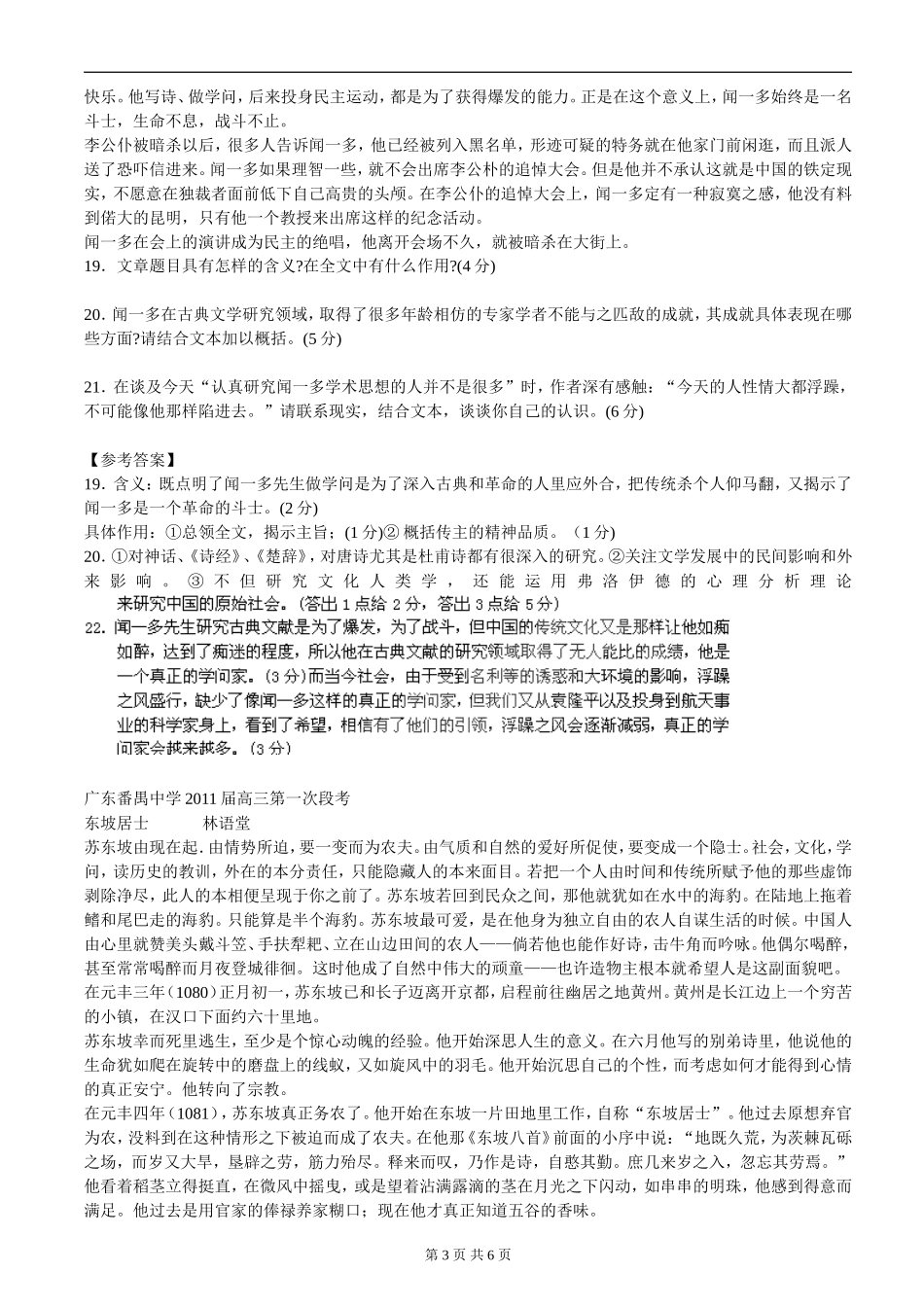2011 高考二轮复习语文分类专题——实用类文本之传记阅读广东兴宁一中 2011 届高三第二次月考阅读下文,完成 19—21 题。(15 分)红楼边的张中行孙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因为做报纸副刊编辑,常常去老北大红楼边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看望张中行先生。一来是听他聊天,二是顺便取稿子。时间过了多年,很是怀念那些时光。我和他多年的交往,谈的最多的是周氏兄弟。在“五四”那代人里,他最推崇周氏兄弟,尤看重知堂(周作人)。一般喜欢知堂者是疏远鲁迅的,有的甚至将两人对立起来。他不这样。这一点上他表现得很宽厚,是个懂得世道的人。鲁迅对他的影响在知性的层面,他觉得那是个超人。不过由于思想上趋于“信”,便不及知堂“疑”的力量。张先生是欣赏怀疑论的人,这既受益于知堂的思路,也得益于罗素的哲学。鲁迅的用世,常人学不来,学不好会成为匪气之人,他绕过了。于是偏于知堂的独思,保留读书人的园地,甚或一点象牙塔的情趣。这也为他后来与杨沫的分手作了注解,不愿卷入“信”的狂欢,在乱世里求一个心灵的宁静,甘愿本乎于心,顺乎于道,如此而已。他晚年被人关注,便是因为残留着几近消失的“五四”的另一传统,将怀疑主义和个性化的独思展现出来,以知堂那样历史的看客姿态,谈阴阳之旅,述春秋之变,敲开了一个个历史的盲点,将人的本色和生命的欲求诗化地点染出来,又不高蹈于众人之上,以平民之躯行世,这在百年间无数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那些豪迈者身上,何曾看见过呢?红楼的生活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就一直工作在这个旧址。l950 年以后,文化格局大变,旧的一套遭废,他心仪的那些东西慢慢地消亡了。他苦于无人对话,于是只能沉浸在记忆里,久久地咀嚼着老北大时代的那些诗文。我觉得他像红楼的遗民,只有“五四”读书人的氛围才唤起了他的快意。后来写《负暄琐话》时,已将多年的心绪披露出来。知堂说北大有两个传统,一是读书不忘救国的,二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前者要改造社会,走向街头,后者则在精神的静观里提供思想的资源。张中行以为在当下中国,缺少的是后者,它可以矫正主流思潮的错误,不断提供精神的各种可能性。而当代教育的实用主义和文化的功利主义,已重创了这一传统。我在他的回忆北大的文章里,感到了他的忧虑。当沉浸在历史的往事里时,他勾勒了那么多我们不曾知晓的故事。文字老到精妙,内心静得没有杂音,仿佛是从博物馆里传来的钟声,传递着失去的足音。他那么感怀新文化的前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