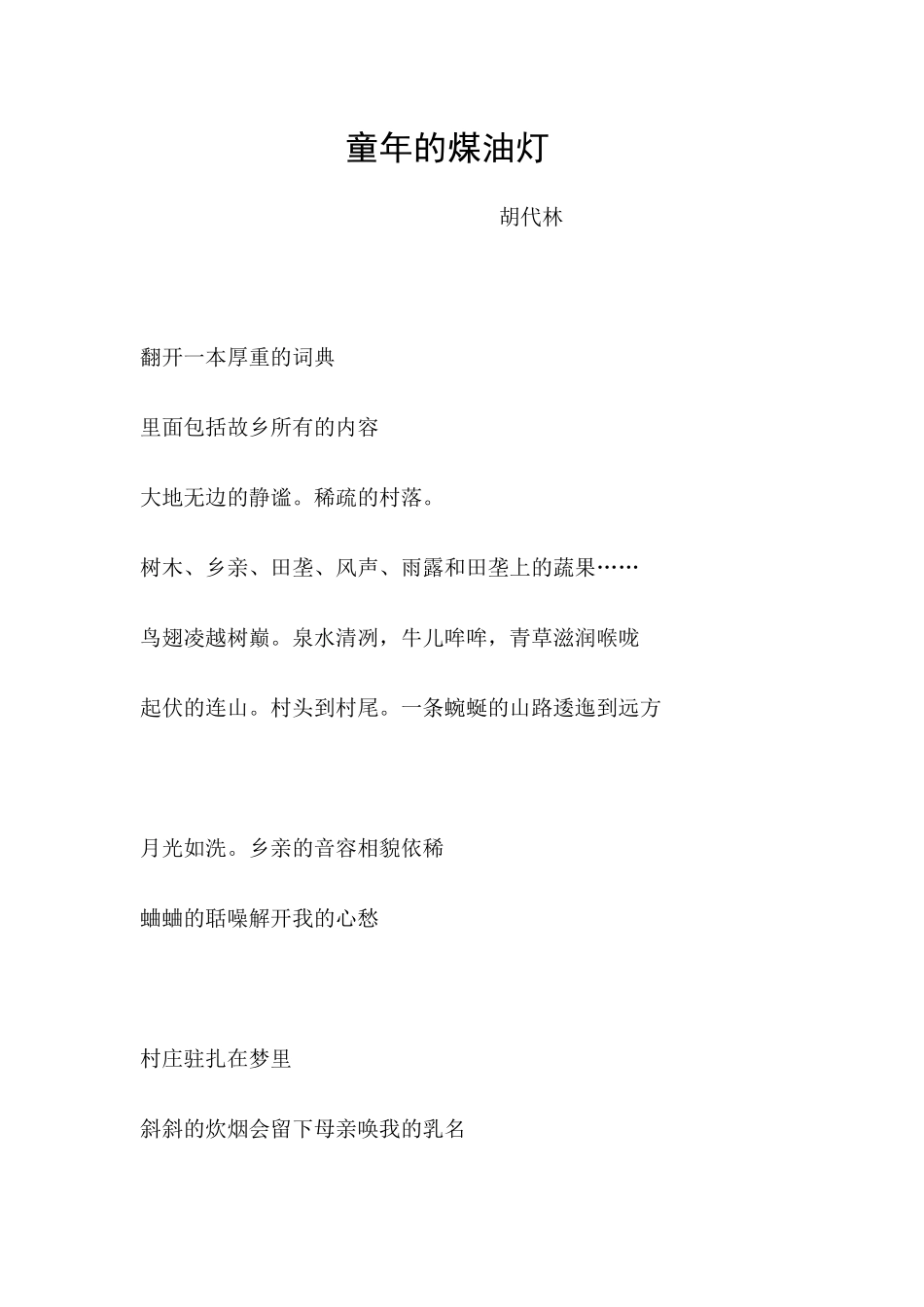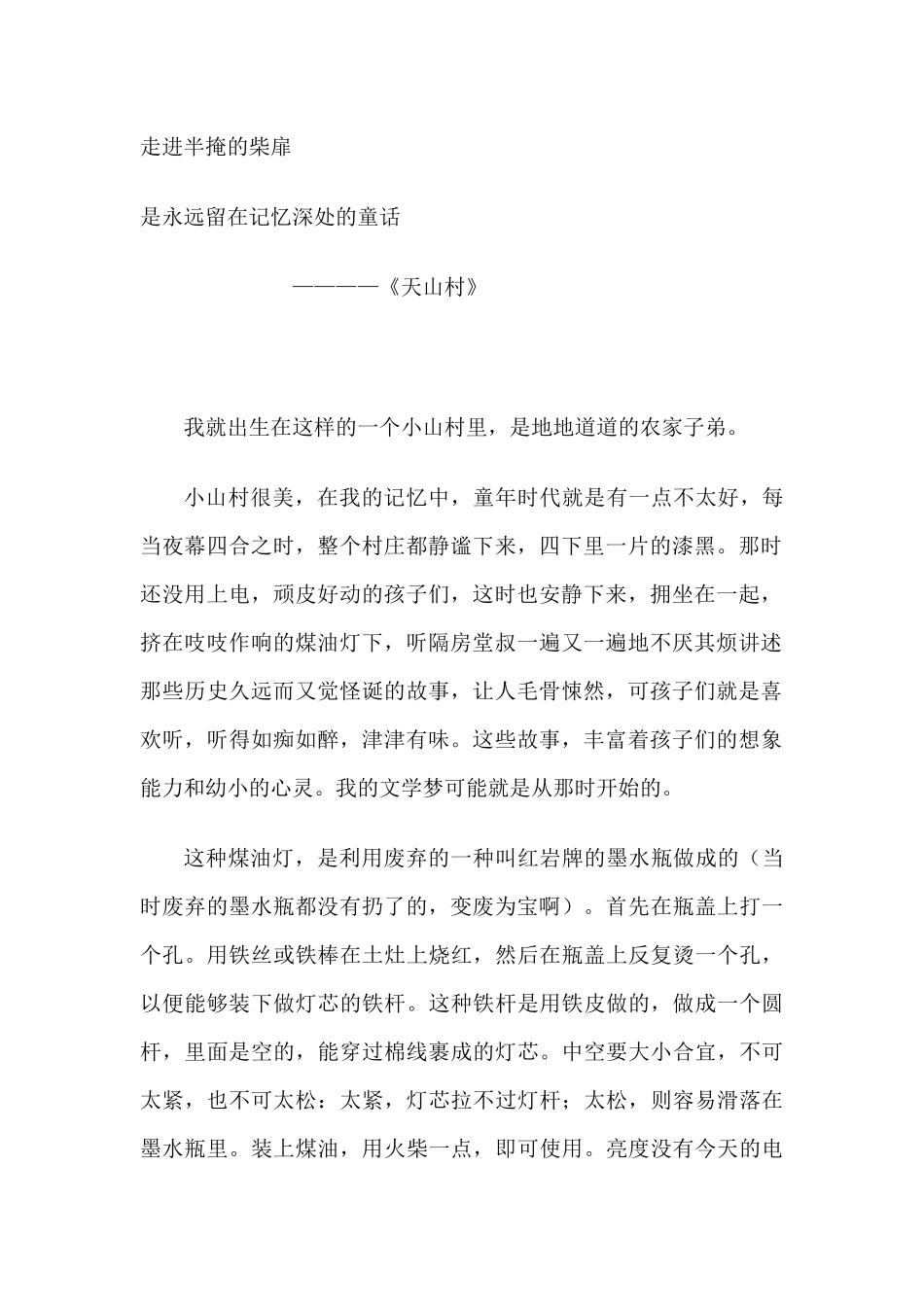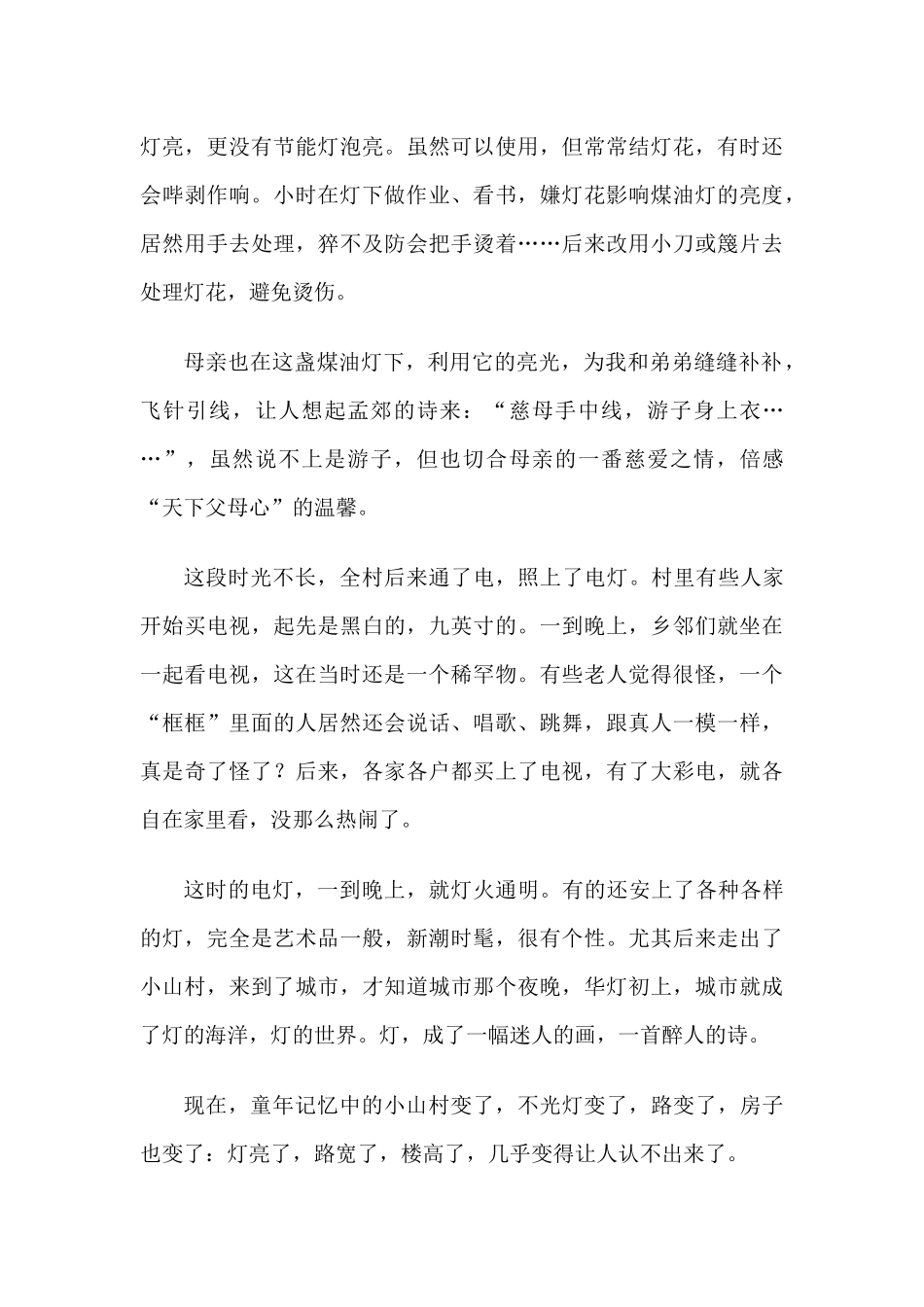童年的煤油灯胡代林 翻开一本厚重的词典里面包括故乡所有的内容大地无边的静谧。稀疏的村落。树木、乡亲、田垄、风声、雨露和田垄上的蔬果……鸟翅凌越树巅。泉水清冽,牛儿哞哞,青草滋润喉咙起伏的连山。村头到村尾。一条蜿蜒的山路逶迤到远方 月光如洗。乡亲的音容相貌依稀蛐蛐的聒噪解开我的心愁 村庄驻扎在梦里斜斜的炊烟会留下母亲唤我的乳名走进半掩的柴扉是永远留在记忆深处的童话 ————《天山村》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小山村很美,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代就是有一点不太好,每当夜幕四合之时,整个村庄都静谧下来,四下里一片的漆黑。那时还没用上电,顽皮好动的孩子们,这时也安静下来,拥坐在一起,挤在吱吱作响的煤油灯下,听隔房堂叔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讲述那些历史久远而又觉怪诞的故事,让人毛骨悚然,可孩子们就是喜欢听,听得如痴如醉,津津有味。这些故事,丰富着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和幼小的心灵。我的文学梦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种煤油灯,是利用废弃的一种叫红岩牌的墨水瓶做成的(当时废弃的墨水瓶都没有扔了的,变废为宝啊)。首先在瓶盖上打一个孔。用铁丝或铁棒在土灶上烧红,然后在瓶盖上反复烫一个孔,以便能够装下做灯芯的铁杆。这种铁杆是用铁皮做的,做成一个圆杆,里面是空的,能穿过棉线裹成的灯芯。中空要大小合宜,不可太紧,也不可太松:太紧,灯芯拉不过灯杆;太松,则容易滑落在墨水瓶里。装上煤油,用火柴一点,即可使用。亮度没有今天的电灯亮,更没有节能灯泡亮。虽然可以使用,但常常结灯花,有时还会哔剥作响。小时在灯下做作业、看书,嫌灯花影响煤油灯的亮度,居然用手去处理,猝不及防会把手烫着……后来改用小刀或篾片去处理灯花,避免烫伤。母亲也在这盏煤油灯下,利用它的亮光,为我和弟弟缝缝补补,飞针引线,让人想起孟郊的诗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虽然说不上是游子,但也切合母亲的一番慈爱之情,倍感“天下父母心”的温馨。这段时光不长,全村后来通了电,照上了电灯。村里有些人家开始买电视,起先是黑白的,九英寸的。一到晚上,乡邻们就坐在一起看电视,这在当时还是一个稀罕物。有些老人觉得很怪,一个“框框”里面的人居然还会说话、唱歌、跳舞,跟真人一模一样,真是奇了怪了?后来,各家各户都买上了电视,有了大彩电,就各自在家里看,没那么热闹了。这时的电灯,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有的还安上了各种各样的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