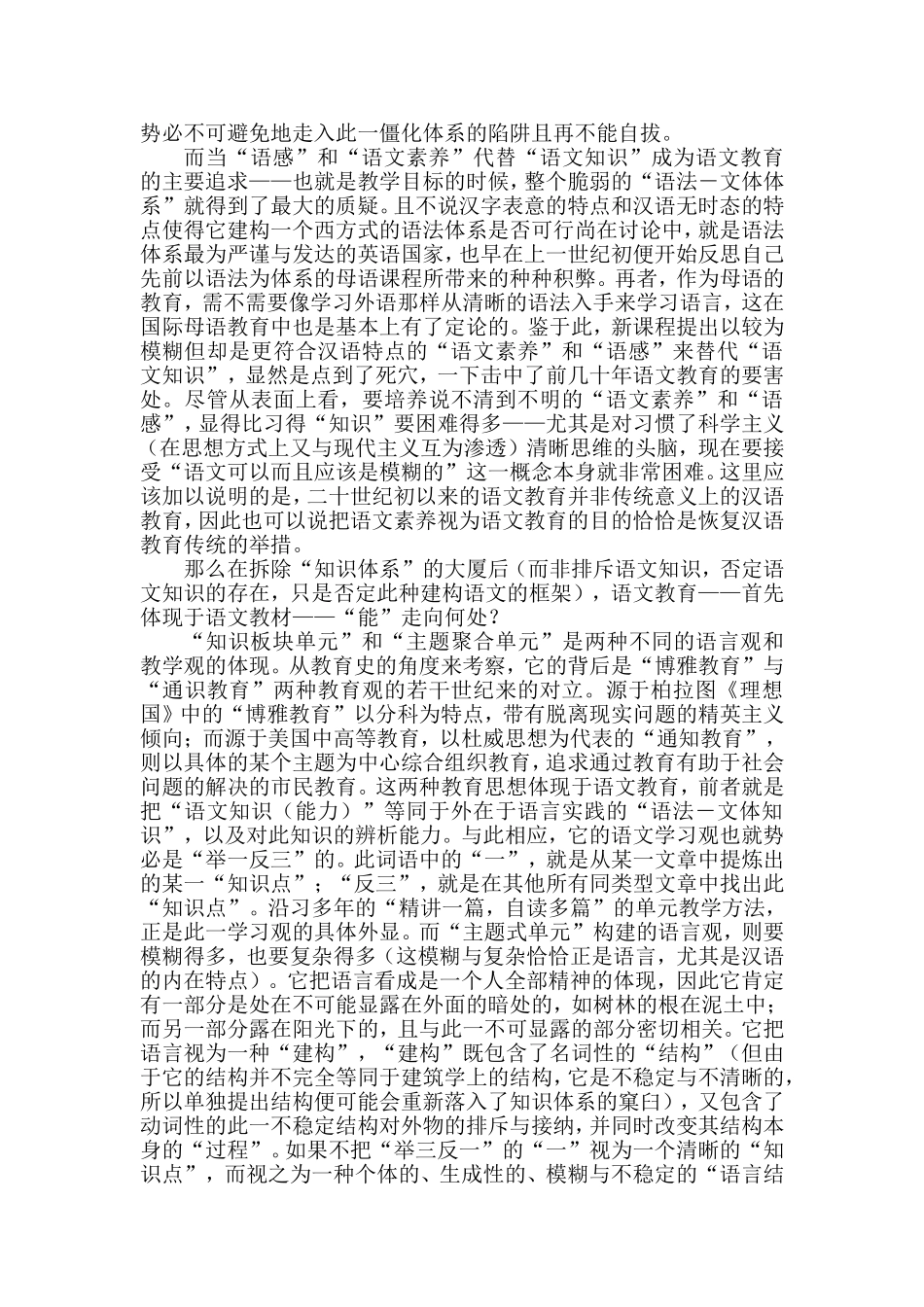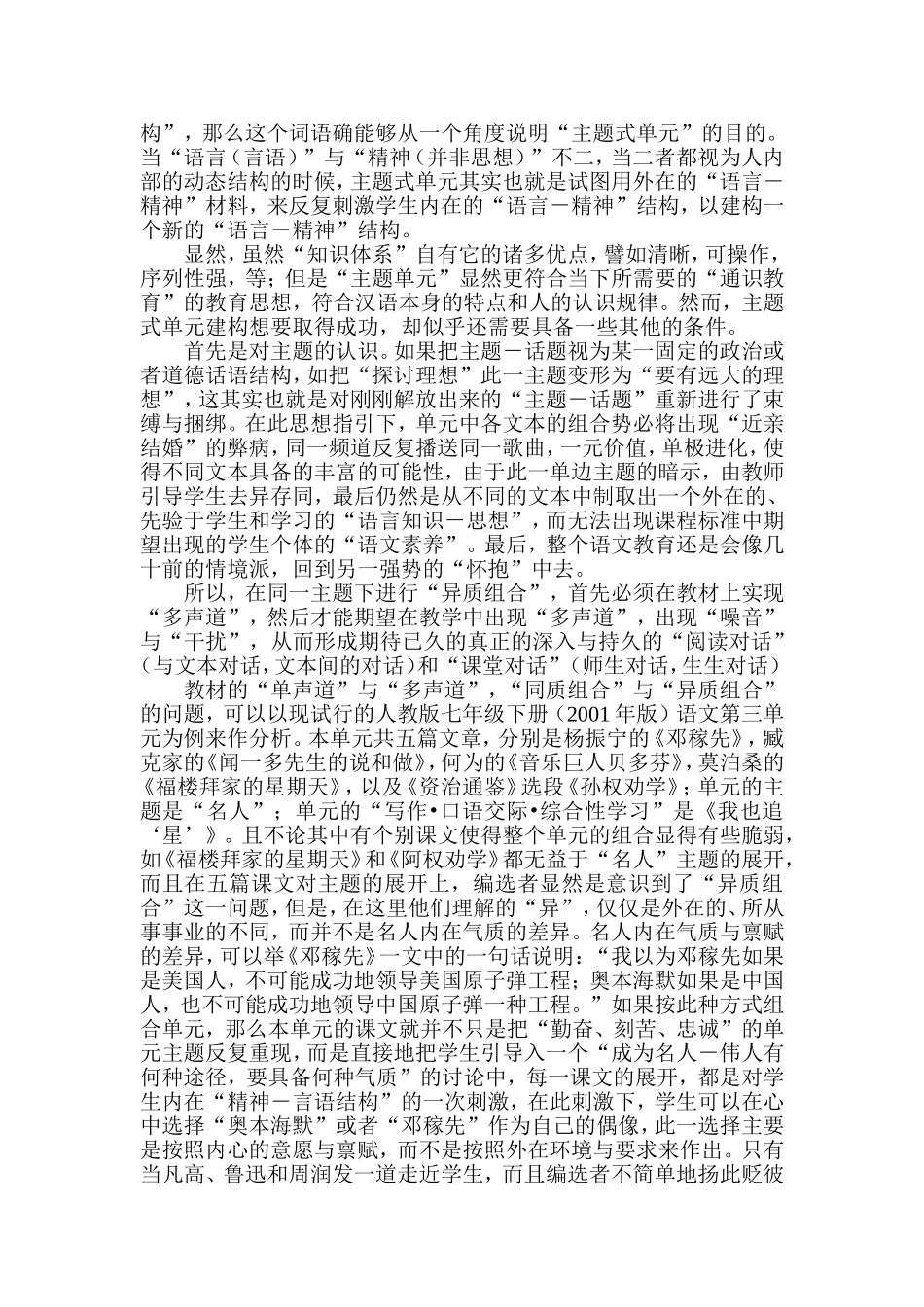从“知识体系”到“主题单元”旧大纲与新课程体现在教材编选上的差异,是单元的组成方式。在旧大纲中,整个语文教育目标根据“语法-文体体系”(文体也可称之为语法体系的附属,因为它在教材中是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来作主要的划分依据的)分解为一整套前后串联、详细可索的知识点,每一单元就是具体一块知识点的落实,如“说明的顺序和方法”,“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议论的方式和方法”等。而这些知识块又是前后呼应承接的,各自在更大的知识版块中形成一个体系的某一特定分枝。如在议论文版块中,一般分为“论点和论据”,“议论的方式和方法”,“议论文语言的严密性”等前后遥相呼应的几个单元(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螺旋式地学习被视为高过长期地单块专题知识的学习,所以在议论文单元间往往穿插其他文体的一些单元)。以这种“知识体系单元”建构课程的背后,是科学主义式的教育哲学,究其根源,在教育史上可追溯到约翰•洛克的白板说,集中体现在泰勒和博比特的科学性课程观中。这种教育思想其实是笛卡尔和牛顿的科学世界观对教育的影响(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它认为知识就是一系列清晰不模糊、朝向某个明确的方向的阶梯(知识即科学,即理性和反观式的认识事物方式,即对感知觉、感悟作精确化外显化的认识。知识即认识的明确化和不断的分解、细化和定格。认识的精确化是其优点,但缺点是太强调分析,将完整的事物分解为彼此隔离的部分来认识,容易忽视整体把握-而整体把握又是最紧要的认识方式,并且这种认识是抽象的认识,缺少生动形象和情趣。而感悟式的认识事物方法则与之相反。),而学习就是按照此阶梯循序渐进地习得知识(后来又把名词性的“知识”用动词来描述,并冠之以“能力”的新名称,但其本质并无变化)。为了照顾思想教育的需要,在这一知识谱系上,又被断断续续地加上思想教育的目标,如把爱国精神放在某一记叙或者小说单元中,把科学精神放在某一说明文单元中;这样,具体每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也就同时含有了知识、能力(从文本中找出此知识的能力而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情感与思想等几个方面。至于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其实并不能这样被规划与操练的困境,则只能靠提倡老师要提高“教学艺术”这四个字来弥补了。把这种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在至今盛行不衰的几个词语上:“知识树”,“一课一得,得得相联”,“目标教学法”。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情境教育法”,或者“情感派”,原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