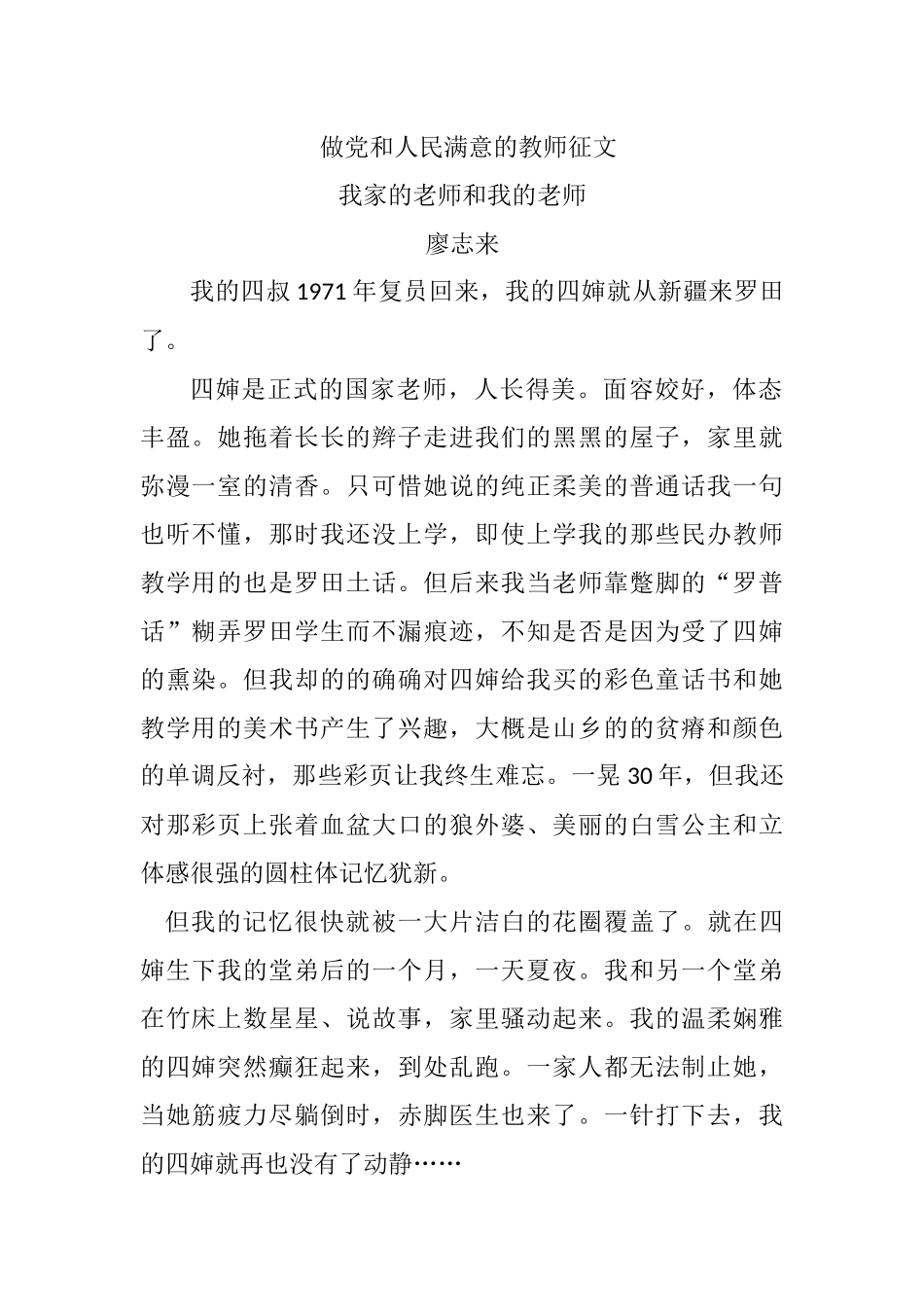做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征文 我家的老师和我的老师廖志来我的四叔 1971 年复员回来,我的四婶就从新疆来罗田了。四婶是正式的国家老师,人长得美。面容姣好,体态丰盈。她拖着长长的辫子走进我们的黑黑的屋子,家里就弥漫一室的清香。只可惜她说的纯正柔美的普通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那时我还没上学,即使上学我的那些民办教师教学用的也是罗田土话。但后来我当老师靠蹩脚的“罗普话”糊弄罗田学生而不漏痕迹,不知是否是因为受了四婶的熏染。但我却的的确确对四婶给我买的彩色童话书和她教学用的美术书产生了兴趣,大概是山乡的的贫瘠和颜色的单调反衬,那些彩页让我终生难忘。一晃 30 年,但我还对那彩页上张着血盆大口的狼外婆、美丽的白雪公主和立体感很强的圆柱体记忆犹新。但我的记忆很快就被一大片洁白的花圈覆盖了。就在四婶生下我的堂弟后的一个月,一天夏夜。我和另一个堂弟在竹床上数星星、说故事,家里骚动起来。我的温柔娴雅的四婶突然癫狂起来,到处乱跑。一家人都无法制止她,当她筋疲力尽躺倒时,赤脚医生也来了。一针打下去,我的四婶就再也没有了动静……不久,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送来大片大片的洁白的花圈,排满了家门前的竹林。我竟然感觉那是那么美丽与圣洁……时光把我的亲人越带越远,而她的音容和风范却在我的心间永驻,让我反复追问:没有教我一个字的四婶为何让我难以忘怀?不知是她的美好形象,还是她带来的文化因子唐突进入我混沌未开世界。我至今难以明白,驽钝如我者居然能读出书来甚至当上语文教师,可能与这些无形的启蒙有关!而把我引进学堂的却是我的六叔。六叔是民办老师,高中毕业就回村里教书。那时的民办老师身份其实就是农民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别人耍的是大锄,他们耍的是粉笔;别人放牧的是牛羊,他们放牧的是我们这些野孩子;别人劳作大约是看着日头计时,他们却能就着钟表按课表工作别人从地里刨食,而他们却在黑板上耕种。而能显示他们好像是文化人身份的就是那一两件运动衫或、白衬衣或是土裁缝仿制的中山装,而最直标志就是那别在上衣口袋上的简易钢笔。如果谁能狠下心来用一年的工资买上一块上海宝石花的手表,那简直就是乡村里的贵族。我的叔叔却是那种贫穷而又执着教书的老师,他一年的工资大致相当于我四婶一个月的工资。六叔教书不到二十岁,干净、清秀,却在我家没有他的居室。学校是他上班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个家。工作了一天他回家吃晚饭,晚饭迟了,就由我和奶奶点着油灯去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