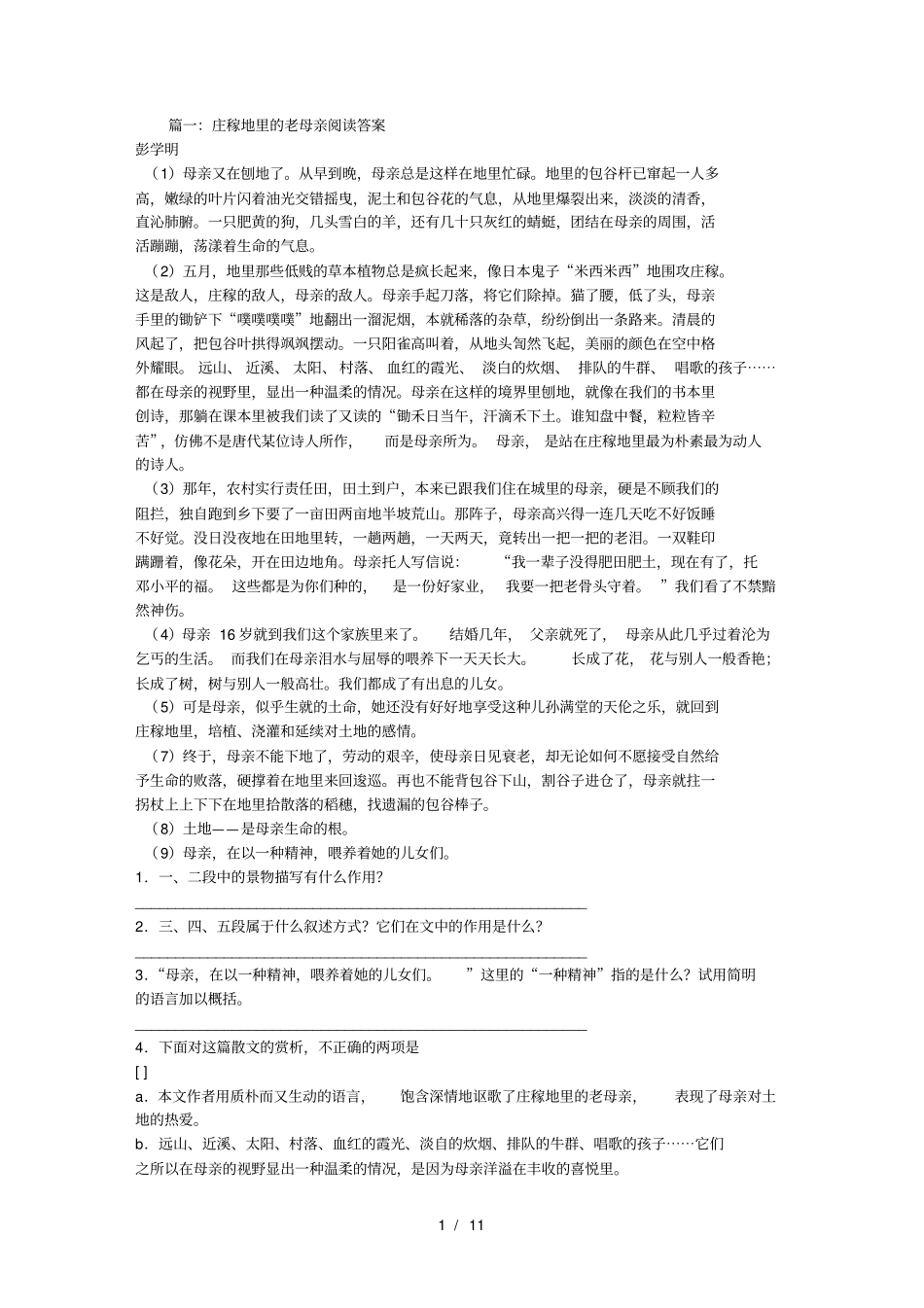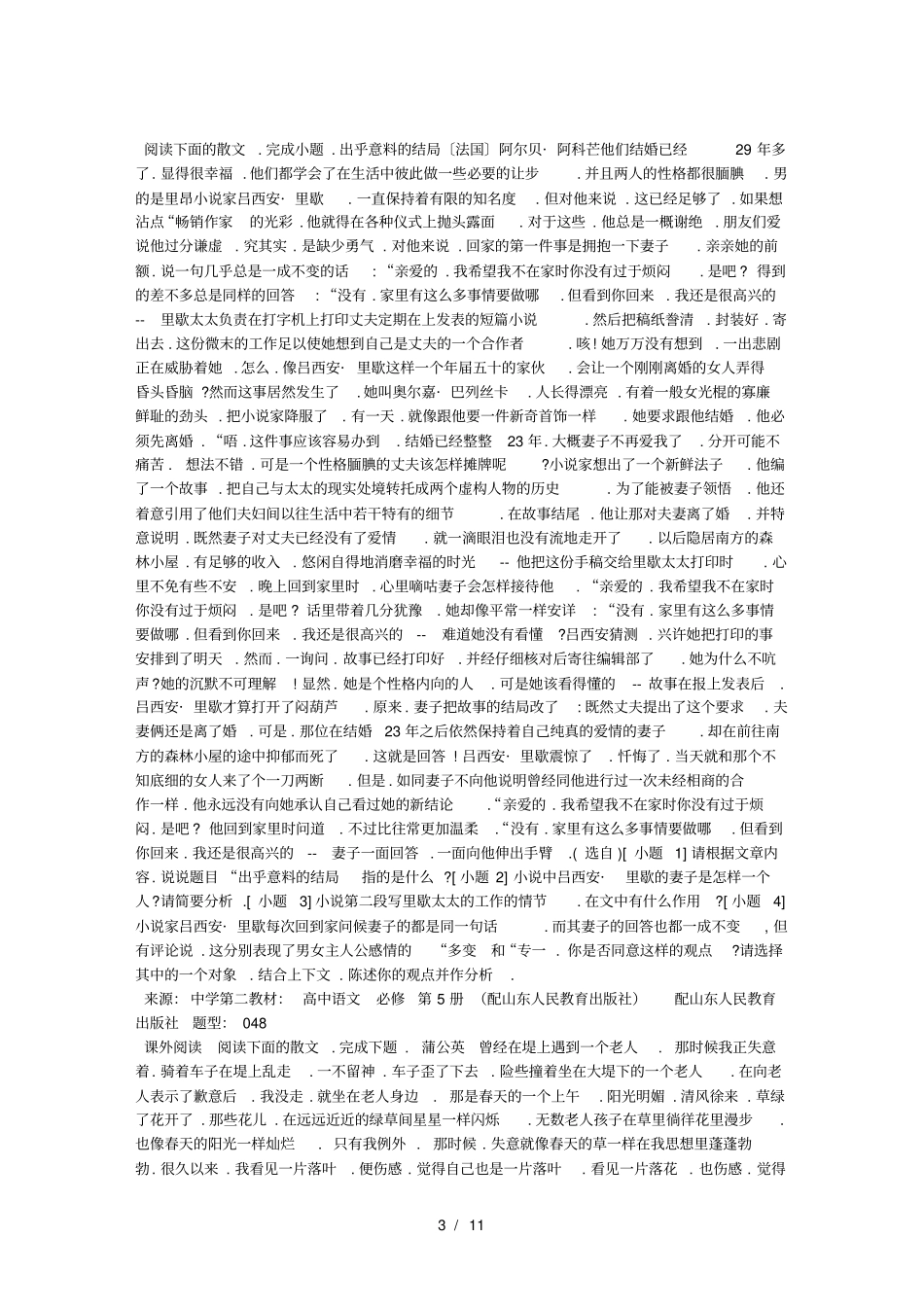1 / 11 篇一:庄稼地里的老母亲阅读答案彭学明(1)母亲又在刨地了。从早到晚,母亲总是这样在地里忙碌。地里的包谷杆已窜起一人多高,嫩绿的叶片闪着油光交错摇曳,泥土和包谷花的气息,从地里爆裂出来,淡淡的清香,直沁肺腑。一只肥黄的狗,几头雪白的羊,还有几十只灰红的蜻蜓,团结在母亲的周围,活活蹦蹦,荡漾着生命的气息。(2)五月,地里那些低贱的草本植物总是疯长起来,像日本鬼子“米西米西”地围攻庄稼。这是敌人,庄稼的敌人,母亲的敌人。母亲手起刀落,将它们除掉。猫了腰,低了头,母亲手里的锄铲下“噗噗噗噗”地翻出一溜泥烟,本就稀落的杂草,纷纷倒出一条路来。清晨的风起了,把包谷叶拱得飒飒摆动。一只阳雀高叫着,从地头訇然飞起,美丽的颜色在空中格外耀眼。 远山、 近溪、 太阳、 村落、 血红的霞光、 淡白的炊烟、 排队的牛群、 唱歌的孩子⋯⋯都在母亲的视野里,显出一种温柔的情况。母亲在这样的境界里刨地,就像在我们的书本里创诗,那躺在课本里被我们读了又读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仿佛不是唐代某位诗人所作,而是母亲所为。 母亲, 是站在庄稼地里最为朴素最为动人的诗人。(3)那年,农村实行责任田,田土到户,本来已跟我们住在城里的母亲,硬是不顾我们的阻拦,独自跑到乡下要了一亩田两亩地半坡荒山。那阵子,母亲高兴得一连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转,一趟两趟,一天两天,竟转出一把一把的老泪。一双鞋印蹒跚着,像花朵,开在田边地角。母亲托人写信说:“我一辈子没得肥田肥土,现在有了,托邓小平的福。 这些都是为你们种的,是一份好家业, 我要一把老骨头守着。 ”我们看了不禁黯然神伤。(4)母亲 16 岁就到我们这个家族里来了。结婚几年, 父亲就死了, 母亲从此几乎过着沦为乞丐的生活。 而我们在母亲泪水与屈辱的喂养下一天天长大。长成了花, 花与别人一般香艳;长成了树,树与别人一般高壮。我们都成了有出息的儿女。(5)可是母亲,似乎生就的土命,她还没有好好地享受这种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就回到庄稼地里,培植、浇灌和延续对土地的感情。(7)终于,母亲不能下地了,劳动的艰辛,使母亲日见衰老,却无论如何不愿接受自然给予生命的败落,硬撑着在地里来回逡巡。再也不能背包谷下山,割谷子进仓了,母亲就拄一拐杖上上下下在地里拾散落的稻穗,找遗漏的包谷棒子。(8)土地——是母亲生命的根。(9)母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