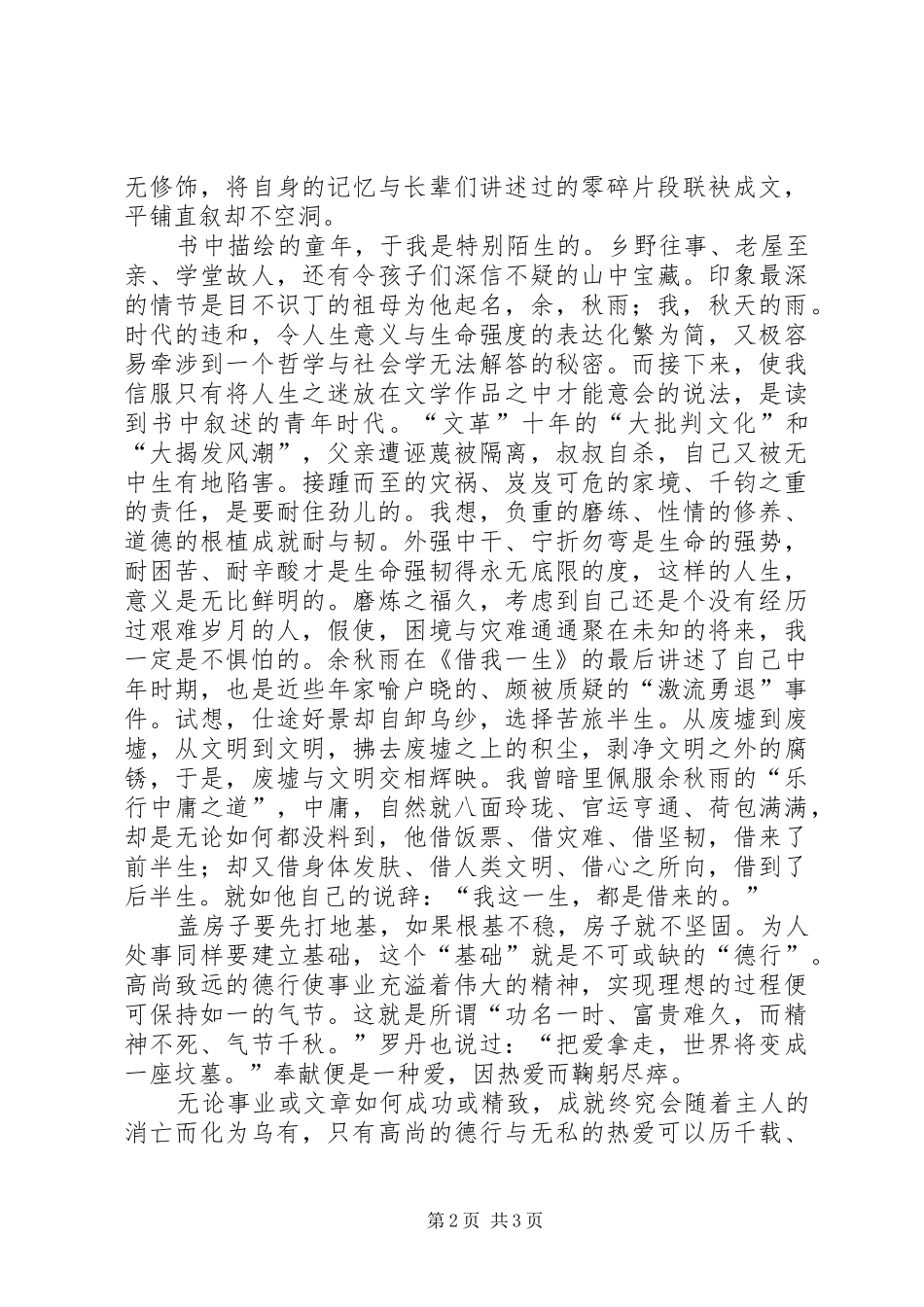读《借我一生》有感以德为本以心为宗在中国当代的学术界,实在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余秋雨这么倍受争议的学者。关于他的任何一种美誉对面,必定会活跃着一种针锋相对的诅咒。当他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各地的文化讲坛上时,或者为了“开启民智”担任公共知识宣传大使时,有人将他恭维成“文化精英”,就必定有人不屑一顾地说他口沫横飞、一个劲儿地跟那儿自我陶醉。面对十面质疑、八方诽谤,他可以面色如常地坐镇cctv评委席;臵身媒体与坊间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他也可以没有只字辩解。当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出版,被诸君质问该书是否充满了一种辩解时,他借鲁迅名言回应说:“一个人到自我辩解的时候,你已经是非常地吃亏了。”《借我一生》的特别之处不单体现在创作背景上,而是无论体裁、题材还是措辞风格都与其以往的作品有别。书里面写道:“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的确,对于那些因余秋雨而“口水切磋”的众人,也未必知悉这部名为《借我一生》的记忆文学作品究竟会成为学术界的“泉眼”还是“死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余秋雨携《借我一生》淡出,留给众人的,除了无尽的传言、风议、舌战、辩论,想必终是一卷“余氏笔触”的道德心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修身种德。道德需要意志长久磨练,需要静心思考体味,需要于生活中点滴地修炼。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学会去热爱。热爱弥足珍贵的生存之地,热爱所见、所闻、所事之岗,热爱心之所向。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已本然。余秋雨的《借我一生》是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书中涉及了诸多关于家族不为人知的经历。六十年代的动乱无序,充斥着丧心病狂的热情与歇斯底里的检讨,还有理智。通篇,措辞无刁钻、语法第1页共3页无修饰,将自身的记忆与长辈们讲述过的零碎片段联袂成文,平铺直叙却不空洞。书中描绘的童年,于我是特别陌生的。乡野往事、老屋至亲、学堂故人,还有令孩子们深信不疑的山中宝藏。印象最深的情节是目不识丁的祖母为他起名,余,秋雨;我,秋天的雨。时代的违和,令人生意义与生命强度的表达化繁为简,又极容易牵涉到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无法解答的秘密。而接下来,使我信服只有将人生之迷放在文学作品之中才能意会的说法,是读到书中叙述的青年时代。“文革”十年的“大批判文化”和“大揭发风潮”,父亲遭诬蔑被隔离,叔叔自杀,自己又被无中生有地陷害。接踵而至的灾祸、岌岌可危的家境、千钧之重的责任,是要耐住劲儿的。我想,负重的磨练、性情的修养、道德的根植成就耐与韧。外强中干、宁折勿弯是生命的强势,耐困苦、耐辛酸才是生命强韧得永无底限的度,这样的人生,意义是无比鲜明的。磨炼之福久,考虑到自己还是个没有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人,假使,困境与灾难通通聚在未知的将来,我一定是不惧怕的。余秋雨在《借我一生》的最后讲述了自己中年时期,也是近些年家喻户晓的、颇被质疑的“激流勇退”事件。试想,仕途好景却自卸乌纱,选择苦旅半生。从废墟到废墟,从文明到文明,拂去废墟之上的积尘,剥净文明之外的腐锈,于是,废墟与文明交相辉映。我曾暗里佩服余秋雨的“乐行中庸之道”,中庸,自然就八面玲珑、官运亨通、荷包满满,却是无论如何都没料到,他借饭票、借灾难、借坚韧,借来了前半生;却又借身体发肤、借人类文明、借心之所向,借到了后半生。就如他自己的说辞:“我这一生,都是借来的。”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如果根基不稳,房子就不坚固。为人处事同样要建立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不可或缺的“德行”。高尚致远的德行使事业充溢着伟大的精神,实现理想的过程便可保持如一的气节。这就是所谓“功名一时、富贵难久,而精神不死、气节千秋。”罗丹也说过:“把爱拿走,世界将变成一座坟墓。”奉献便是一种爱,因热爱而鞠躬尽瘁。无论事业或文章如何成功或精致,成就终究会随着主人的消亡而化为乌有,只有高尚的德行与无私的热爱可以历千载、第2页共3页传万代,感化后世、亘古不衰。回想多年之前通宵阅读《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