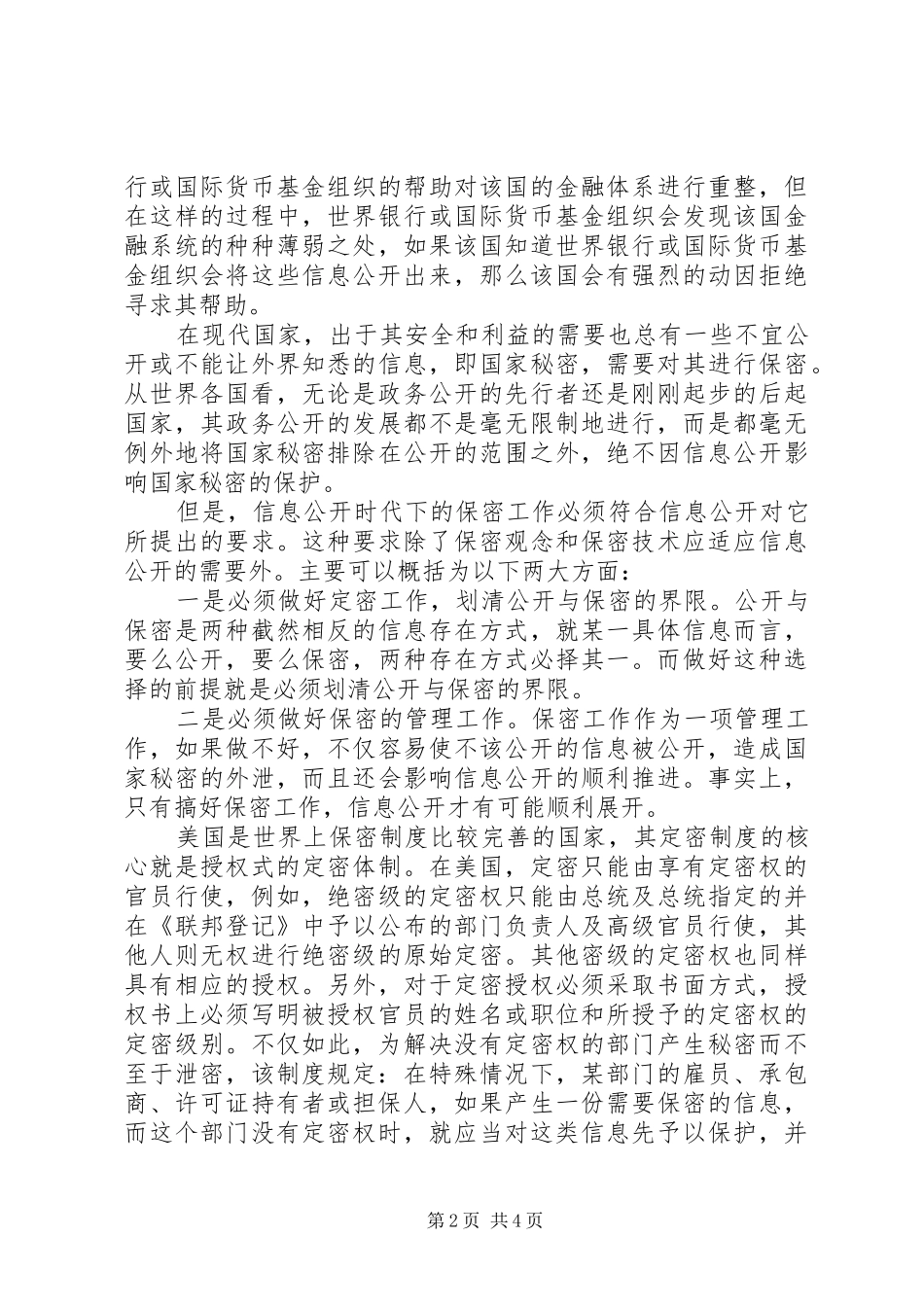信息公开时代的信息保密问题随着透明化、公开化日渐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信息”也成为我们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在金融货币政策领域,政府是否应当秘密行动,有着广泛的争论:政府是否应将自己的工作进展公开。可以允许有什么样的延迟。对细节的公开应该到什么程度。如果市场确信这些信息具有至为重要的价值,难道政府就不应该及时公开这些信息吗。显然,各国政府在自己的运作过程中,并不那么情愿信息公开。尤其是对诸如金融货币政策之类事务的公开讨论可能会使得经济动荡,有时候,信息公开会带来生死攸关的后果。在这里,重要的,并非信息是否公开的问题,而是信息如何公开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和信息公开方式值得借鉴。美联储在例行会议后一段时间,必然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的纪要,这也让市场更加了解作为央行的美联储的思维逻辑和行动方式,很多时候,市场参与者可以准确预测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并且主动做出调整,这实际上降低了调控成本,也加强了政府的权威。实际上,由于信息早晚总要被公开,当下试图将信息密闭起来的程序和做法,在随后的信息披露之后必然会受到公众的质疑。人们一般认为,经济要更加稳定地运行,一定经常性地作一些微调而不是大规模的调整。因此,稳定的信息流将使得经济有可能变得更加稳定。在信息持续公开的情况下,人们不需要再对某一个时段给予特别关注,也可以减少事后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从世界范围看,经济领域的保密不仅增加了总体不稳定性,而且在许多国家,也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成为导致腐败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承认,信息公开确实有一定的限度。例如,政府在履行其行政职责的过程中收集的大量个人的隐私信息(诸如收入状况、健康资料等),这些与个人有关的隐秘信息,构成了信息公开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例外。与以上隐私信息多少有些类似的是机密信息,这些信息的公开会给后续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有的国家会寻求世界银第1页共4页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该国的金融体系进行重整,但在这样的过程中,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发现该国金融系统的种种薄弱之处,如果该国知道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将这些信息公开出来,那么该国会有强烈的动因拒绝寻求其帮助。在现代国家,出于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也总有一些不宜公开或不能让外界知悉的信息,即国家秘密,需要对其进行保密。从世界各国看,无论是政务公开的先行者还是刚刚起步的后起国家,其政务公开的发展都不是毫无限制地进行,而是都毫无例外地将国家秘密排除在公开的范围之外,绝不因信息公开影响国家秘密的保护。但是,信息公开时代下的保密工作必须符合信息公开对它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要求除了保密观念和保密技术应适应信息公开的需要外。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大方面:一是必须做好定密工作,划清公开与保密的界限。公开与保密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信息存在方式,就某一具体信息而言,要么公开,要么保密,两种存在方式必择其一。而做好这种选择的前提就是必须划清公开与保密的界限。二是必须做好保密的管理工作。保密工作作为一项管理工作,如果做不好,不仅容易使不该公开的信息被公开,造成国家秘密的外泄,而且还会影响信息公开的顺利推进。事实上,只有搞好保密工作,信息公开才有可能顺利展开。美国是世界上保密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定密制度的核心就是授权式的定密体制。在美国,定密只能由享有定密权的官员行使,例如,绝密级的定密权只能由总统及总统指定的并在《联邦登记》中予以公布的部门负责人及高级官员行使,其他人则无权进行绝密级的原始定密。其他密级的定密权也同样具有相应的授权。另外,对于定密授权必须采取书面方式,授权书上必须写明被授权官员的姓名或职位和所授予的定密权的定密级别。不仅如此,为解决没有定密权的部门产生秘密而不至于泄密,该制度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某部门的雇员、承包商、许可证持有者或担保人,如果产生一份需要保密的信息,而这个部门没有定密权时,就应当对这类信息先予以保护,并第2页共4页立即把此信息转给有该信息定密权的部门。如果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