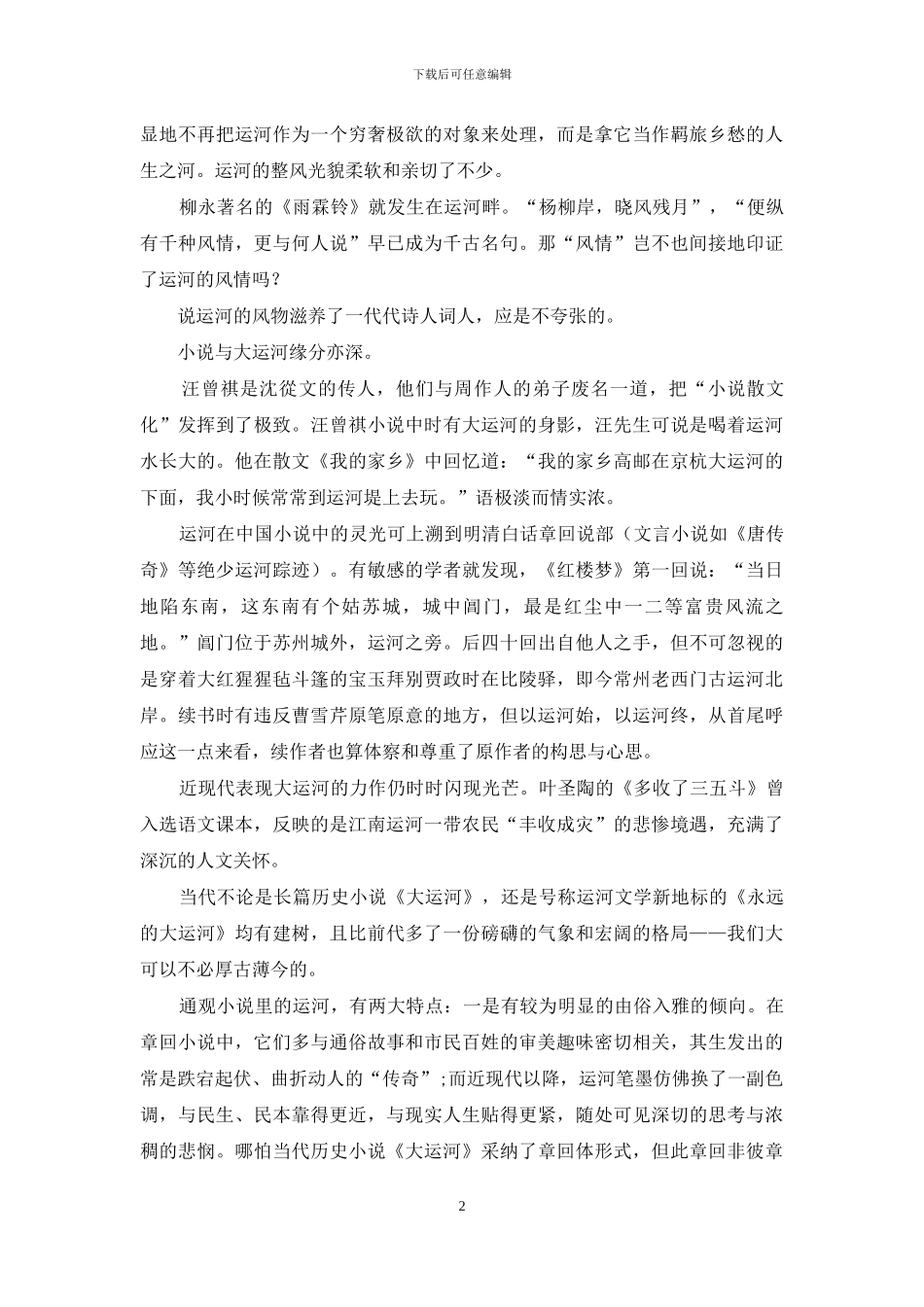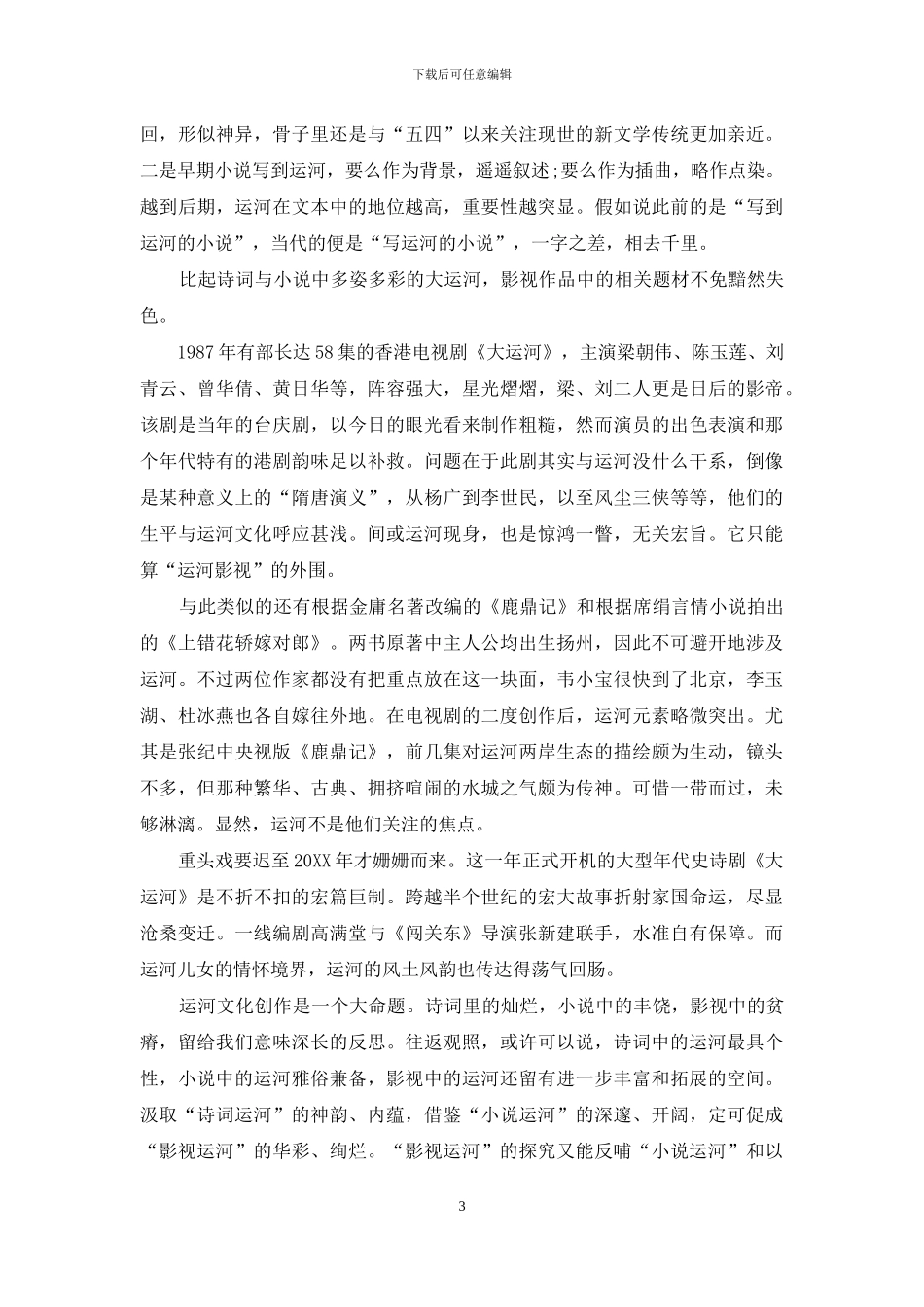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诗词、小说与影视中的大运河诗词、小说与影视中的大运河 陶然 “大运河”在中国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不论隋炀帝下扬州所引发的一系列民间传说与趣闻轶事及戏剧曲艺等,单是从诗词、小说与影视中运河题材的一次次出现,也可发现“大运河”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长河中从未缺席。 大运河系由隋朝第二代皇帝隋炀帝下令开凿。隋朝史称“流星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速,文治武功曾煊赫一时,却不到四十年就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强大的唐朝和最富庶的宋朝。这两个王朝恰好是“诗的朝代”和“词的时代”,因此诗词中常常显现大运河的身影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白居易的《隋堤柳》,对炀帝开运河持较为严冷的否定态度。诗风仍是所谓“乐天体”,与《长恨歌》《琵琶行》一脉相承,明白如话,老妪能解,唯艺术成就不及那两首脍炙人口之作,主题上也有持论过苛之嫌——只见大运河的“祸在当代”,不见它造福民生、沟通南北的“功在千秋”;只认定隋炀帝开此一河是恣意享乐,完全抹杀(或真的想不到)他的战略眼光与长远布局。在白居易的这首诗中,大运河的形象很不光彩,可说是对河与人双重的不公平。事实上隋炀帝通此一河,以如此浩大的工程只为一睹琼花的尊容,只为饱览沿途风光,在政治家的层面上有多少可能性?炀帝的动机客观来说是“公私兼顾,以公为主”,虽不排除借此巡行观光的因素,却更是为了要把天下一统前的北齐、北周故地与江南的陈政权以一条畅通的大水路紧紧扭结在一起,让隋王朝真正在经济沟通、文化心理上融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有鉴于此,《隋堤柳》足够真诚,却不足够冷静与超迈。 与此相似的诗作还有一批,这多少反应了当时诗人群体的主流认知。 到了北宋,与隋朝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而享受到的运河的便利比唐代显著,不同的声音就此出现。宋词光耀千秋,以婉约派为正宗,离愁别绪为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恰好与汴河(运河)上的迎来送往息息相关。相当多的词作明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显地不再把运河作为一个穷奢极欲的对象来处理,而是拿它当作羁旅乡愁的人生之河。运河的整风光貌柔软和亲切了不少。 柳永著名的《雨霖铃》就发生在运河畔。“杨柳岸,晓风残月”,“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早已成为千古名句。那“风情”岂不也间接地印证了运河的风情吗? 说运河的风物滋养了一代代诗人词人,应是不夸张的。 小说与大运河缘分亦深。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传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