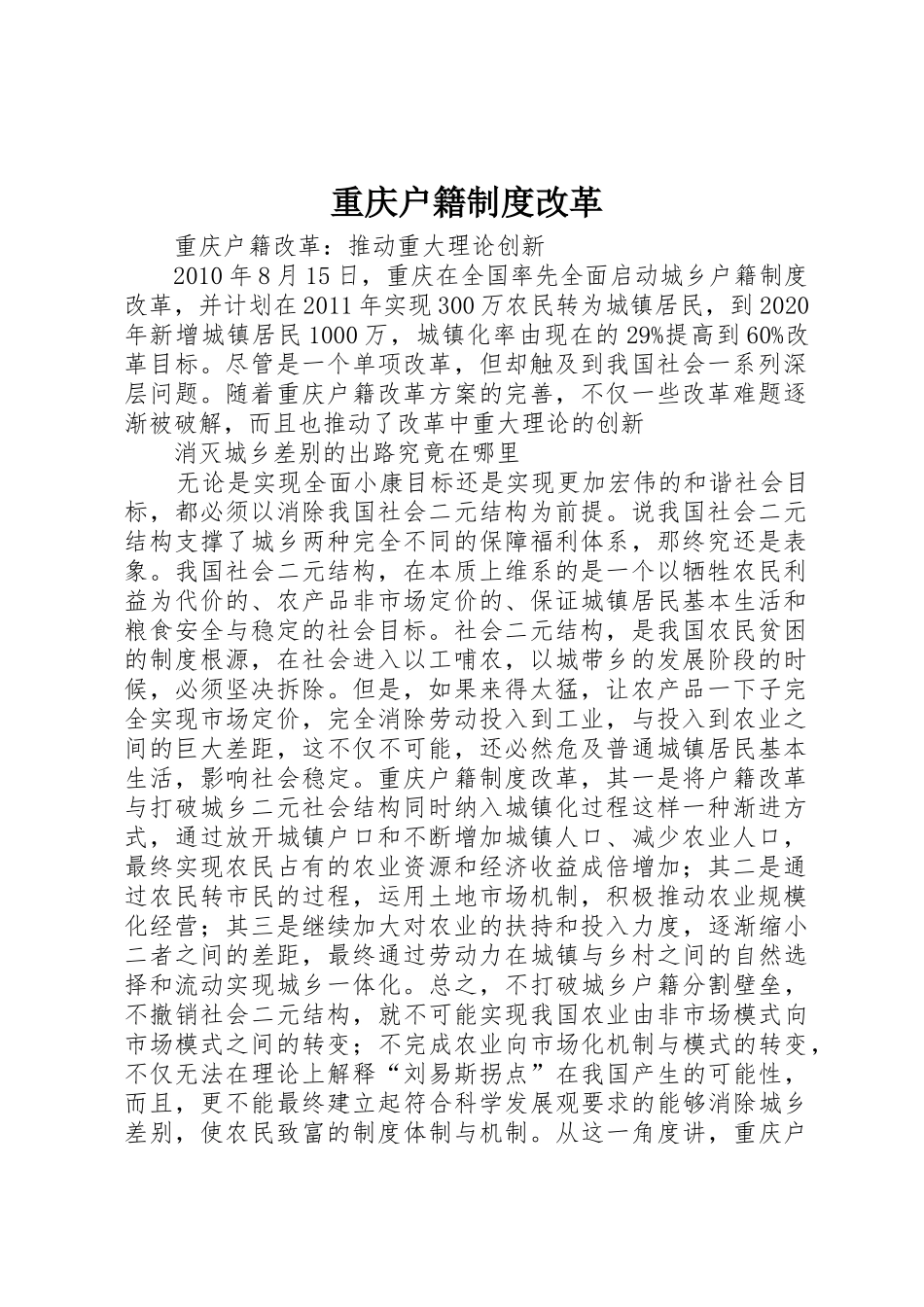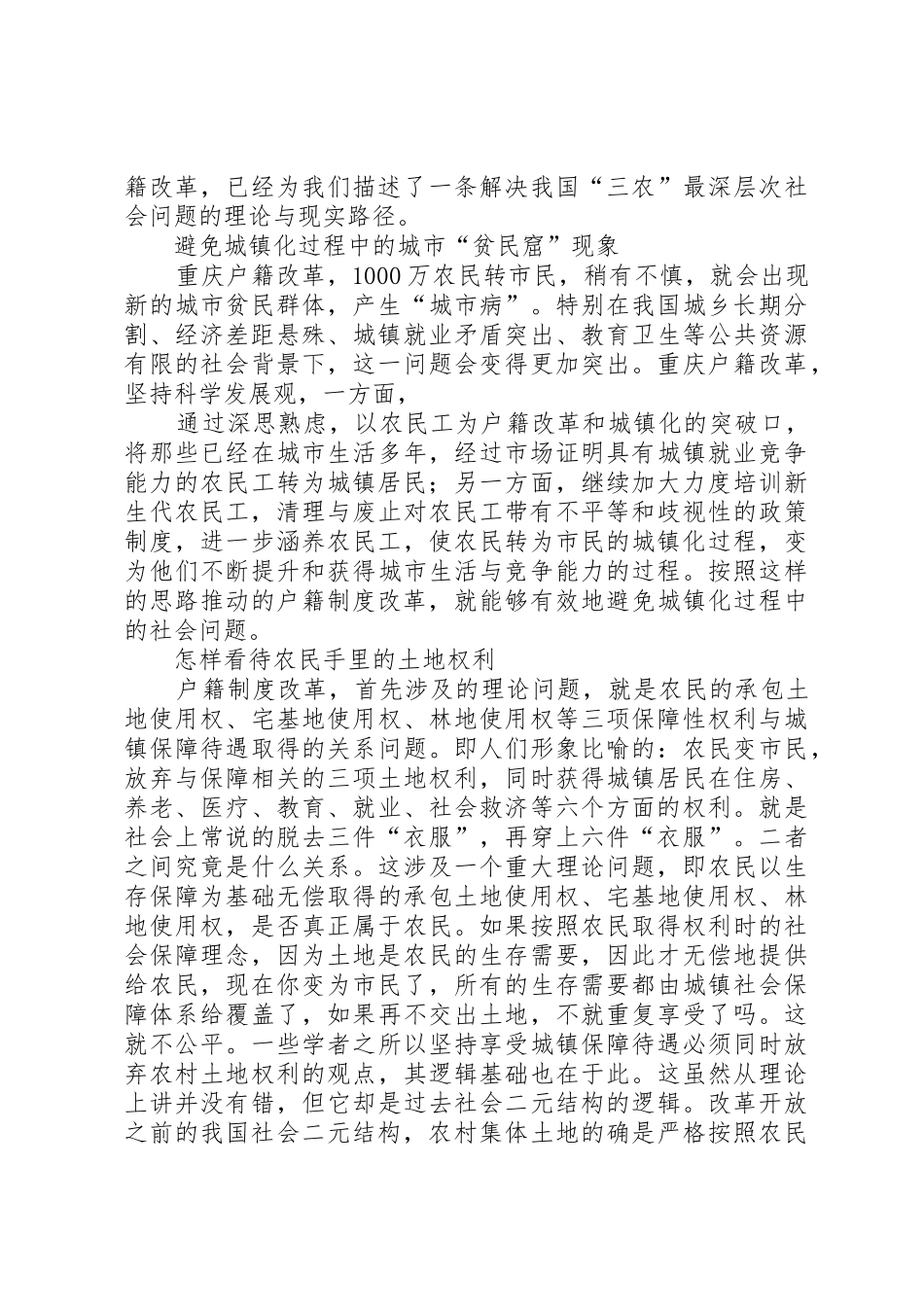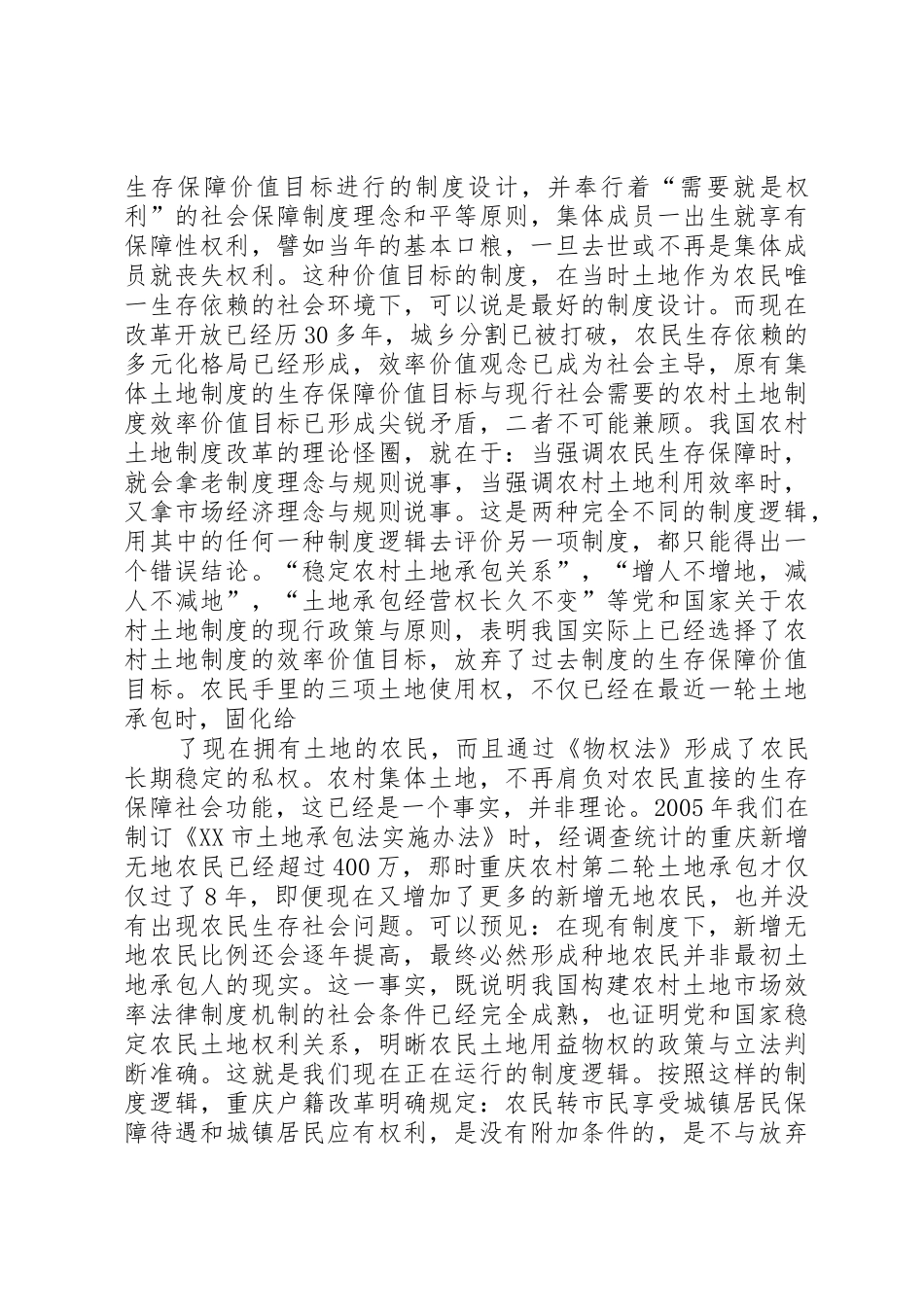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户籍改革:推动重大理论创新 2010 年 8 月 15 日,重庆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并计划在 2011 年实现 300 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到 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 1000 万,城镇化率由现在的 29%提高到 60%改革目标。尽管是一个单项改革,但却触及到我国社会一系列深层问题。随着重庆户籍改革方案的完善,不仅一些改革难题逐渐被破解,而且也推动了改革中重大理论的创新 消灭城乡差别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还是实现更加宏伟的和谐社会目标,都必须以消除我国社会二元结构为前提。说我国社会二元结构支撑了城乡两种完全不同的保障福利体系,那终究还是表象。我国社会二元结构,在本质上维系的是一个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农产品非市场定价的、保证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和粮食安全与稳定的社会目标。社会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在社会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必须坚决拆除。但是,如果来得太猛,让农产品一下子完全实现市场定价,完全消除劳动投入到工业,与投入到农业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不仅不可能,还必然危及普通城镇居民基本生活,影响社会稳定。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其一是将户籍改革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同时纳入城镇化过程这样一种渐进方式,通过放开城镇户口和不断增加城镇人口、减少农业人口,最终实现农民占有的农业资源和经济收益成倍增加;其二是通过农民转市民的过程,运用土地市场机制,积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三是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力度,逐渐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终通过劳动力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自然选择和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总之,不打破城乡户籍分割壁垒,不撤销社会二元结构,就不可能实现我国农业由非市场模式向市场模式之间的转变;不完成农业向市场化机制与模式的转变,不仅无法在理论上解释“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产生的可能性,而且,更不能最终建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能够消除城乡差别,使农民致富的制度体制与机制。从这一角度讲,重庆户籍改革,已经为我们描述了一条解决我国“三农”最深层次社会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路径。 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贫民窟”现象 重庆户籍改革,1000 万农民转市民,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新的城市贫民群体,产生“城市病”。特别在我国城乡长期分割、经济差距悬殊、城镇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有限的社会背景下,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重庆户籍改革,坚持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