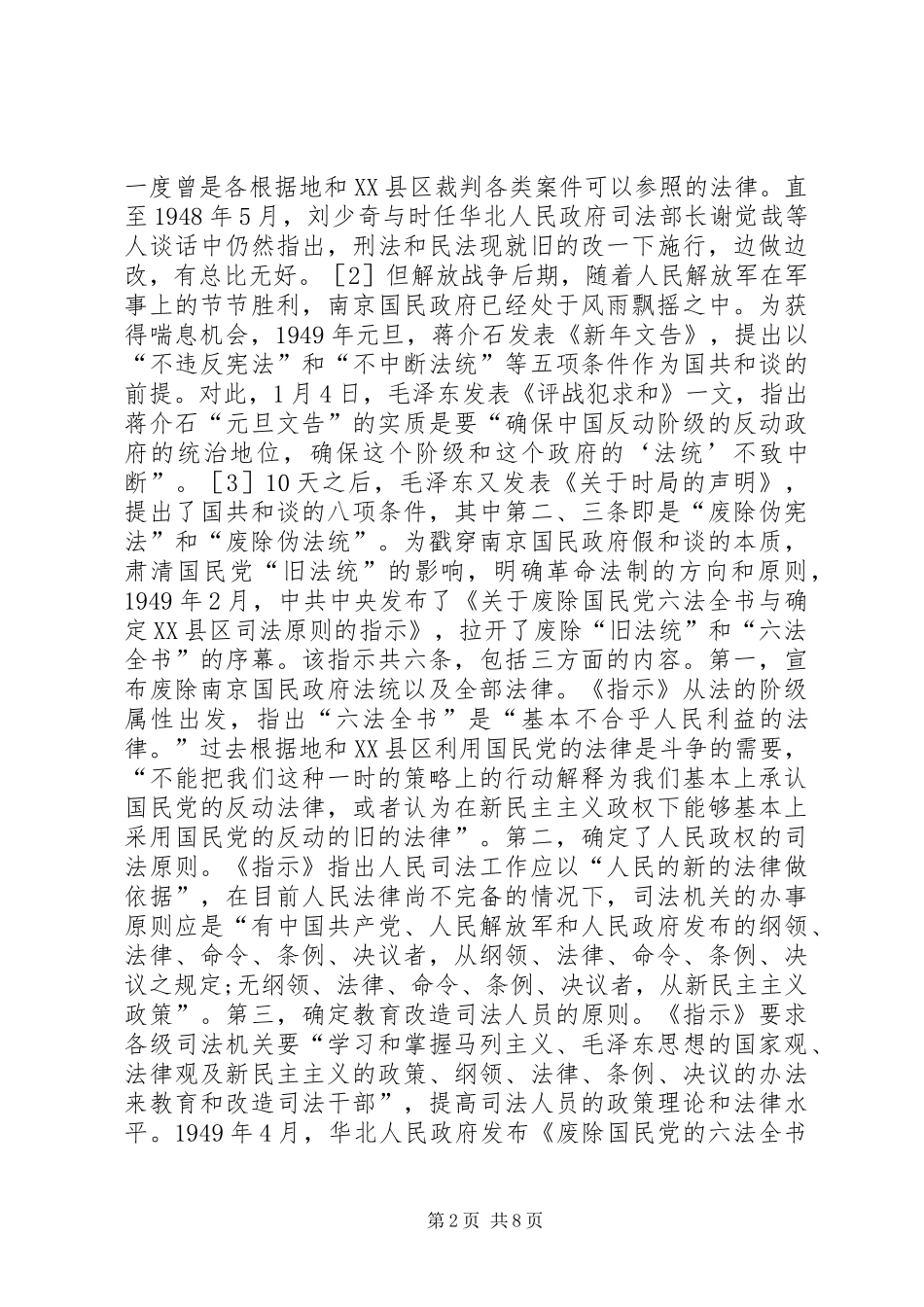司法变革回溯与思考法律和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系统,社会文化是一种法律制度和司法秩序产生、发展并赖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根本因素,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往往导致一国司法制度和司法文化的变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深刻巨变迫切要求司法观念的改弦更张和司法制度的破旧立新。为此,党和国家在司法领域中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废除以“六法全书”①为标志的“旧法统”秩序,二是树立“兴无灭资”的司法观和“学苏批资”的法制观,三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司法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从司法观念、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等各方面清除了支撑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旧司法秩序,在一张崭新的图纸上描绘出社会主义的司法蓝图,奠定了新中国的司法秩序。但囿于时代的特殊性和观念的局限性,当年的司法变革确实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60年后,站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场波澜壮阔、曲折蜿蜒的司法变革之路,对于身处中国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我们选择何种司法改革路径具有重要价值。一、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建立人民的新司法(一)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始末所谓“法统”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狭义上的“法统”即是合法之正统,是针对政府统治权力在法律上的来源而言,主要是指一国的宪法体系和宪政秩序。其二,广义上的“法统”就是法律之统治,其外延囊括一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按照这种理解,国民党的“旧法统”在狭义层面上主要指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宪法性文件,而广义层面则囊括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全部法律———以“六法全书”为主体,包括相关判例、解释例、党规党纪以及蒋介石手谕和命令在内的一整套法律体系。[1]不过从当时的革命实践来看,共产党人将“旧法统”直接视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实际上,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革命法制之外,“六法全书”第1页共8页一度曾是各根据地和XX县区裁判各类案件可以参照的法律。直至1948年5月,刘少奇与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谢觉哉等人谈话中仍然指出,刑法和民法现就旧的改一下施行,边做边改,有总比无好。[2]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获得喘息机会,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以“不违反宪法”和“不中断法统”等五项条件作为国共和谈的前提。对此,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指出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实质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3]10天之后,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三条即是“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为戳穿南京国民政府假和谈的本质,肃清国民党“旧法统”的影响,明确革命法制的方向和原则,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XX县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拉开了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的序幕。该指示共六条,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宣布废除南京国民政府法统以及全部法律。《指示》从法的阶级属性出发,指出“六法全书”是“基本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法律。”过去根据地和XX县区利用国民党的法律是斗争的需要,“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或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能够基本上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的法律”。第二,确定了人民政权的司法原则。《指示》指出人民司法工作应以“人民的新的法律做依据”,在目前人民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是“有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发布的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第三,确定教育改造司法人员的原则。《指示》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