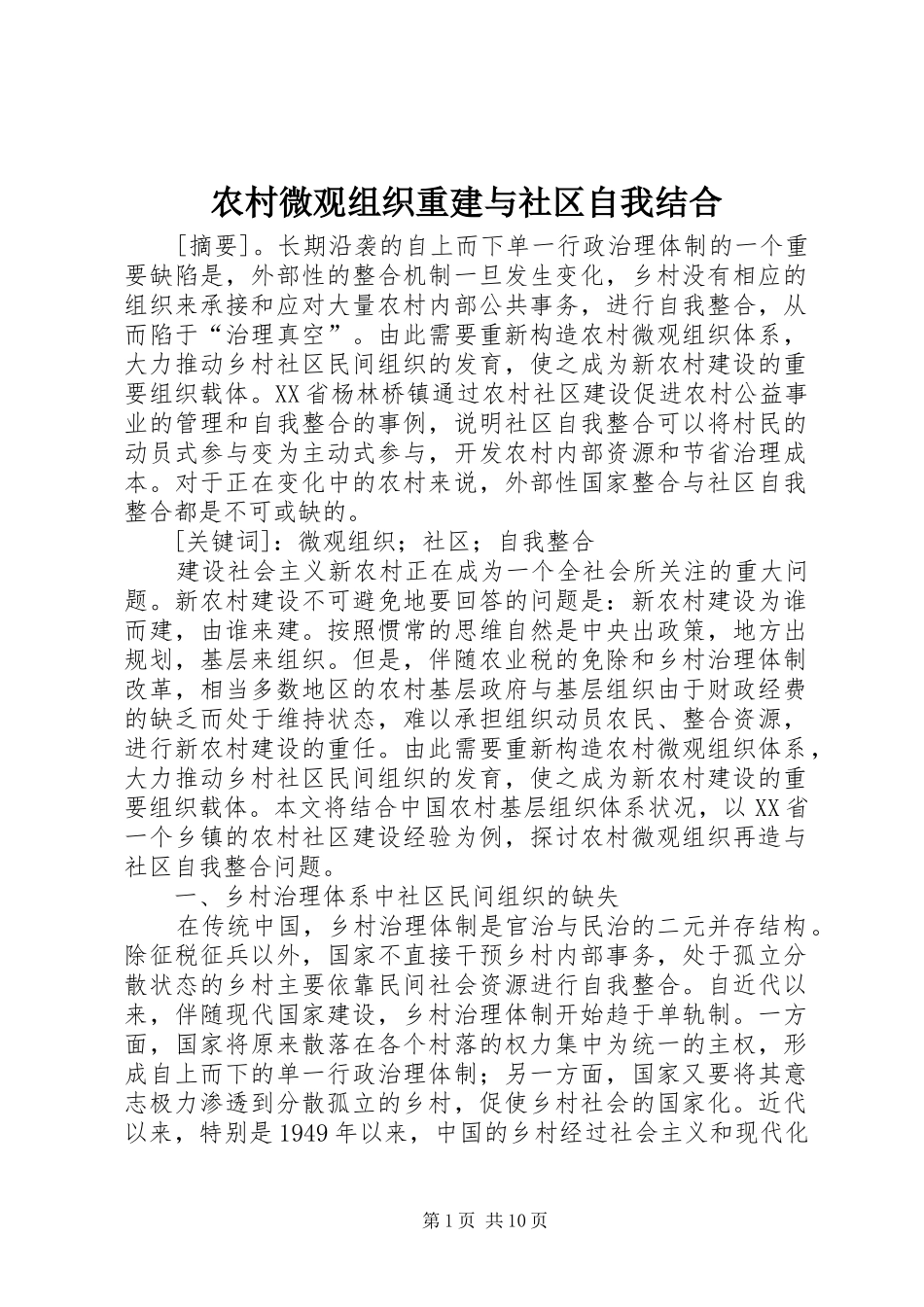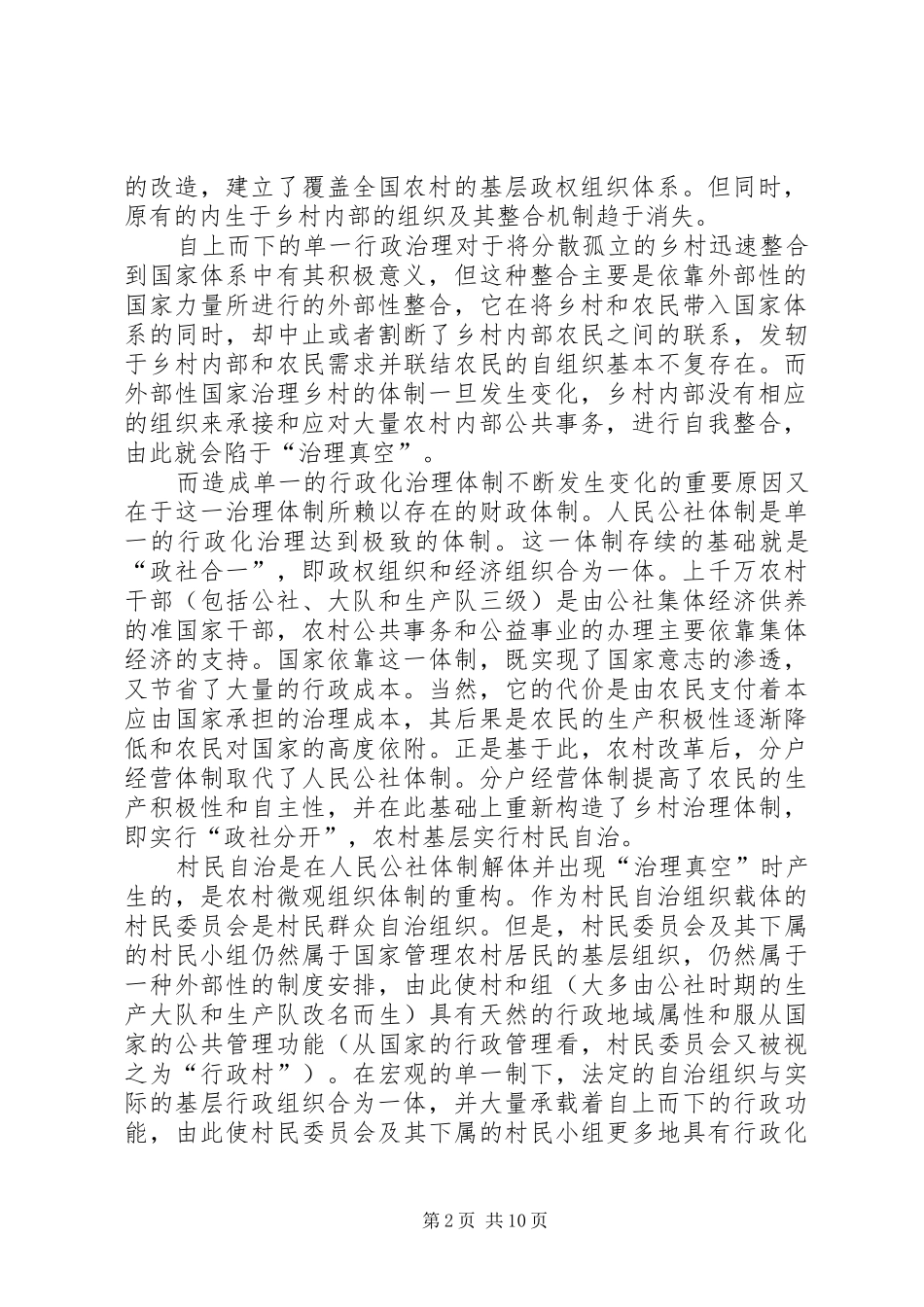农村微观组织重建与社区自我结合[摘要]。长期沿袭的自上而下单一行政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外部性的整合机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从而陷于“治理真空”。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XX省杨林桥镇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自我整合的事例,说明社区自我整合可以将村民的动员式参与变为主动式参与,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和节省治理成本。对于正在变化中的农村来说,外部性国家整合与社区自我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XX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主权,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第1页共10页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人民公社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在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第2页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