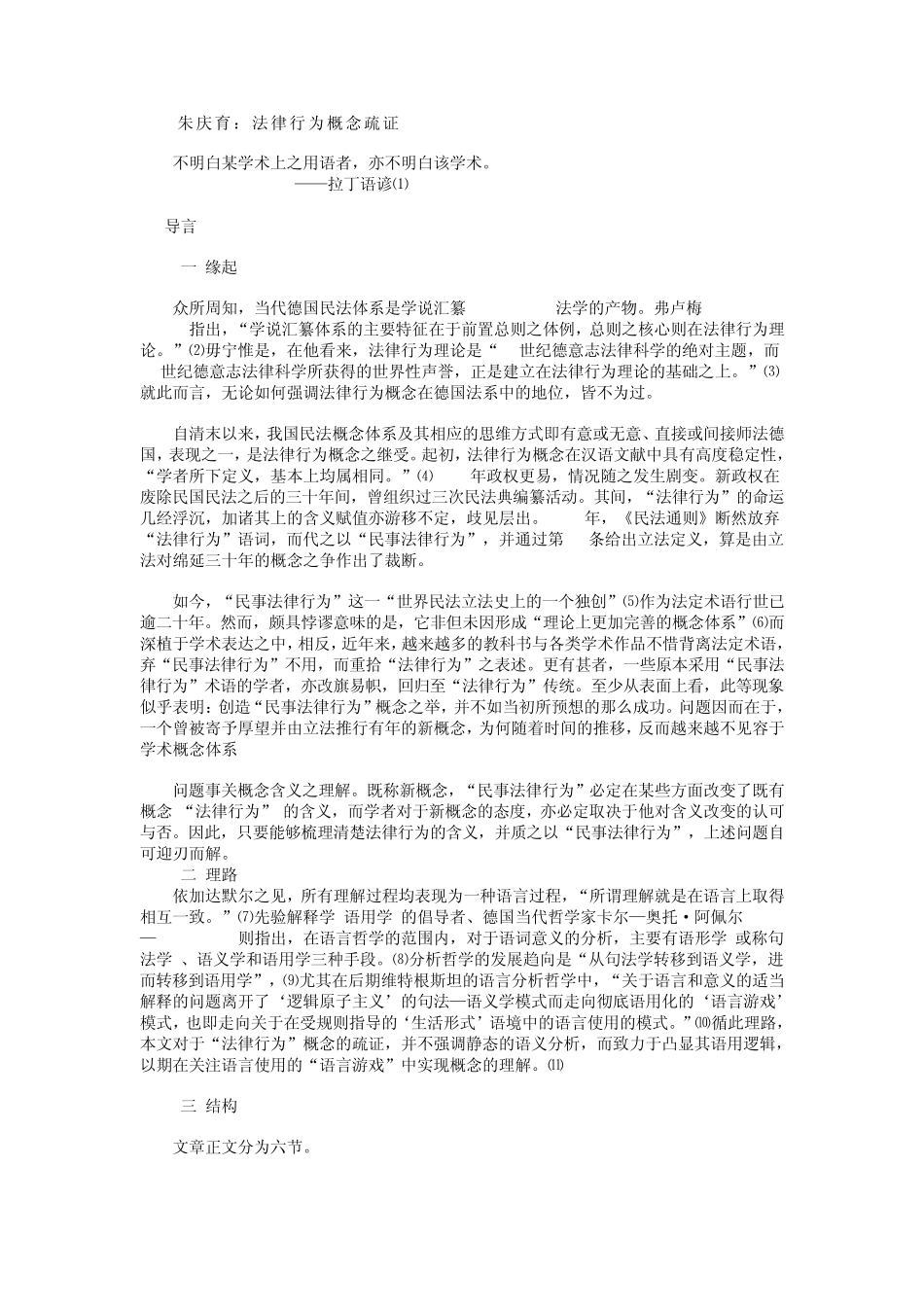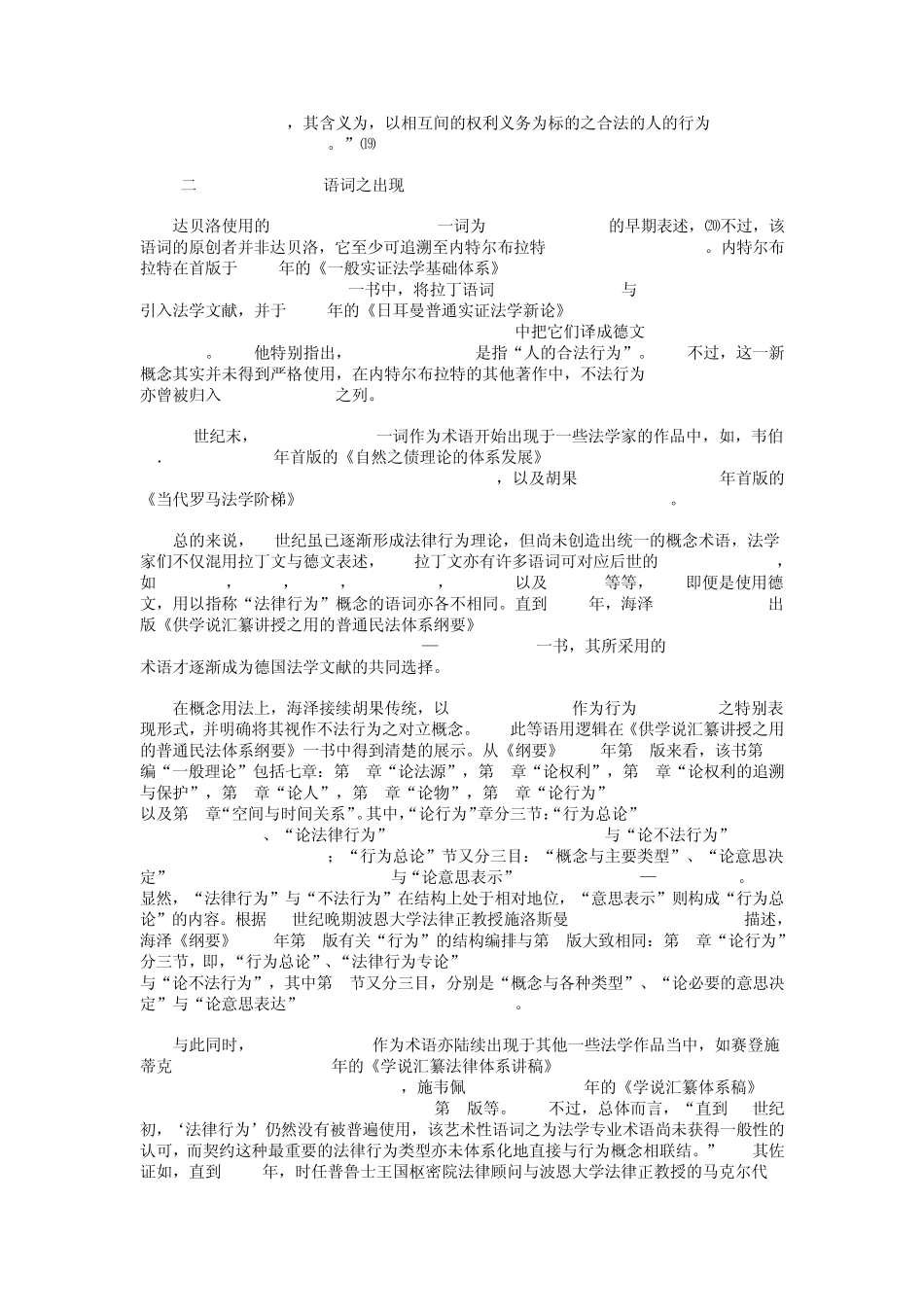朱庆育:法律行为概念疏证 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 ——拉丁语谚⑴ 导言 (一)缘起 众所周知,当代德国民法体系是学说汇纂(Pandekten)法学的产物。弗卢梅(Werner Flume)指出,“学说汇纂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前置总则之体例,总则之核心则在法律行为理论。”⑵毋宁惟是,在他看来,法律行为理论是“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的绝对主题,而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所获得的世界性声誉,正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⑶就此而言,无论如何强调法律行为概念在德国法系中的地位,皆不为过。 自清末以来,我国民法概念体系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即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师法德国,表现之一,是法律行为概念之继受。起初,法律行为概念在汉语文献中具有高度稳定性,“学者所下定义,基本上均属相同。”⑷1949年政权更易,情况随之发生剧变。新政权在废除民国民法之后的三十年间,曾组织过三次民法典编纂活动。其间,“法律行为”的命运几经浮沉,加诸其上的含义赋值亦游移不定,歧见层出。1986年,《民法通则》断然放弃“法律行为”语词,而代之以“民事法律行为”,并通过第54条给出立法定义,算是由立法对绵延三十年的概念之争作出了裁断。 如今,“民事法律行为”这一“世界民法立法史上的一个独创”⑸作为法定术语行世已逾二十年。然而,颇具悖谬意味的是,它非但未因形成“理论上更加完善的概念体系”⑹而深植于学术表达之中,相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科书与各类学术作品不惜背离法定术语,弃“民事法律行为”不用,而重拾“法律行为”之表述。更有甚者,一些原本采用“民事法律行为”术语的学者,亦改旗易帜,回归至“法律行为”传统。至少从表面上看,此等现象似乎表明:创造“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举,并不如当初所预想的那么成功。问题因而在于,一个曾被寄予厚望并由立法推行有年的新概念,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不见容于学术概念体系? 问题事关概念含义之理解。既称新概念,“民事法律行为”必定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既有概念(“法律行为”)的含义,而学者对于新概念的态度,亦必定取决于他对含义改变的认可与否。因此,只要能够梳理清楚法律行为的含义,并质之以“民事法律行为”,上述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二)理路 依加达默尔之见,所有理解过程均表现为一种语言过程,“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⑺先验解释学(语用学)的倡导者、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则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