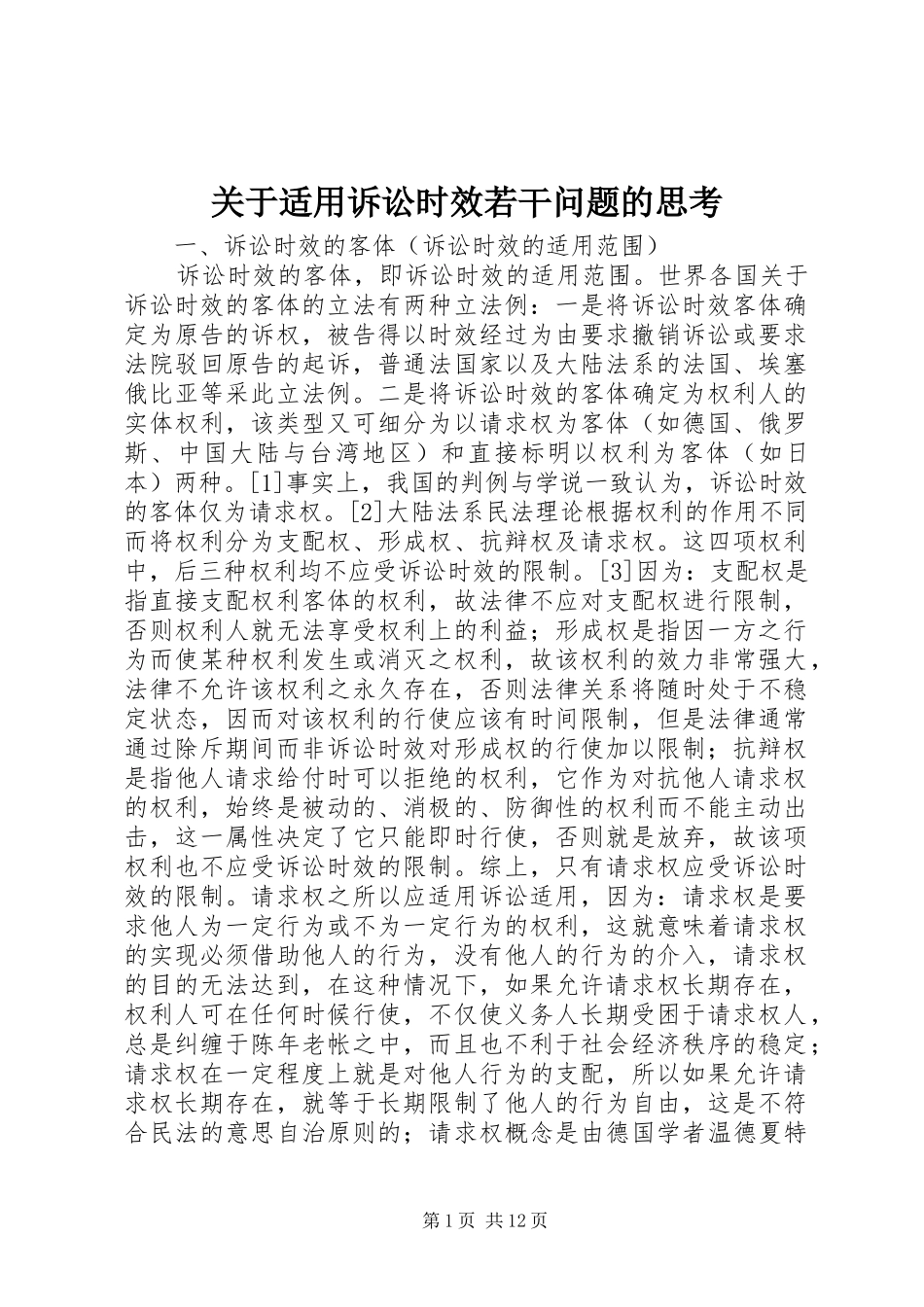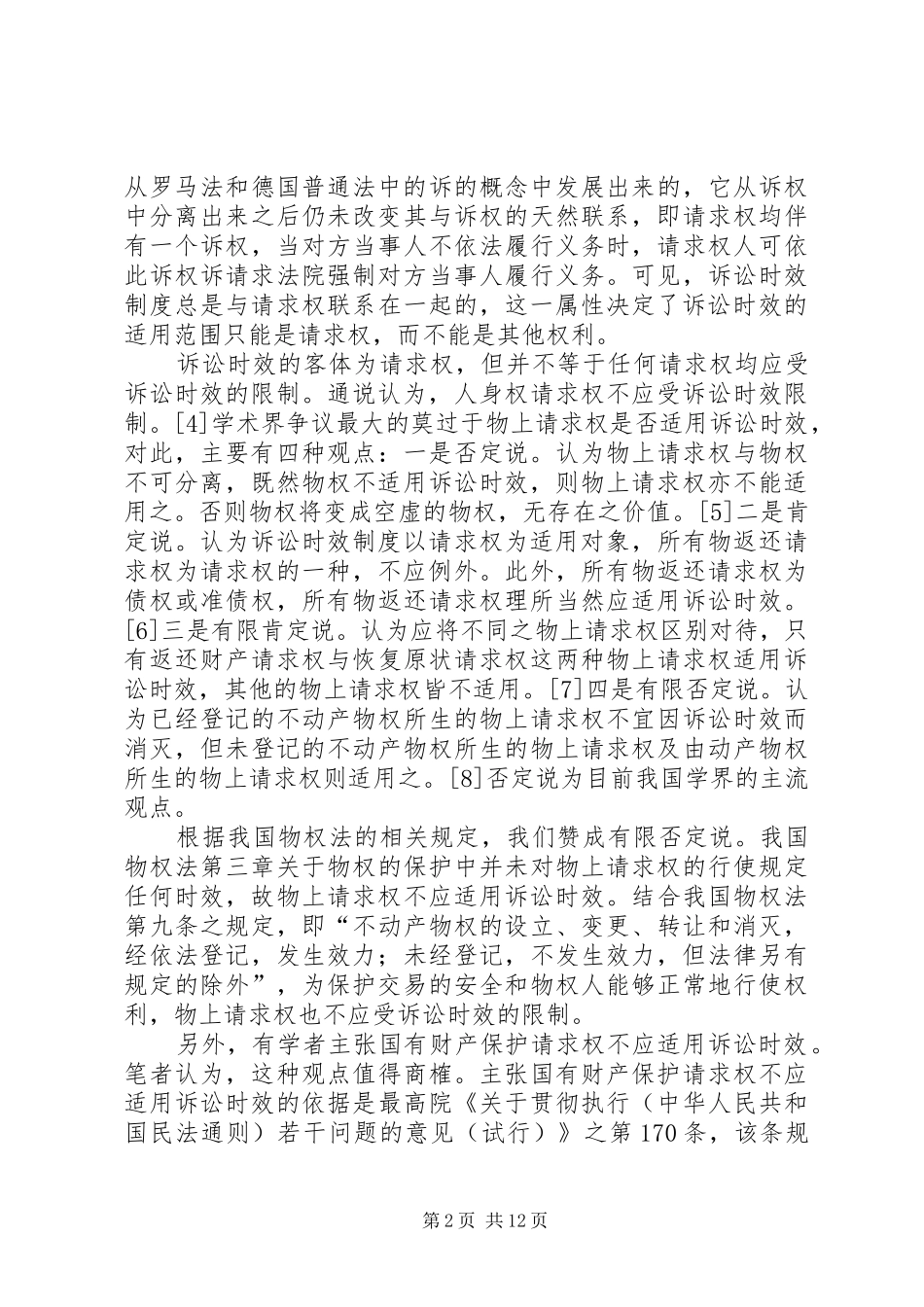关于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思考一、诉讼时效的客体(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客体,即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世界各国关于诉讼时效的客体的立法有两种立法例:一是将诉讼时效客体确定为原告的诉权,被告得以时效经过为由要求撤销诉讼或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普通法国家以及大陆法系的法国、埃塞俄比亚等采此立法例。二是将诉讼时效的客体确定为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该类型又可细分为以请求权为客体(如德国、俄罗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和直接标明以权利为客体(如日本)两种。[1]事实上,我国的判例与学说一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仅为请求权。[2]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根据权利的作用不同而将权利分为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及请求权。这四项权利中,后三种权利均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3]因为:支配权是指直接支配权利客体的权利,故法律不应对支配权进行限制,否则权利人就无法享受权利上的利益;形成权是指因一方之行为而使某种权利发生或消灭之权利,故该权利的效力非常强大,法律不允许该权利之永久存在,否则法律关系将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对该权利的行使应该有时间限制,但是法律通常通过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对形成权的行使加以限制;抗辩权是指他人请求给付时可以拒绝的权利,它作为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防御性的权利而不能主动出击,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只能即时行使,否则就是放弃,故该项权利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综上,只有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请求权之所以应适用诉讼适用,因为: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请求权的实现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没有他人的行为的介入,请求权的目的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请求权长期存在,权利人可在任何时候行使,不仅使义务人长期受困于请求权人,总是纠缠于陈年老帐之中,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请求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他人行为的支配,所以如果允许请求权长期存在,就等于长期限制了他人的行为自由,这是不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请求权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夏特第1页共12页从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中的诉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从诉权中分离出来之后仍未改变其与诉权的天然联系,即请求权均伴有一个诉权,当对方当事人不依法履行义务时,请求权人可依此诉权诉请求法院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可见,诉讼时效制度总是与请求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属性决定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只能是请求权,而不能是其他权利。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但并不等于任何请求权均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通说认为,人身权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4]学术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对此,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上请求权亦不能适用之。否则物权将变成空虚的物权,无存在之价值。[5]二是肯定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以请求权为适用对象,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请求权的一种,不应例外。此外,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债权或准债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理所当然应适用诉讼时效。[6]三是有限肯定说。认为应将不同之物上请求权区别对待,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上请求权皆不适用。[7]四是有限否定说。认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则适用之。[8]否定说为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赞成有限否定说。我国物权法第三章关于物权的保护中并未对物上请求权的行使规定任何时效,故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结合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保护交易的安全和物权人能够正常地行使权利,物上请求权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另外,有学者主张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主张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是最高院《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