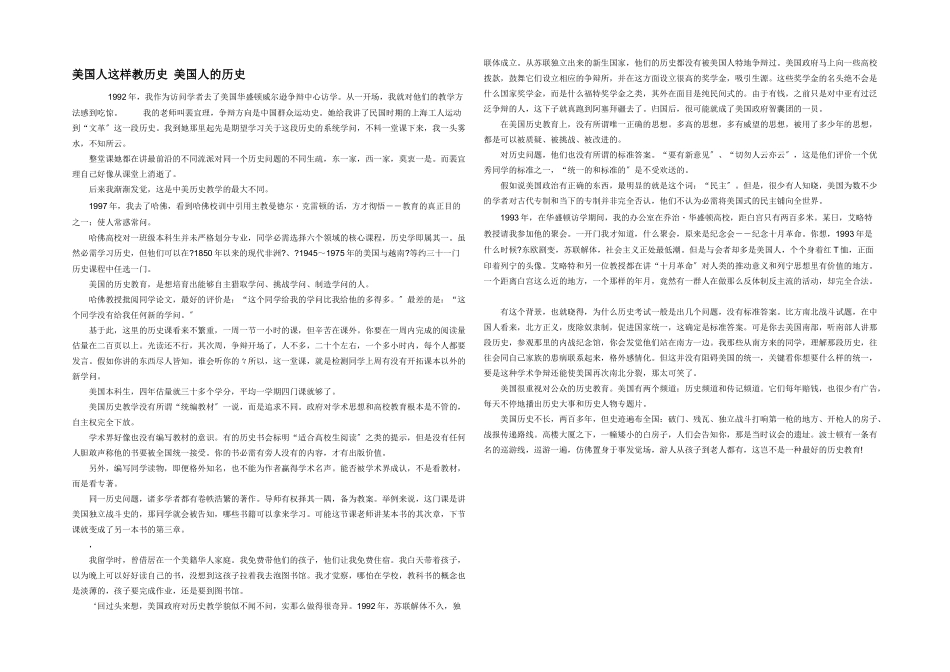美国人这样教历史 美国人的历史 1992 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争辩中心访学。从一开场,我就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感到吃惊。 我的老师叫裴宜理,争辩方向是中国群众运动史。她给我讲了民国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到“文革〞这一段历史。我到她那里起先是期望学习关于这段历史的系统学问,不料一堂课下来,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整堂课她都在讲最前沿的不同流派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不同生疏,东一家,西一家,莫衷一是。而裴宜理自己好像从课堂上消逝了。 后来我渐渐发觉,这是中美历史教学的最大不同。 1997 年,我去了哈佛,看到哈佛校训中引用主教曼德尔・克雷顿的话,方才彻悟――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一:使人常惑常问。 哈佛高校对一班级本科生并未严格划分专业,同学必需选择六个领域的核心课程,历史学即属其一。虽然必需学习历史,但他们可以在?1850 年以来的现代非洲?、?1945~1975 年的美国与越南?等约三十一门历史课程中任选一门。 美国的历史教育,是想培育出能够自主猎取学问、挑战学问、制造学问的人。 哈佛教授批阅同学论文,最好的评价是:“这个同学给我的学问比我给他的多得多。〞最差的是:“这个同学没有给我任何新的学问。〞 基于此,这里的历史课看来不繁重,一周一节一小时的课,但辛苦在课外。你要在一周内完成的阅读量估量在二百页以上。光读还不行,其次周,争辩开场了,人不多,二十个左右,一个多小时内,每个人都要发言。假如你讲的东西尽人皆知,谁会听你的々所以,这一堂课,就是检测同学上周有没有开拓课本以外的新学问。 美国本科生,四年估量就三十多个学分,平均一学期四门课就够了。 美国历史教学没有所谓“统编教材〞一说,而是追求不同。政府对学术思想和高校教育根本是不管的,自主权完全下放。 学术界好像也没有编写教材的意识。有的历史书会标明“适合高校生阅读〞之类的提示,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声称他的书要被全国统一接受。你的书必需有旁人没有的内容,才有出版价值。 另外,编写同学读物,即便格外知名,也不能为作者赢得学术名声。能否被学术界成认,不是看教材,而是看专著。 同一历史问题,诸多学者都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导师有权择其一隅,备为教案。举例来说,这门课是讲美国独立战斗史的,那同学就会被告知,哪些书籍可以拿来学习。可能这节课老师讲某本书的其次章,下节课就变成了另一本书的第三章。 , 我留学时,曾借居在一个美籍华人家庭。我免费带他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