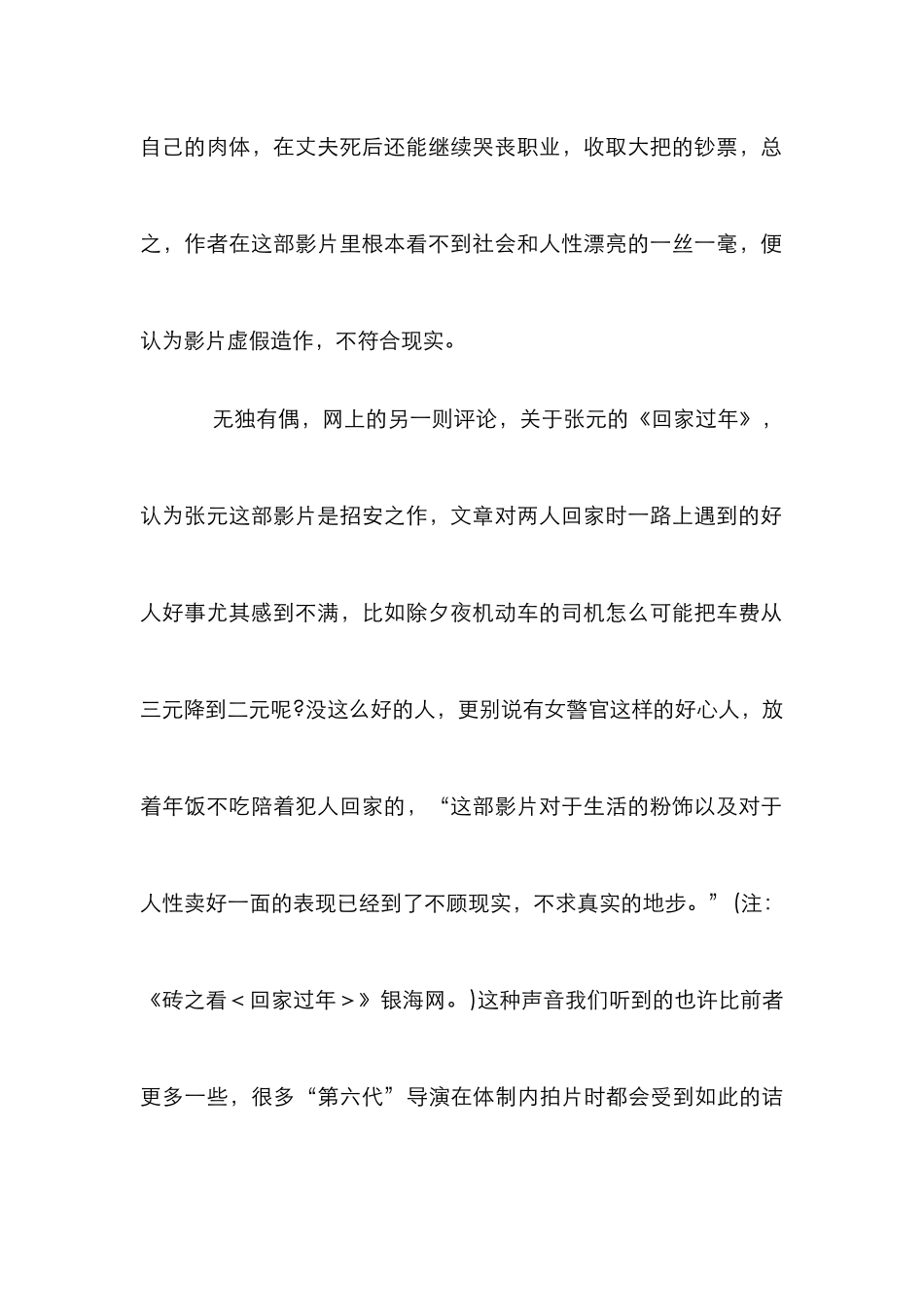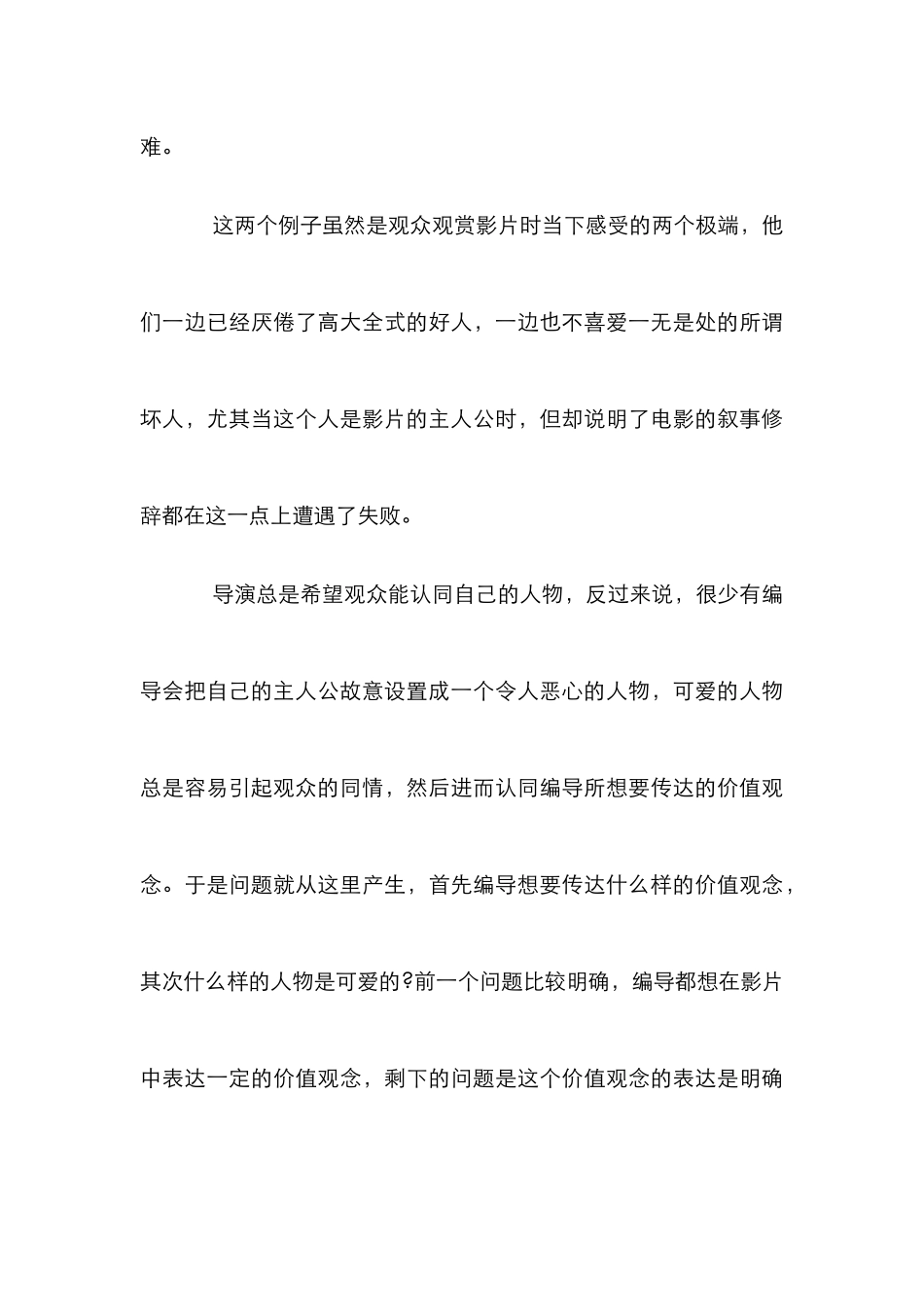电影保守倾向管理论文 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修辞方式具有叙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和叙事修辞中倚重的价值体系两者的关联,把握“第六代”电影的文本现象。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人性漂亮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爱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假如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讨论的。 那么“第六代”导演试图通过影片传达什么样的知识、情感、价值或信仰呢? “不同于某些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