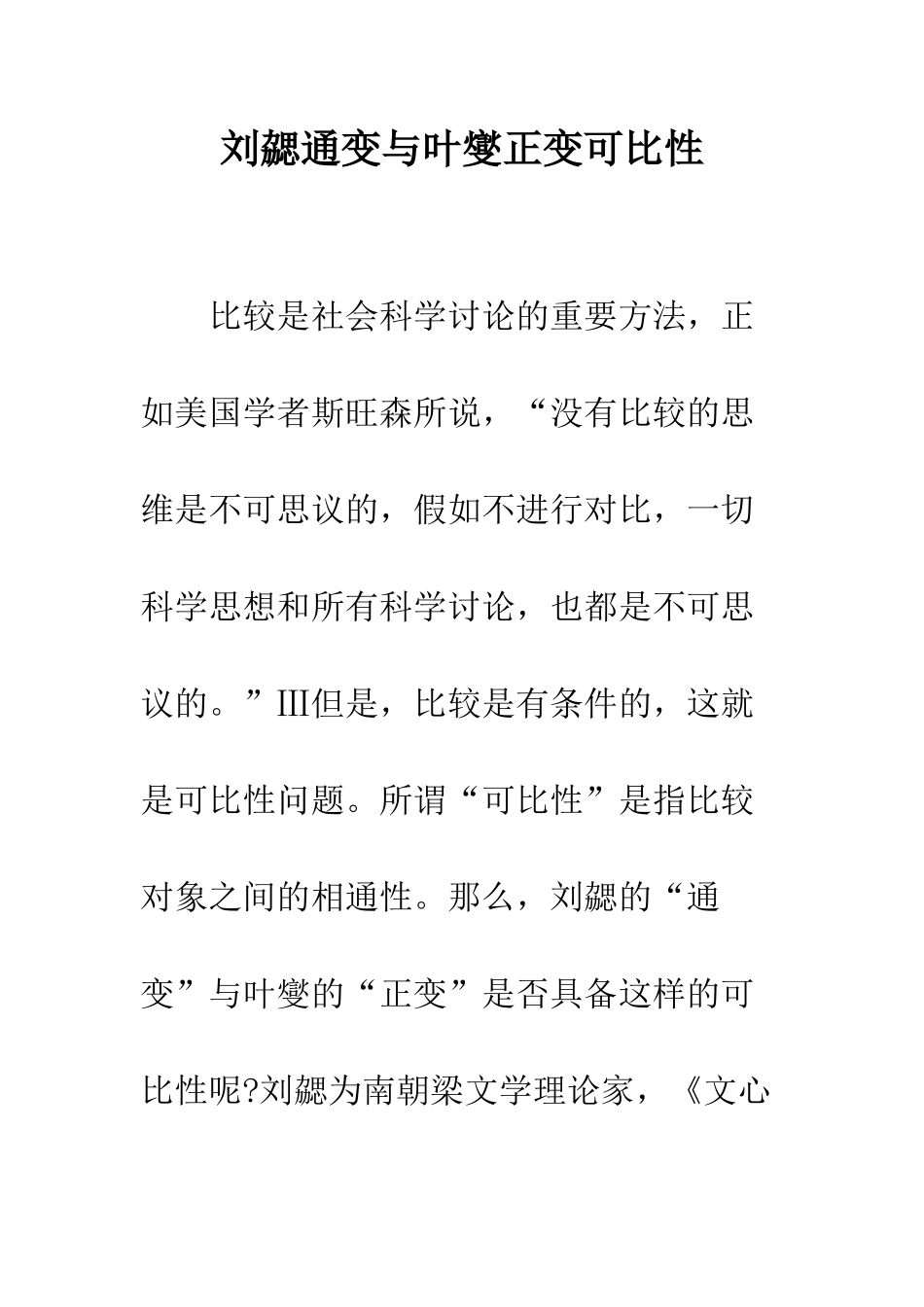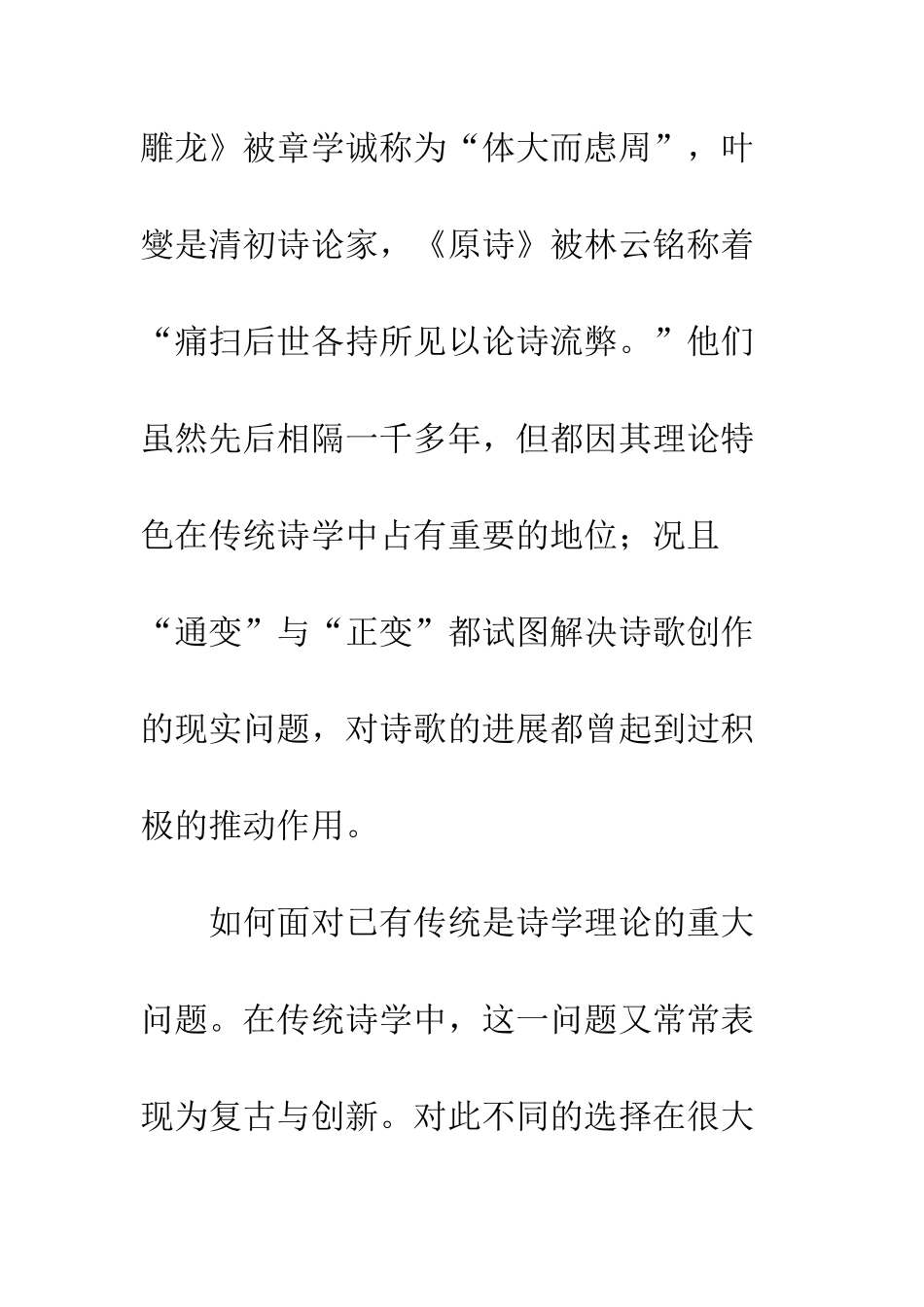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可比性 比较是社会科学讨论的重要方法,正如美国学者斯旺森所说,“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讨论,也都是不可思议的。”Ⅲ但是,比较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可比性问题。所谓“可比性”是指比较对象之间的相通性。那么,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是否具备这样的可比性呢?刘勰为南朝梁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被章学诚称为“体大而虑周”,叶燮是清初诗论家,《原诗》被林云铭称着“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他们虽然先后相隔一千多年,但都因其理论特色在传统诗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况且“通变”与“正变”都试图解决诗歌创作的现实问题,对诗歌的进展都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何面对已有传统是诗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在传统诗学中,这一问题又常常表现为复古与创新。对此不同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进展。刘勰的齐梁与叶燮的明清之际,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集中期,使他们诗学思想产生于类似的语境,因此,在复古与创新之间便成为两者可比性的前提。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思想方面的控制,这为新思想的产生让出了较大的空间。就诗学而言,原来依附于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开始独立,并且,各种不相容的诗学观念又可能同存于一个空间。刘勰正处于“复古”与“新变”的争论点上。 就复古而言,西晋挚虞树立复古大旗,认为文学应“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回到儒家诗教的老路,为人伦教化服务。当五言体诗从民间走向文人,成为主流之时,他又极力提倡“四言为正”,伸四言,黜五言,显示其保守性。裴子野又在《雕虫论》中批判刘宋至齐梁诗为“吟咏情性”、“非止乎礼义”,坚持儒家诗教中心,“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坚守“古法”。与此相应,东晋葛洪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儒,但文学观念却选择新变。与挚虞相反,他提出今文胜古文,坚持认为“古者事醇素,今者莫不雕饰”,是时移世改,理自然也。以萧纲为首的宫体诗人也极力批判崇古宗经的文风,指责他们“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萧子显梳理建安到刘宋的诗歌线索,认为“不相祖述”,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主张。萧统也在《文选序》中提出“踵其事而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