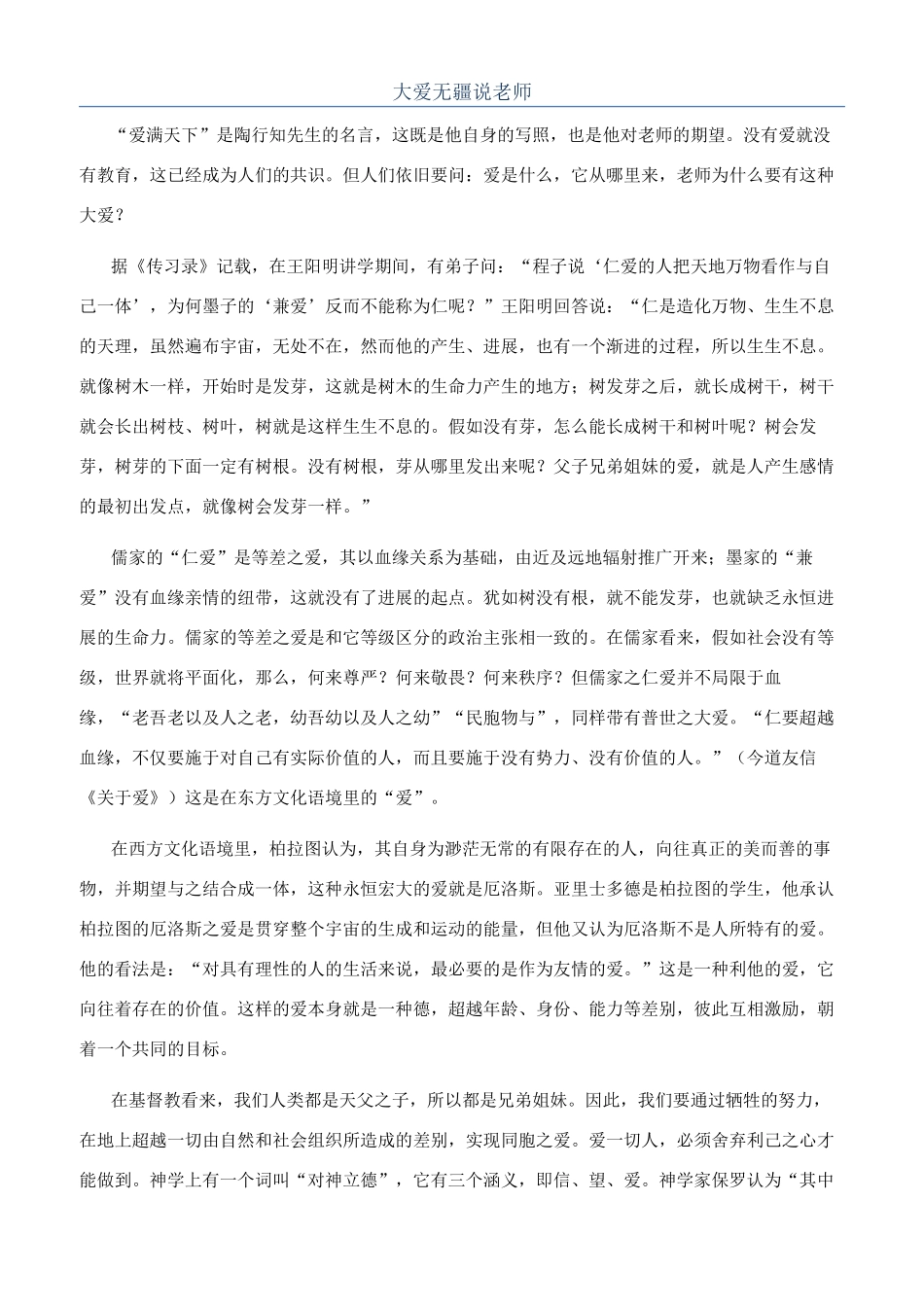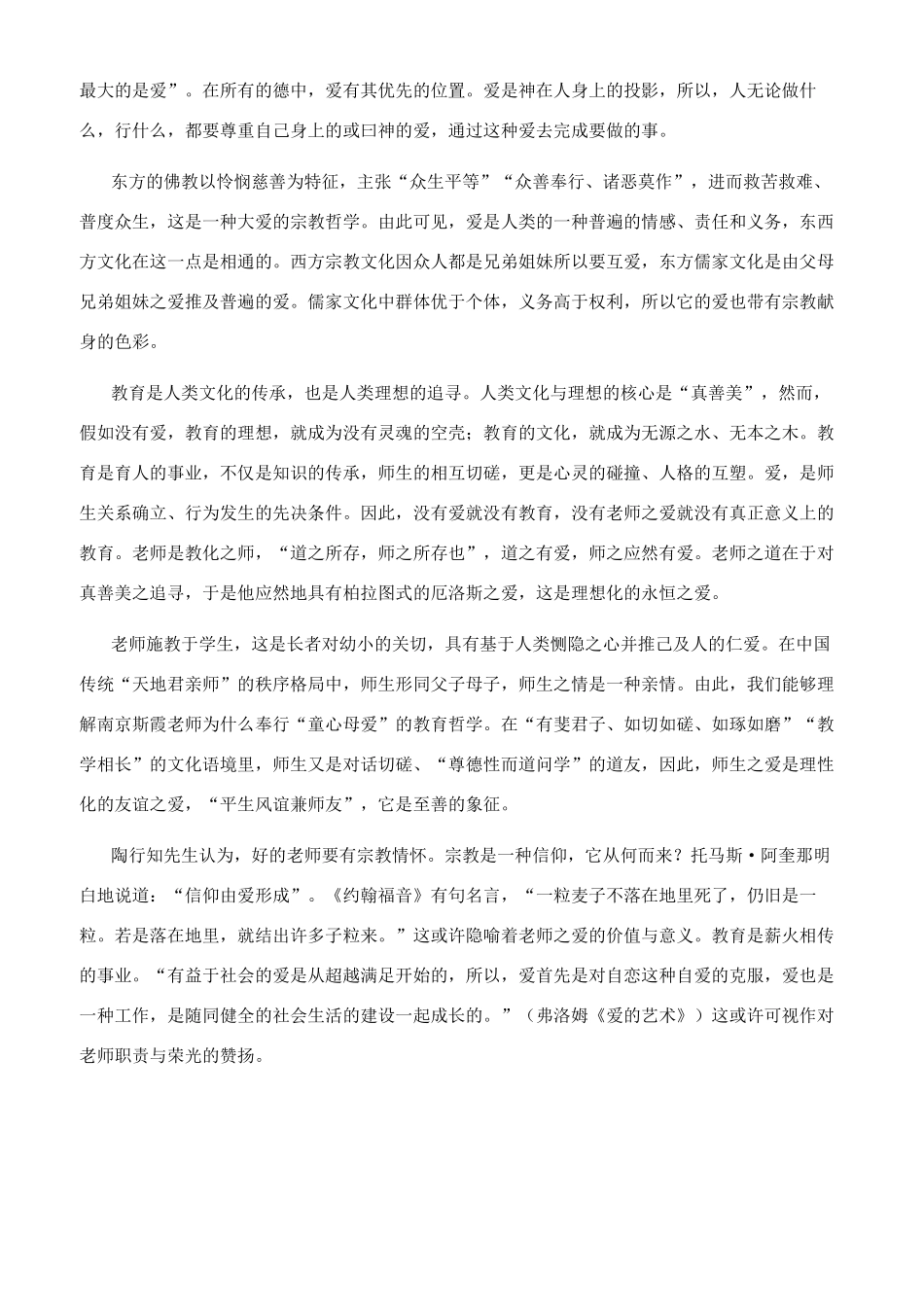大爱无疆说老师“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这既是他自身的写照,也是他对老师的期望。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人们依旧要问:爱是什么,它从哪里来,老师为什么要有这种大爱?据《传习录》记载,在王阳明讲学期间,有弟子问:“程子说‘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与自己一体’,为何墨子的‘兼爱’反而不能称为仁呢?”王阳明回答说:“仁是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虽然遍布宇宙,无处不在,然而他的产生、进展,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生生不息。就像树木一样,开始时是发芽,这就是树木的生命力产生的地方;树发芽之后,就长成树干,树干就会长出树枝、树叶,树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假如没有芽,怎么能长成树干和树叶呢?树会发芽,树芽的下面一定有树根。没有树根,芽从哪里发出来呢?父子兄弟姐妹的爱,就是人产生感情的最初出发点,就像树会发芽一样。”儒家的“仁爱”是等差之爱,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近及远地辐射推广开来;墨家的“兼爱”没有血缘亲情的纽带,这就没有了进展的起点。犹如树没有根,就不能发芽,也就缺乏永恒进展的生命力。儒家的等差之爱是和它等级区分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在儒家看来,假如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将平面化,那么,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儒家之仁爱并不局限于血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胞物与”,同样带有普世之大爱。“仁要超越血缘,不仅要施于对自己有实际价值的人,而且要施于没有势力、没有价值的人。”(今道友信《关于爱》)这是在东方文化语境里的“爱”。在西方文化语境里,柏拉图认为,其自身为渺茫无常的有限存在的人,向往真正的美而善的事物,并期望与之结合成一体,这种永恒宏大的爱就是厄洛斯。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承认柏拉图的厄洛斯之爱是贯穿整个宇宙的生成和运动的能量,但他又认为厄洛斯不是人所特有的爱。他的看法是:“对具有理性的人的生活来说,最必要的是作为友情的爱。”这是一种利他的爱,它向往着存在的价值。这样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德,超越年龄、身份、能力等差别,彼此互相激励,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基督教看来,我们人类都是天父之子,所以都是兄弟姐妹。因此,我们要通过牺牲的努力,在地上超越一切由自然和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差别,实现同胞之爱。爱一切人,必须舍弃利己之心才能做到。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对神立德”,它有三个涵义,即信、望、爱。神学家保罗认为“其中最大的是爱”。在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