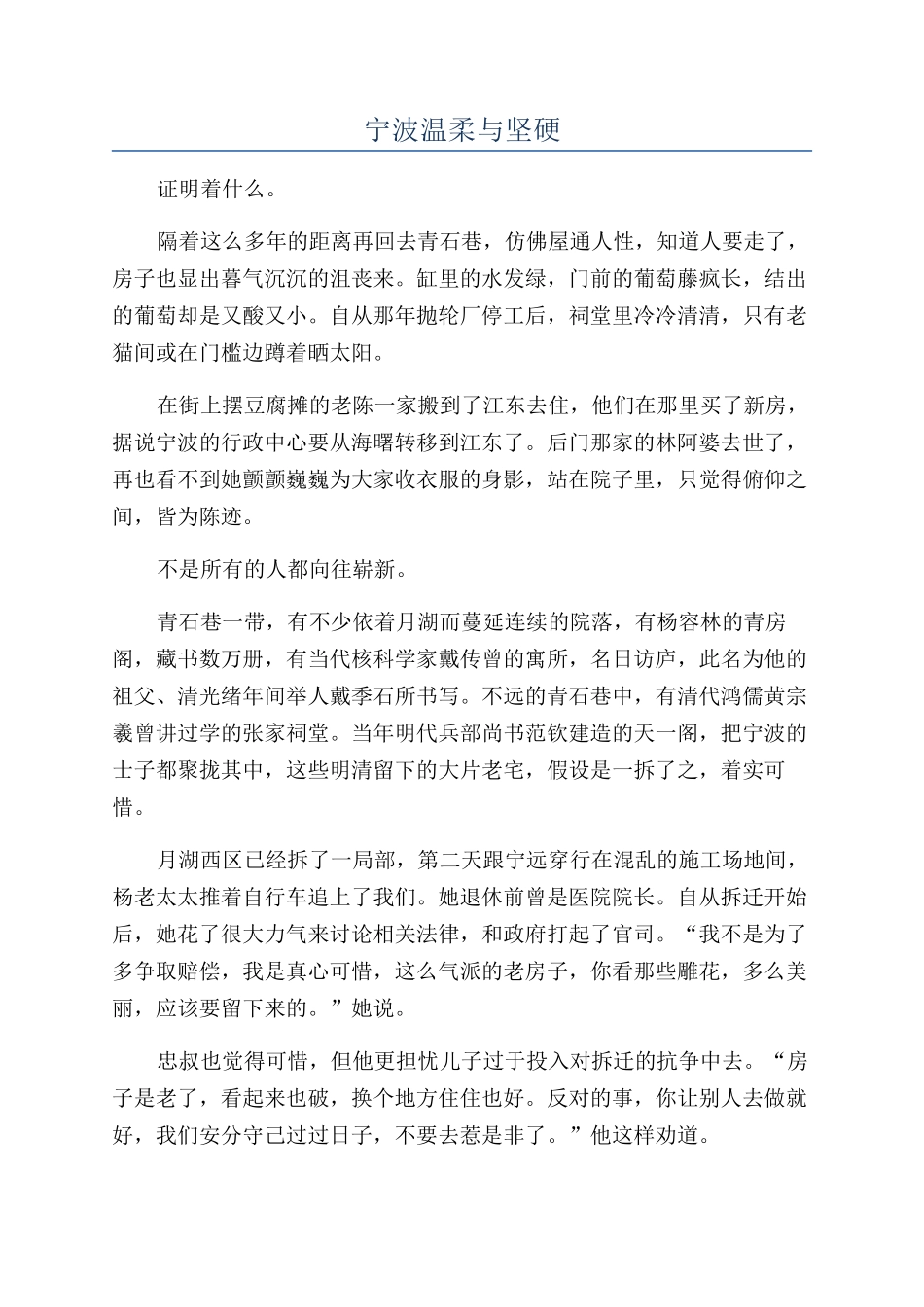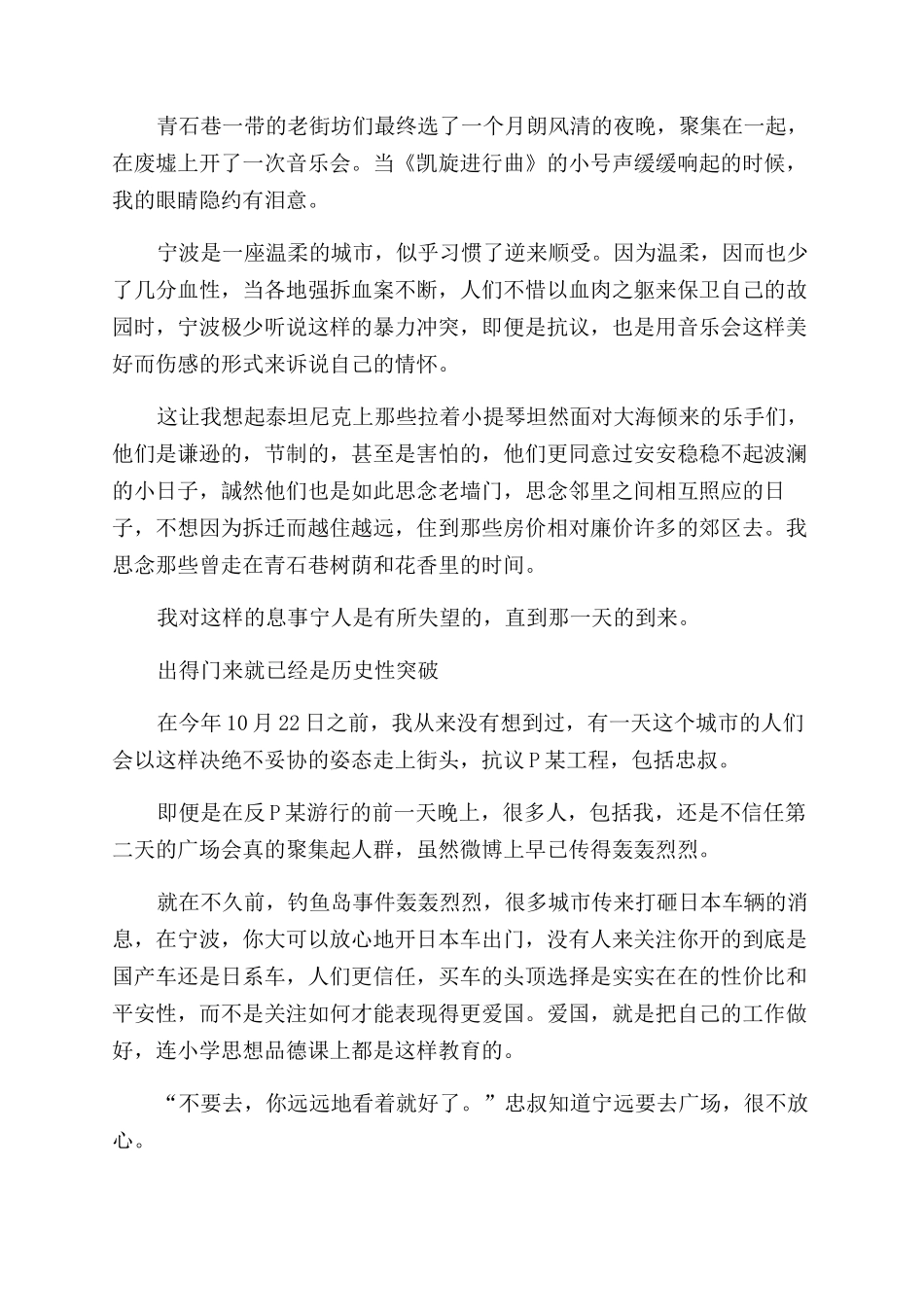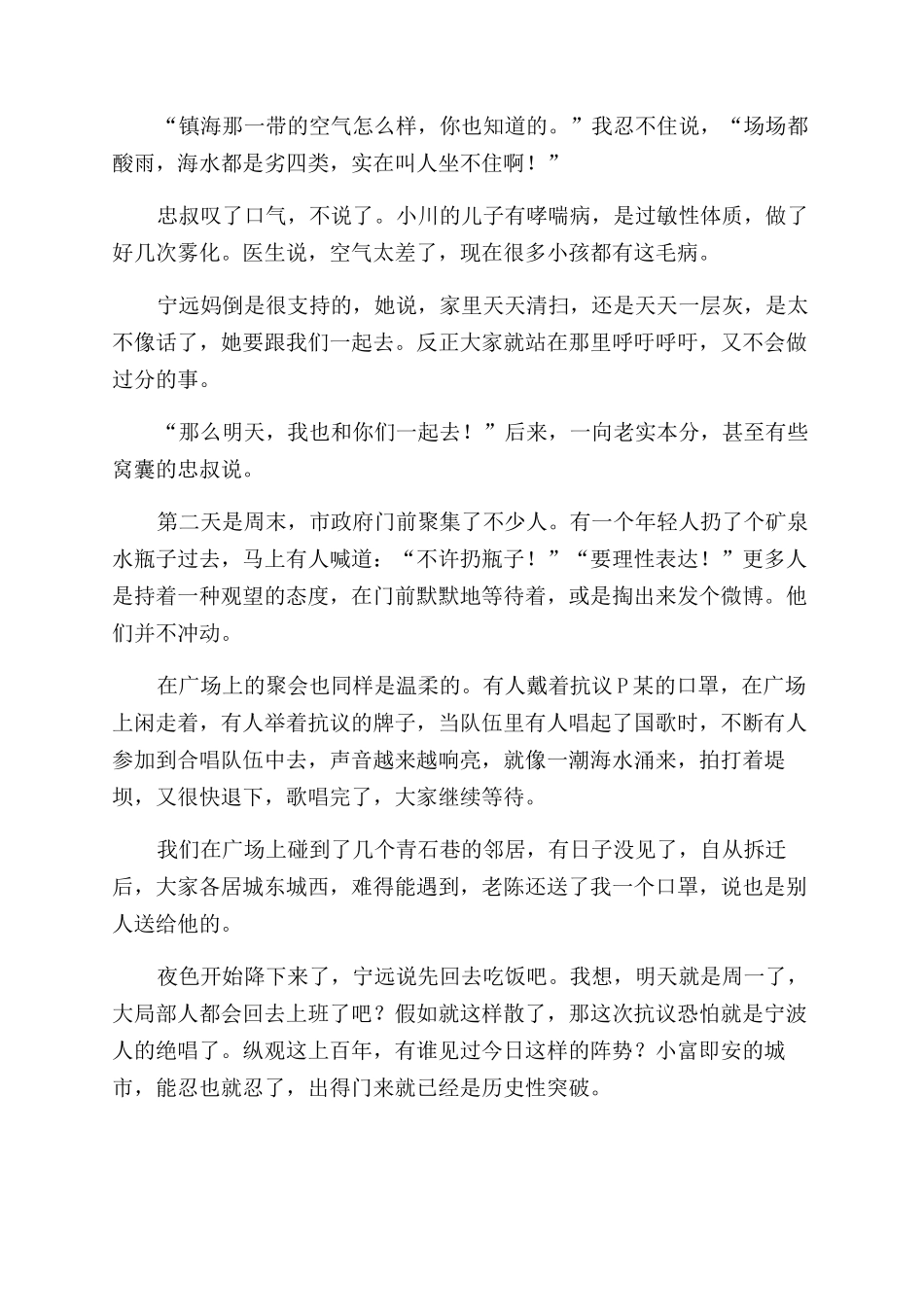宁波温柔与坚硬证明着什么。隔着这么多年的距离再回去青石巷,仿佛屋通人性,知道人要走了,房子也显出暮气沉沉的沮丧来。缸里的水发绿,门前的葡萄藤疯长,结出的葡萄却是又酸又小。自从那年抛轮厂停工后,祠堂里冷冷清清,只有老猫间或在门槛边蹲着晒太阳。在街上摆豆腐摊的老陈一家搬到了江东去住,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据说宁波的行政中心要从海曙转移到江东了。后门那家的林阿婆去世了,再也看不到她颤颤巍巍为大家收衣服的身影,站在院子里,只觉得俯仰之间,皆为陈迹。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崭新。青石巷一带,有不少依着月湖而蔓延连续的院落,有杨容林的青房阁,藏书数万册,有当代核科学家戴传曾的寓所,名日访庐,此名为他的祖父、清光绪年间举人戴季石所书写。不远的青石巷中,有清代鸿儒黄宗羲曾讲过学的张家祠堂。当年明代兵部尚书范钦建造的天一阁,把宁波的士子都聚拢其中,这些明清留下的大片老宅,假设是一拆了之,着实可惜。月湖西区已经拆了一局部,第二天跟宁远穿行在混乱的施工场地间,杨老太太推着自行车追上了我们。她退休前曾是医院院长。自从拆迁开始后,她花了很大力气来讨论相关法律,和政府打起了官司。“我不是为了多争取赔偿,我是真心可惜,这么气派的老房子,你看那些雕花,多么美丽,应该要留下来的。”她说。忠叔也觉得可惜,但他更担忧儿子过于投入对拆迁的抗争中去。“房子是老了,看起来也破,换个地方住住也好。反对的事,你让别人去做就好,我们安分守己过过日子,不要去惹是非了。”他这样劝道。青石巷一带的老街坊们最终选了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聚集在一起,在废墟上开了一次音乐会。当《凯旋进行曲》的小号声缓缓响起的时候,我的眼睛隐约有泪意。宁波是一座温柔的城市,似乎习惯了逆来顺受。因为温柔,因而也少了几分血性,当各地强拆血案不断,人们不惜以血肉之躯来保卫自己的故园时,宁波极少听说这样的暴力冲突,即便是抗议,也是用音乐会这样美好而伤感的形式来诉说自己的情怀。这让我想起泰坦尼克上那些拉着小提琴坦然面对大海倾来的乐手们,他们是谦逊的,节制的,甚至是害怕的,他们更同意过安安稳稳不起波澜的小日子,誠然他们也是如此思念老墙门,思念邻里之间相互照应的日子,不想因为拆迁而越住越远,住到那些房价相对廉价许多的郊区去。我思念那些曾走在青石巷树荫和花香里的时间。我对这样的息事宁人是有所失望的,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在今年 10 月 22 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