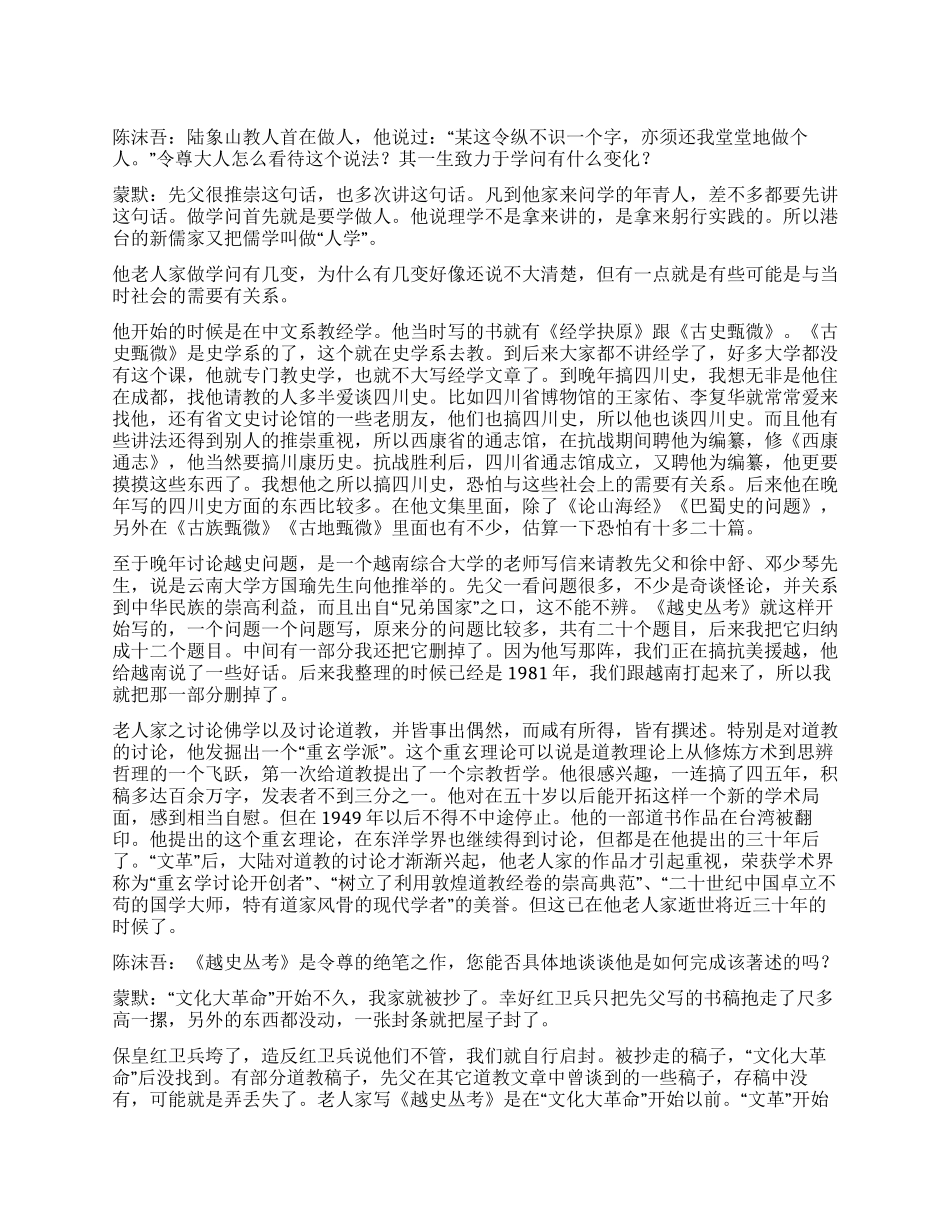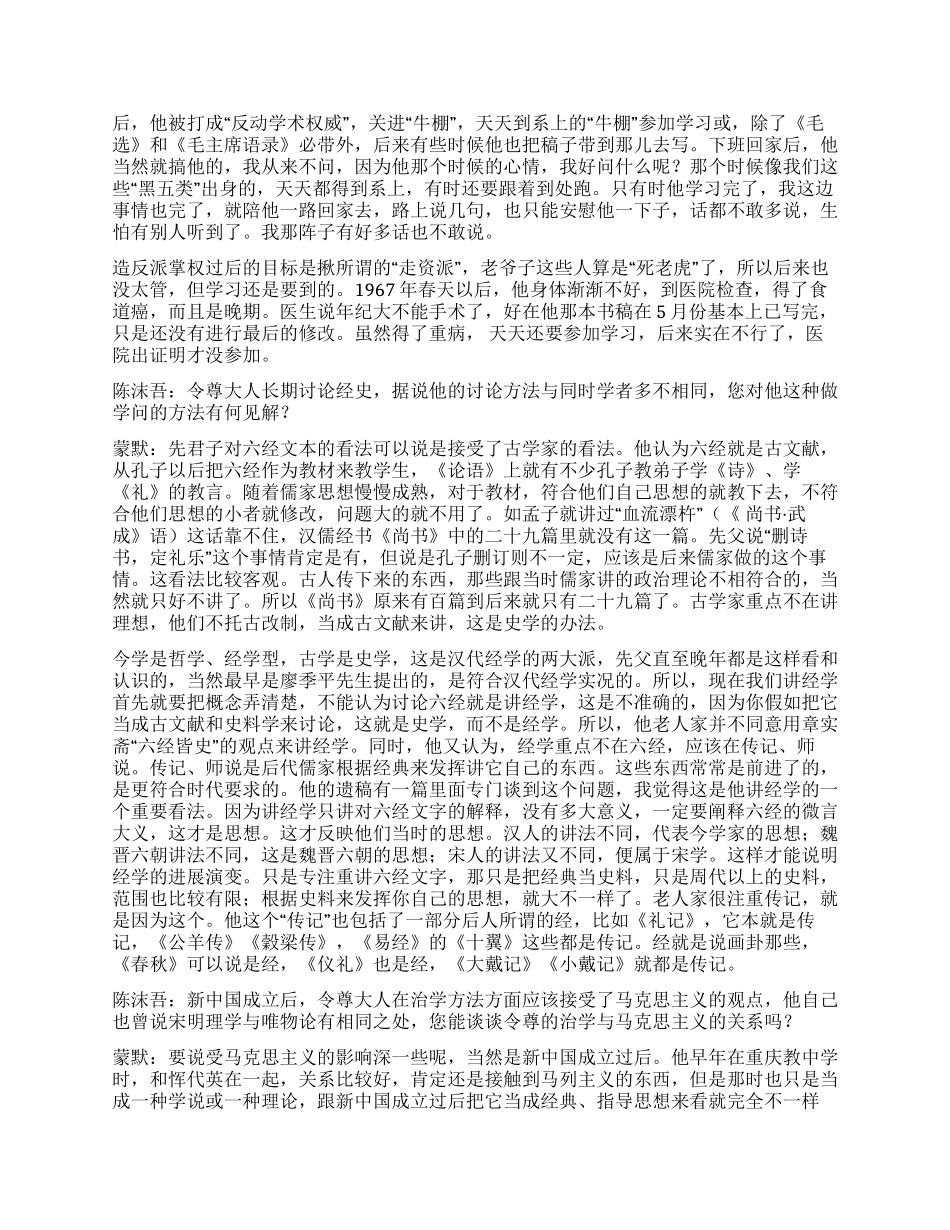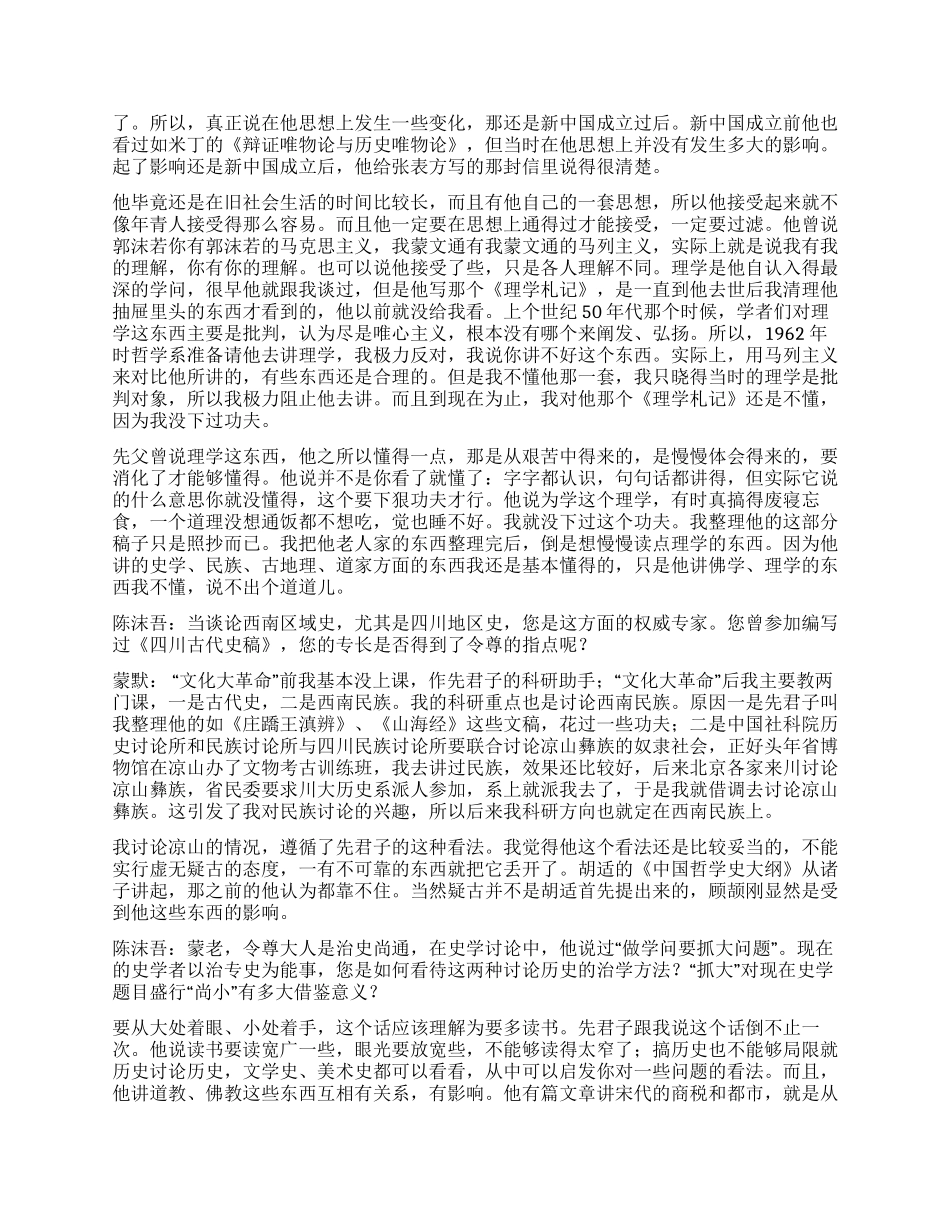“陈沫吾:陆象山教人首在做人,他说过: 某这令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令尊大人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其一生致力于学问有什么变化?蒙默:先父很推崇这句话,也多次讲这句话。凡到他家来问学的年青人,差不多都要先讲这句话。做学问首先就是要学做人。他说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行实践的。所以港“”台的新儒家又把儒学叫做 人学 。他老人家做学问有几变,为什么有几变好像还说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就是有些可能是与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系。他开始的时候是在中文系教经学。他当时写的书就有《经学抉原》跟《古史甄微》。《古史甄微》是史学系的了,这个就在史学系去教。到后来大家都不讲经学了,好多大学都没有这个课,他就专门教史学,也就不大写经学文章了。到晚年搞四川史,我想无非是他住在成都,找他请教的人多半爱谈四川史。比如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李复华就常常爱来找他,还有省文史讨论馆的一些老朋友,他们也搞四川史,所以他也谈四川史。而且他有些讲法还得到别人的推崇重视,所以西康省的通志馆,在抗战期间聘他为编纂,修《西康通志》,他当然要搞川康历史。抗战胜利后,四川省通志馆成立,又聘他为编纂,他更要摸摸这些东西了。我想他之所以搞四川史,恐怕与这些社会上的需要有关系。后来他在晚年写的四川史方面的东西比较多。在他文集里面,除了《论山海经》《巴蜀史的问题》,另外在《古族甄微》《古地甄微》里面也有不少,估算一下恐怕有十多二十篇。至于晚年讨论越史问题,是一个越南综合大学的老师写信来请教先父和徐中舒、邓少琴先生,说是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向他推举的。先父一看问题很多,不少是奇谈怪论,并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崇高利益,而且出自 兄弟国家 之口,这不能不辨。《越史丛考》就这样开始写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写,原来分的问题比较多,共有二十个题目,后来我把它归纳成十二个题目。中间有一部分我还把它删掉了。因为他写那阵,我们正在搞抗美援越,他给越南说了一些好话。后来我整理的时候已经是 1981 年,我们跟越南打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那一部分删掉了。老人家之讨论佛学以及讨论道教,并皆事出偶然,而咸有所得,皆有撰述。特别是对道教“”的讨论,他发掘出一个 重玄学派 。这个重玄理论可以说是道教理论上从修炼方术到思辨哲理的一个飞跃,第一次给道教提出了一个宗教哲学。他很感兴趣,一连搞了四五年,积稿多达百余万字,发表者不到三分之一。他对在五十岁以后能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