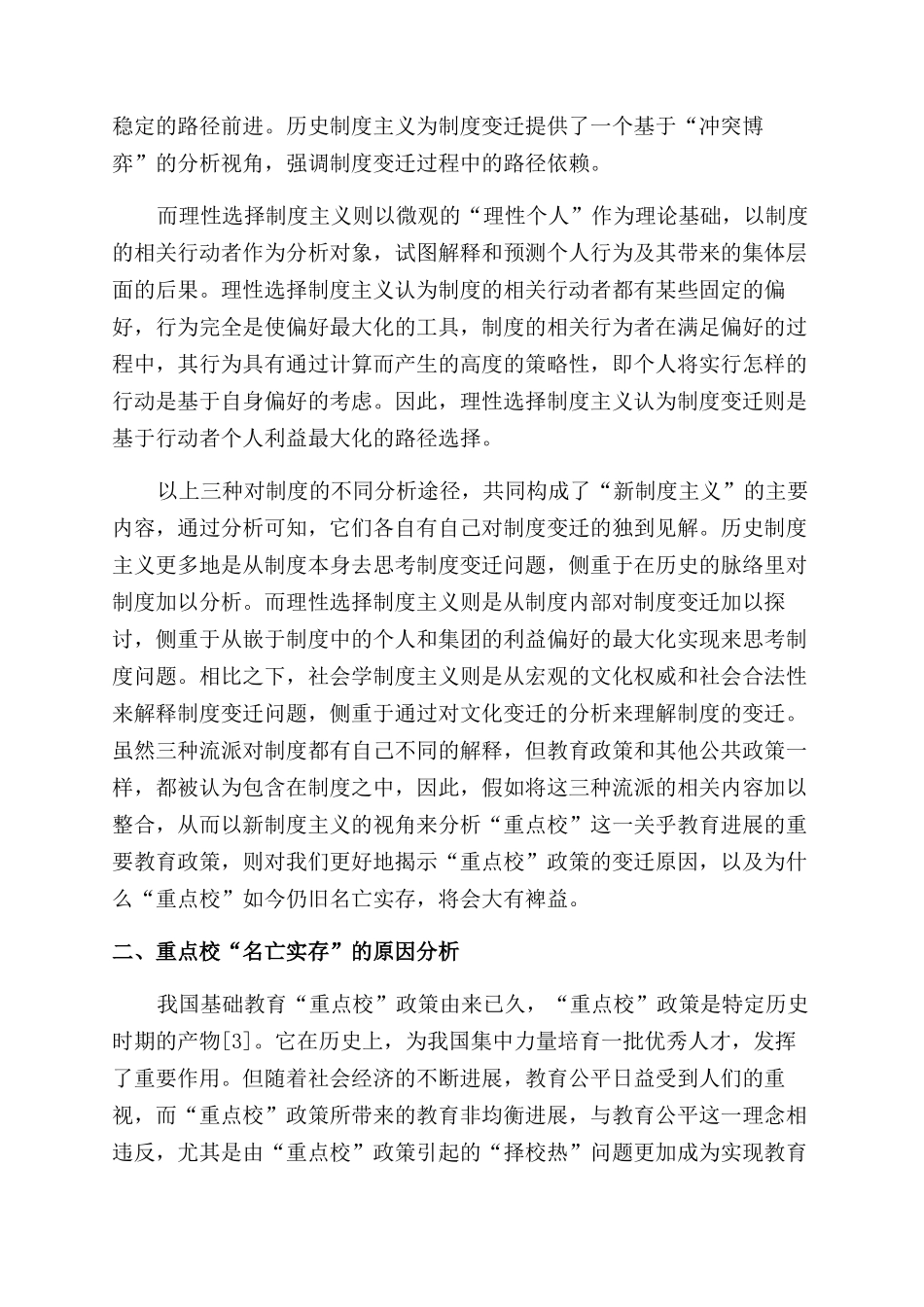新制度主义视角下重点校“名亡实存的原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关系到个人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进展。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飞速进展的今日,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已成为每个人强烈的利益诉求。义务教育阶段作为个人进展的奠基阶段,其教育质量的优劣对个人的成长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与此相关的教育政策便自然更加为人们所关注。政策是对全社会的利益作权威性的分配[1]。“重点校”政策作为一项对义务教育阶段权利与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重要教育政策,其不断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学校与受教育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本文拟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政策以及重点校“名亡实存”的原因作一些分析。一、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随着 20 世纪后半期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主义理论的式微,20 世纪 80年代的社会科学讨论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即重新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并对制度的性质及制度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进行了探讨,并揭示了文化、法律规范、习俗、价值观等在构建人类行为、分配利益与权力、影响个人决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样一种讨论范式被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派别,其内部思想流派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分类是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提到的,他们将“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2]。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就是嵌入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法律规范和惯例等,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在不断地进展变化。在对制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进展演变都与权力有关,而且着重体现权力之间的非对称关系,通过权力间的冲突与竞争,及之间不断的利益博弈,逐渐形成了某些利益集团,这样,制度便会给予这些集团以更多接近制度决策的机会。因此,制度便会倾向于向着有利于某些集团利益的方向进展,从而推动历史沿着某一相对稳定的路径前进。历史制度主义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基于“冲突博弈”的分析视角,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以微观的“理性个人”作为理论基础,以制度的相关行动者作为分析对象,试图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带来的集体层面的后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相关行动者都有某些固定的偏好,行为完全是使偏好最大化的工具,制度的相关行为者在满足偏好的过程中,其行为具有通过计算而产生的高度的策略性,即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