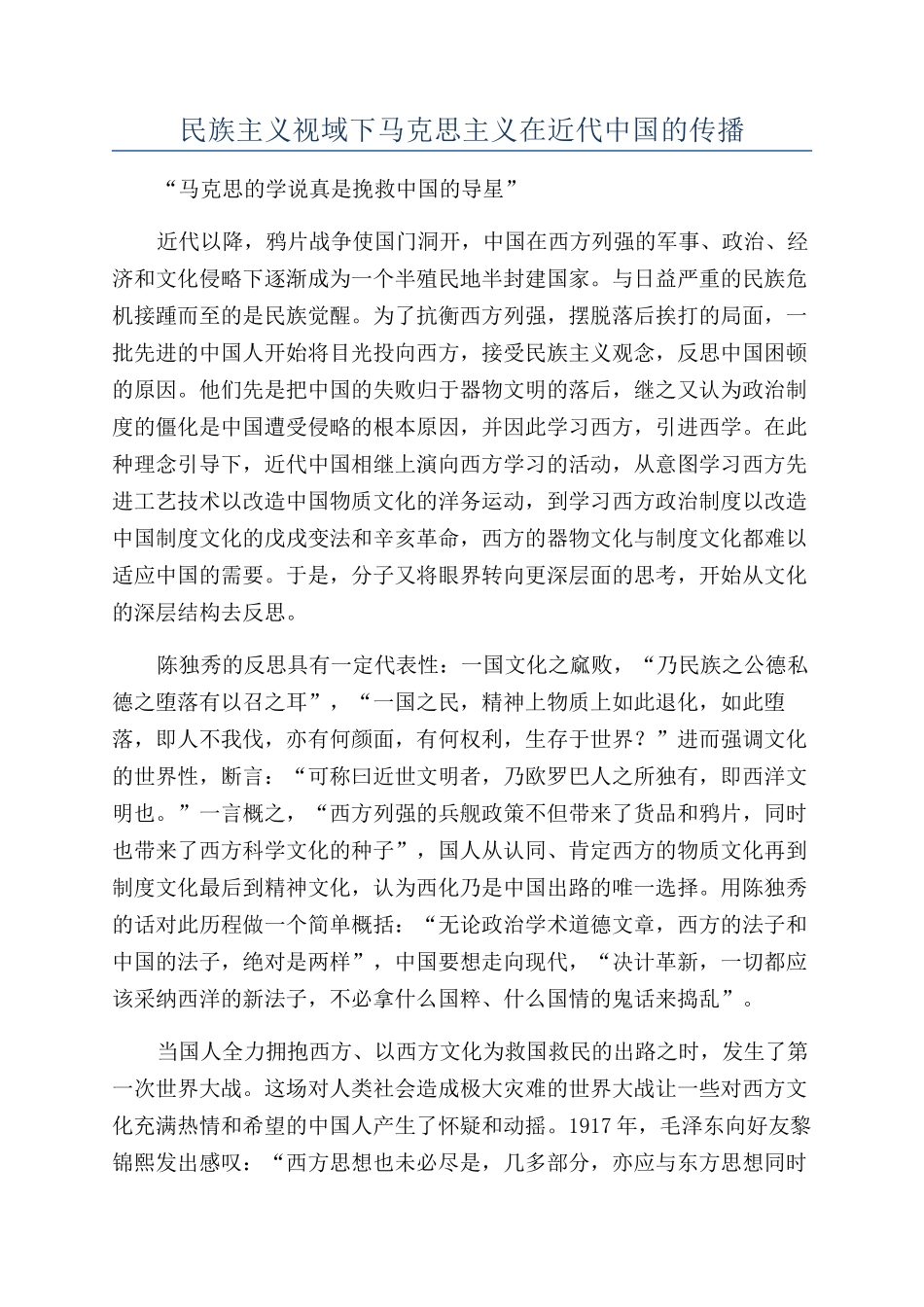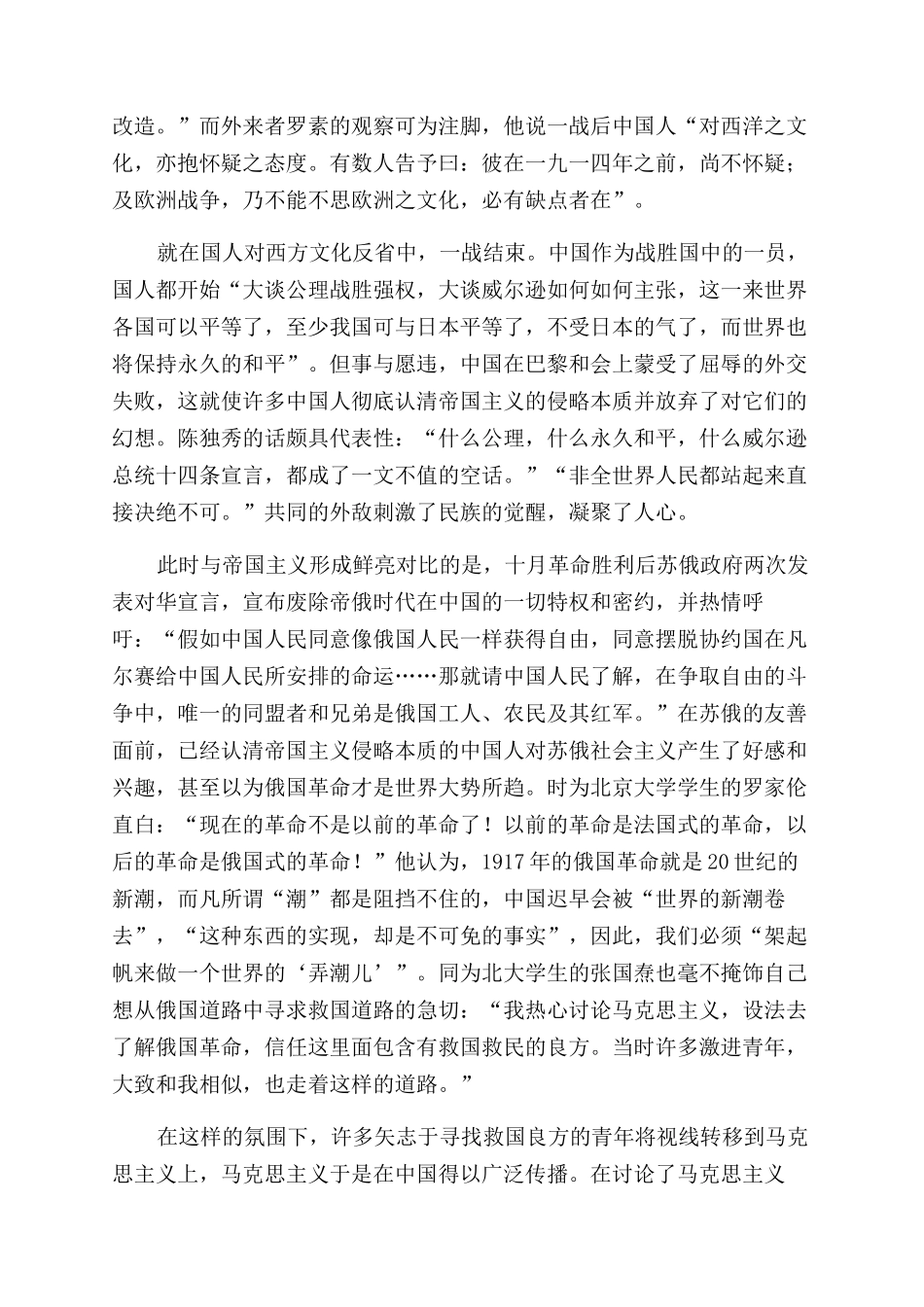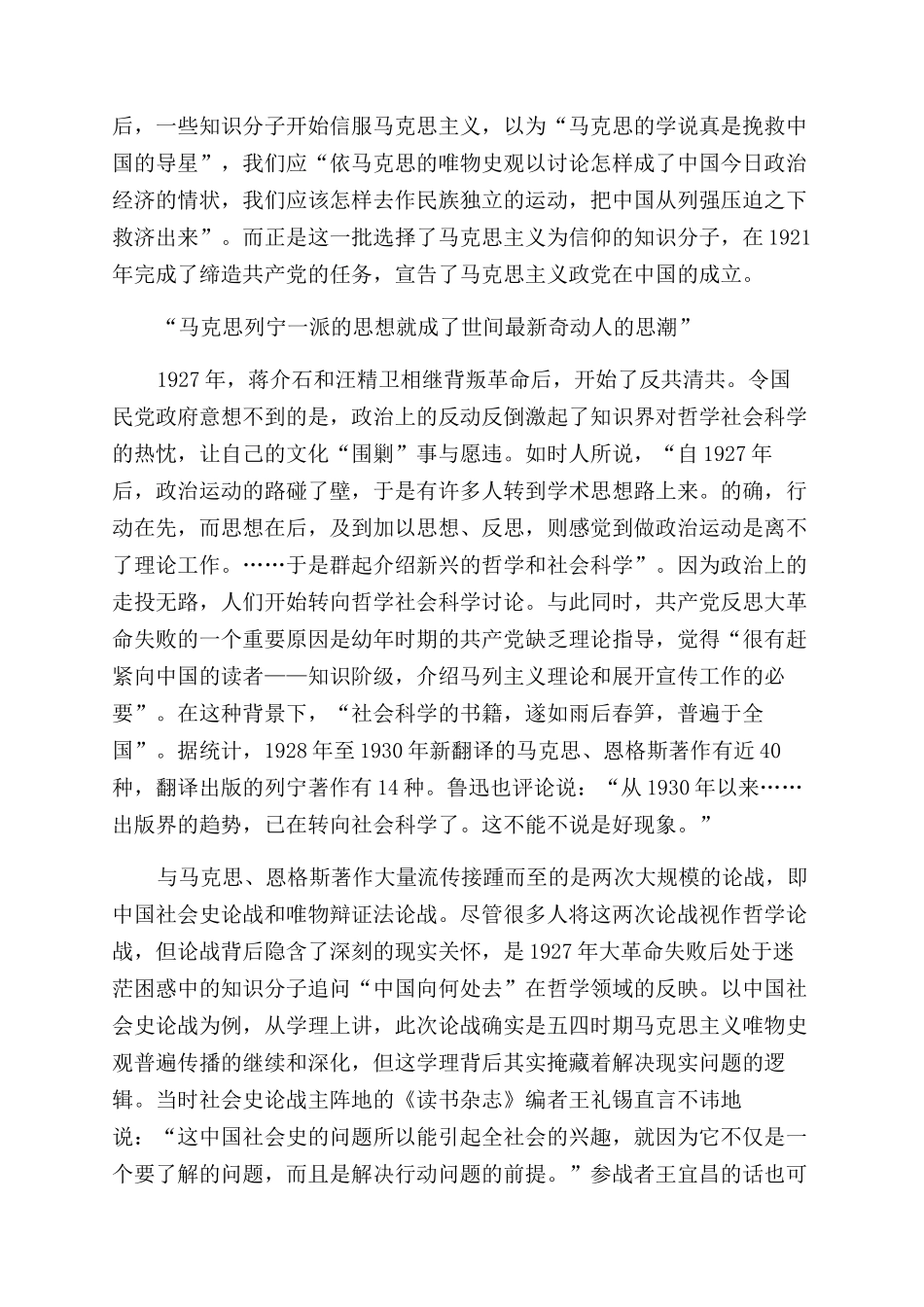民族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挽救中国的导星”近代以降,鸦片战争使国门洞开,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下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接踵而至的是民族觉醒。为了抗衡西方列强,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接受民族主义观念,反思中国困顿的原因。他们先是把中国的失败归于器物文明的落后,继之又认为政治制度的僵化是中国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并因此学习西方,引进西学。在此种理念引导下,近代中国相继上演向西方学习的活动,从意图学习西方先进工艺技术以改造中国物质文化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西方的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都难以适应中国的需要。于是,分子又将眼界转向更深层面的思考,开始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去反思。陈独秀的反思具有一定代表性:一国文化之窳败,“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进而强调文化的世界性,断言:“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一言概之,“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国人从认同、肯定西方的物质文化再到制度文化最后到精神文化,认为西化乃是中国出路的唯一选择。用陈独秀的话对此历程做一个简单概括:“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方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中国要想走向现代,“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纳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当国人全力拥抱西方、以西方文化为救国救民的出路之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灾难的世界大战让一些对西方文化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1917 年,毛泽东向好友黎锦熙发出感叹:“西方思想也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而外来者罗素的观察可为注脚,他说一战后中国人“对西洋之文化,亦抱怀疑之态度。有数人告予曰:彼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尚不怀疑;及欧洲战争,乃不能不思欧洲之文化,必有缺点者在”。就在国人对西方文化反省中,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中的一员,国人都开始“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