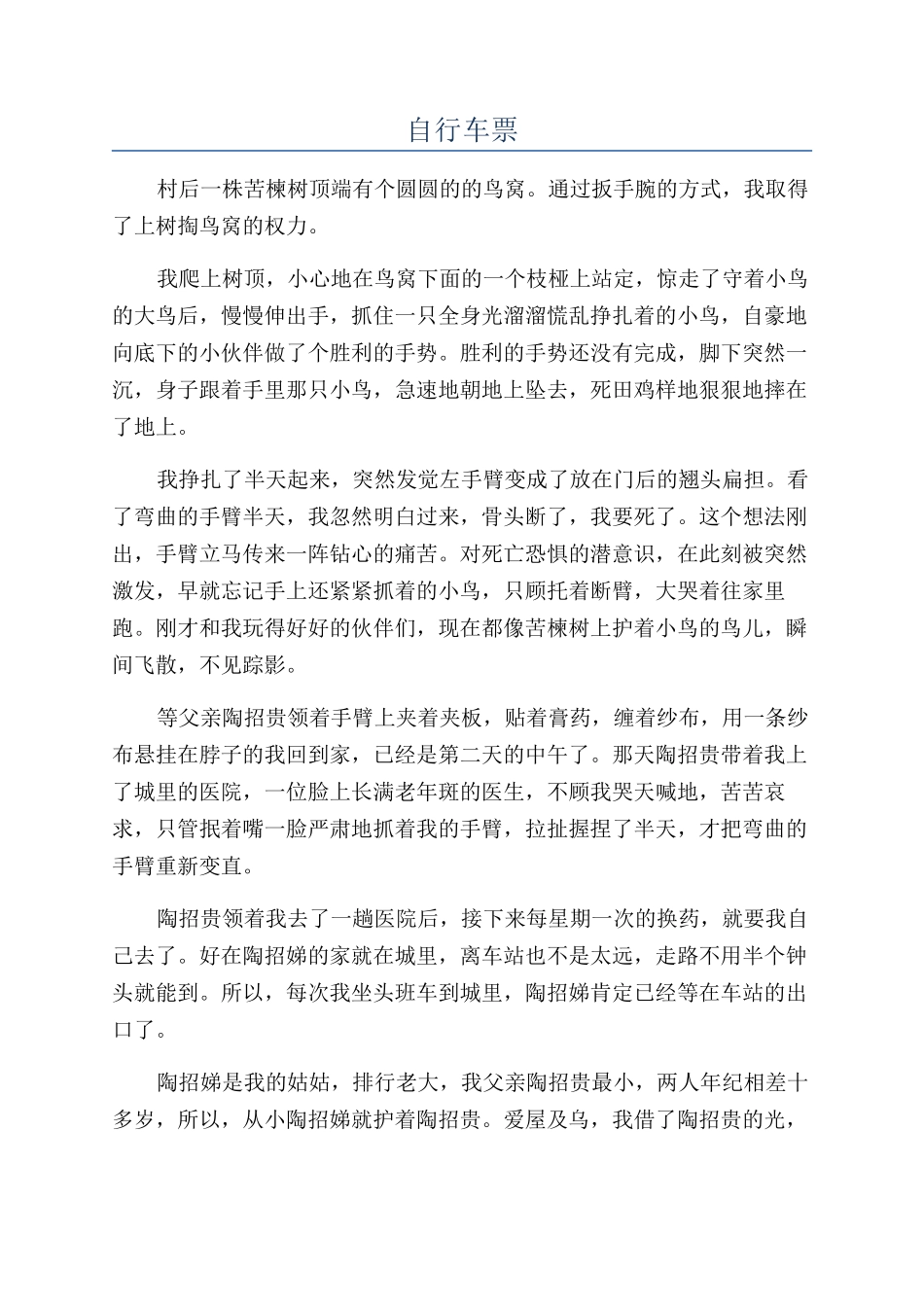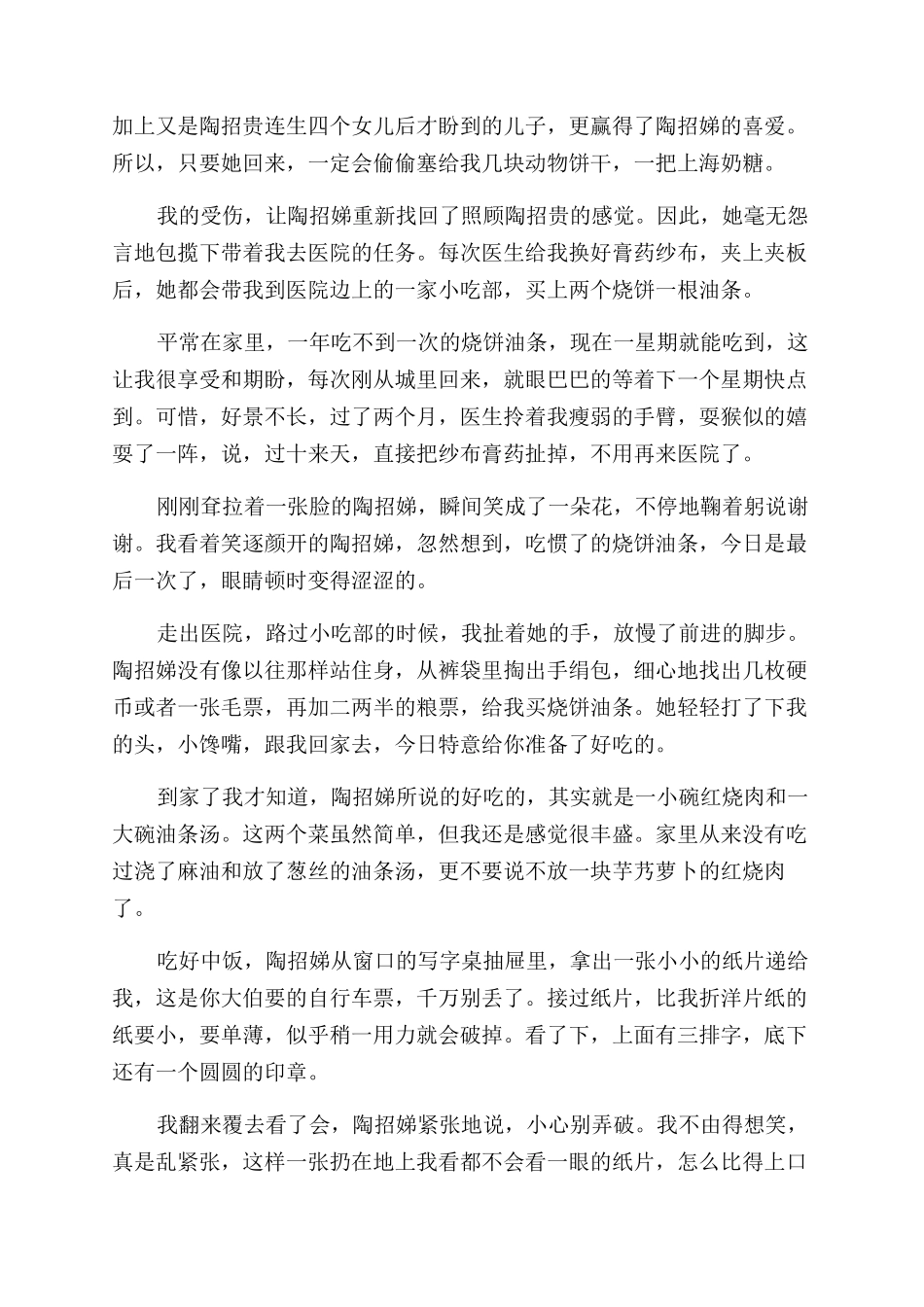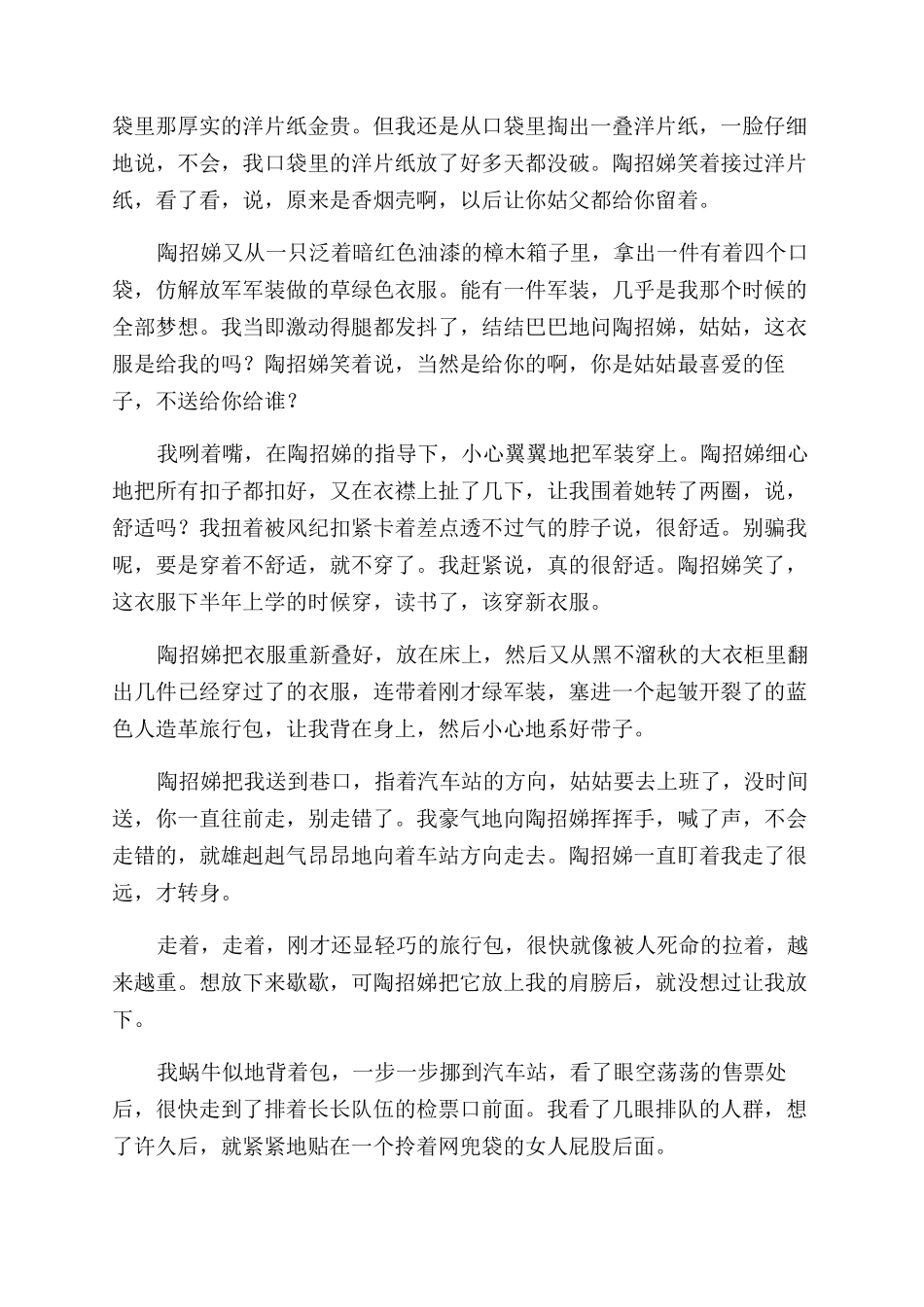自行车票村后一株苦楝树顶端有个圆圆的的鸟窝。通过扳手腕的方式,我取得了上树掏鸟窝的权力。我爬上树顶,小心地在鸟窝下面的一个枝桠上站定,惊走了守着小鸟的大鸟后,慢慢伸出手,抓住一只全身光溜溜慌乱挣扎着的小鸟,自豪地向底下的小伙伴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胜利的手势还没有完成,脚下突然一沉,身子跟着手里那只小鸟,急速地朝地上坠去,死田鸡样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我挣扎了半天起来,突然发觉左手臂变成了放在门后的翘头扁担。看了弯曲的手臂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骨头断了,我要死了。这个想法刚出,手臂立马传来一阵钻心的痛苦。对死亡恐惧的潜意识,在此刻被突然激发,早就忘记手上还紧紧抓着的小鸟,只顾托着断臂,大哭着往家里跑。刚才和我玩得好好的伙伴们,现在都像苦楝树上护着小鸟的鸟儿,瞬间飞散,不见踪影。等父亲陶招贵领着手臂上夹着夹板,贴着膏药,缠着纱布,用一条纱布悬挂在脖子的我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那天陶招贵带着我上了城里的医院,一位脸上长满老年斑的医生,不顾我哭天喊地,苦苦哀求,只管抿着嘴一脸严肃地抓着我的手臂,拉扯握捏了半天,才把弯曲的手臂重新变直。陶招贵领着我去了一趟医院后,接下来每星期一次的换药,就要我自己去了。好在陶招娣的家就在城里,离车站也不是太远,走路不用半个钟头就能到。所以,每次我坐头班车到城里,陶招娣肯定已经等在车站的出口了。陶招娣是我的姑姑,排行老大,我父亲陶招贵最小,两人年纪相差十多岁,所以,从小陶招娣就护着陶招贵。爱屋及乌,我借了陶招贵的光,加上又是陶招贵连生四个女儿后才盼到的儿子,更赢得了陶招娣的喜爱。所以,只要她回来,一定会偷偷塞给我几块动物饼干,一把上海奶糖。我的受伤,让陶招娣重新找回了照顾陶招贵的感觉。因此,她毫无怨言地包揽下带着我去医院的任务。每次医生给我换好膏药纱布,夹上夹板后,她都会带我到医院边上的一家小吃部,买上两个烧饼一根油条。平常在家里,一年吃不到一次的烧饼油条,现在一星期就能吃到,这让我很享受和期盼,每次刚从城里回来,就眼巴巴的等着下一个星期快点到。可惜,好景不长,过了两个月,医生拎着我瘦弱的手臂,耍猴似的嬉耍了一阵,说,过十来天,直接把纱布膏药扯掉,不用再来医院了。刚刚耷拉着一张脸的陶招娣,瞬间笑成了一朵花,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我看着笑逐颜开的陶招娣,忽然想到,吃惯了的烧饼油条,今日是最后一次了,眼睛顿时变得涩涩的。走出医院,路过小吃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