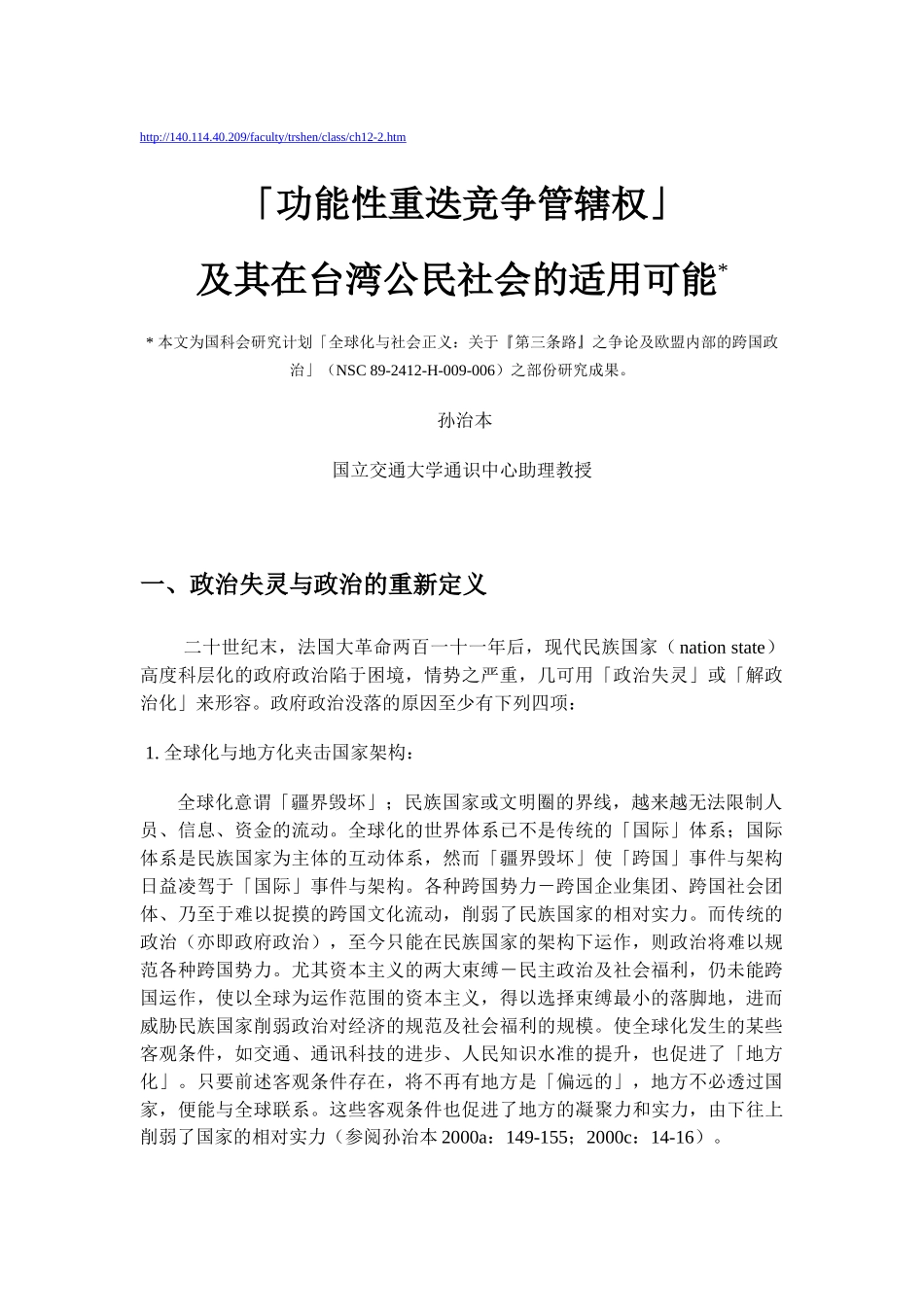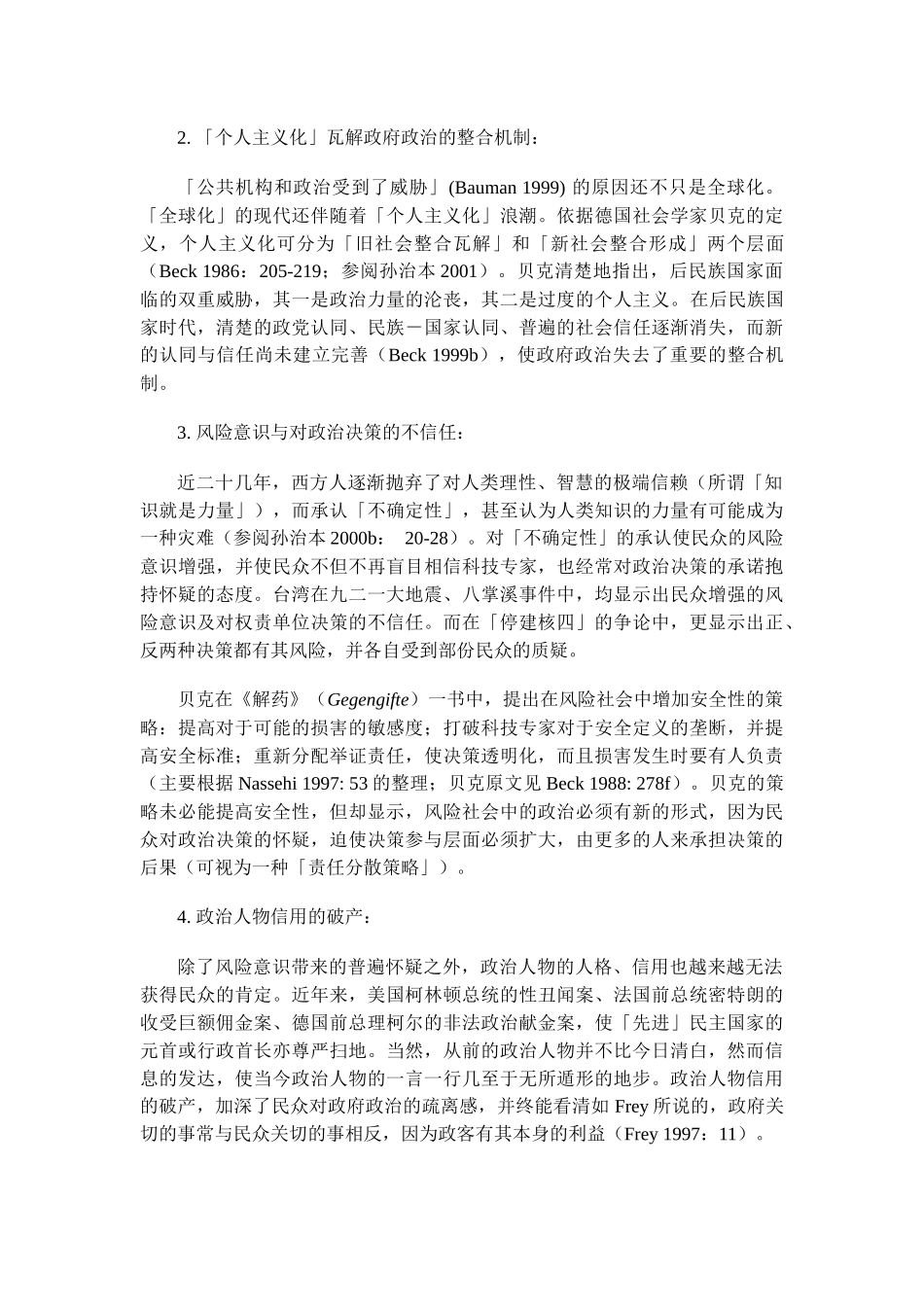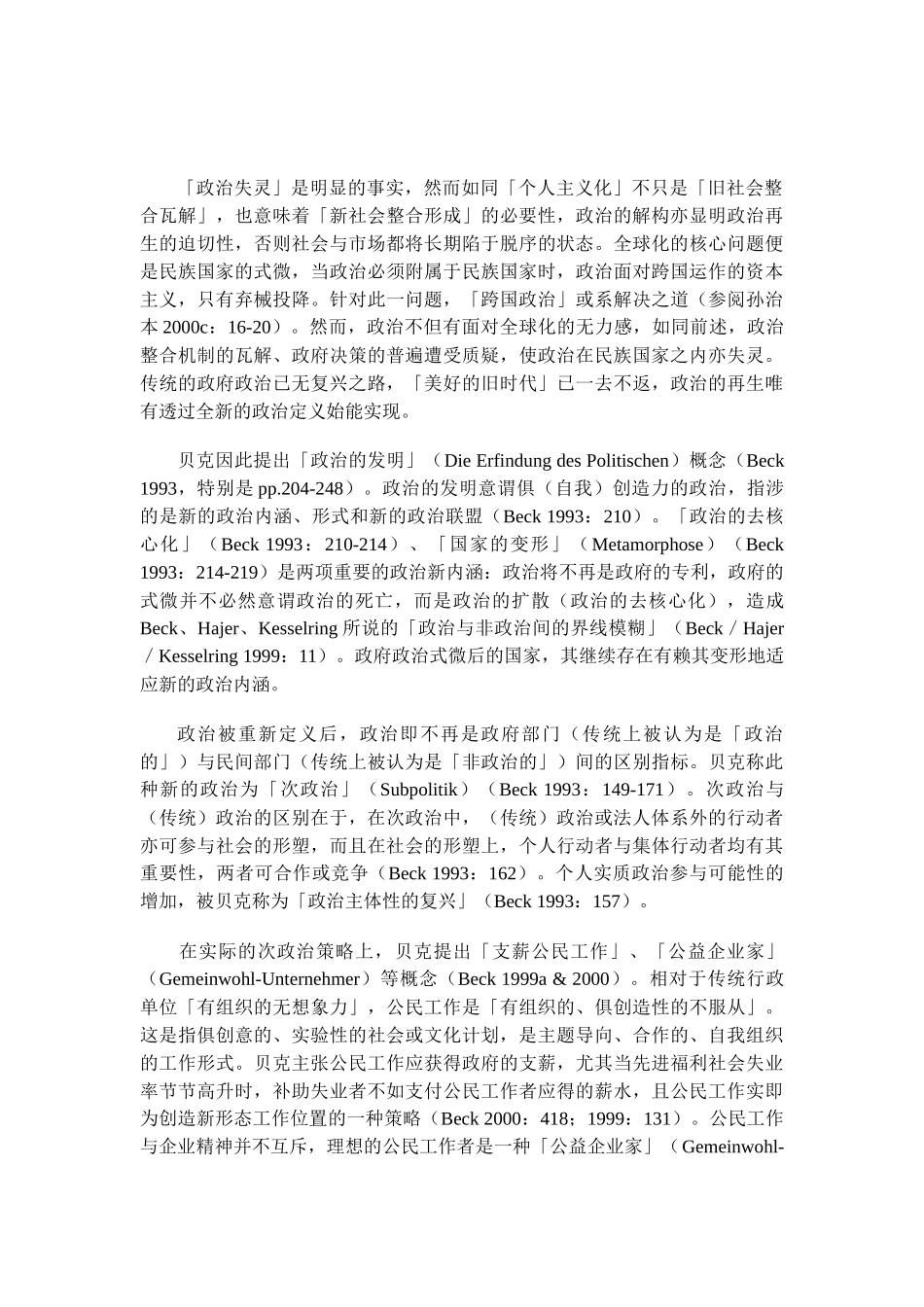http://140.114.40.209/faculty/trshen/class/ch12-2.htm「功能性重迭竞争管辖权」及其在台湾公民社会的适用可能** 本文为国科会研究计划「全球化与社会正义:关于『第三条路』之争论及欧盟内部的跨国政治」(NSC 89-2412-H-009-006)之部份研究成果。 孙治本国立交通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 一、政治失灵与政治的重新定义 二十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两百一十一年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高度科层化的政府政治陷于困境,情势之严重,几可用「政治失灵」或「解政治化」来形容。政府政治没落的原因至少有下列四项: 1. 全球化与地方化夹击国家架构:全球化意谓「疆界毁坏」;民族国家或文明圈的界线,越来越无法限制人员、信息、资金的流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已不是传统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互动体系,然而「疆界毁坏」使「跨国」事件与架构日益凌驾于「国际」事件与架构。各种跨国势力-跨国企业集团、跨国社会团体、乃至于难以捉摸的跨国文化流动,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相对实力。而传统的政治(亦即政府政治),至今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运作,则政治将难以规范各种跨国势力。尤其资本主义的两大束缚-民主政治及社会福利,仍未能跨国运作,使以全球为运作范围的资本主义,得以选择束缚最小的落脚地,进而威胁民族国家削弱政治对经济的规范及社会福利的规模。使全球化发生的某些客观条件,如交通、通讯科技的进步、人民知识水准的提升,也促进了「地方化」。只要前述客观条件存在,将不再有地方是「偏远的」,地方不必透过国家,便能与全球联系。这些客观条件也促进了地方的凝聚力和实力,由下往上削弱了国家的相对实力(参阅孙治本 2000a:149-155;2000c:14-16)。2. 「个人主义化」瓦解政府政治的整合机制:「公共机构和政治受到了威胁」(Bauman 1999) 的原因还不只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现代还伴随着「个人主义化」浪潮。依据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定义,个人主义化可分为「旧社会整合瓦解」和「新社会整合形成」两个层面(Beck 1986:205-219;参阅孙治本 2001)。贝克清楚地指出,后民族国家面临的双重威胁,其一是政治力量的沦丧,其二是过度的个人主义。在后民族国家时代,清楚的政党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普遍的社会信任逐渐消失,而新的认同与信任尚未建立完善(Beck 1999b),使政府政治失去了重要的整合机制。3. 风险意识与对政治决策的不信任:近二十几年,西方人逐渐抛弃了对人类理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