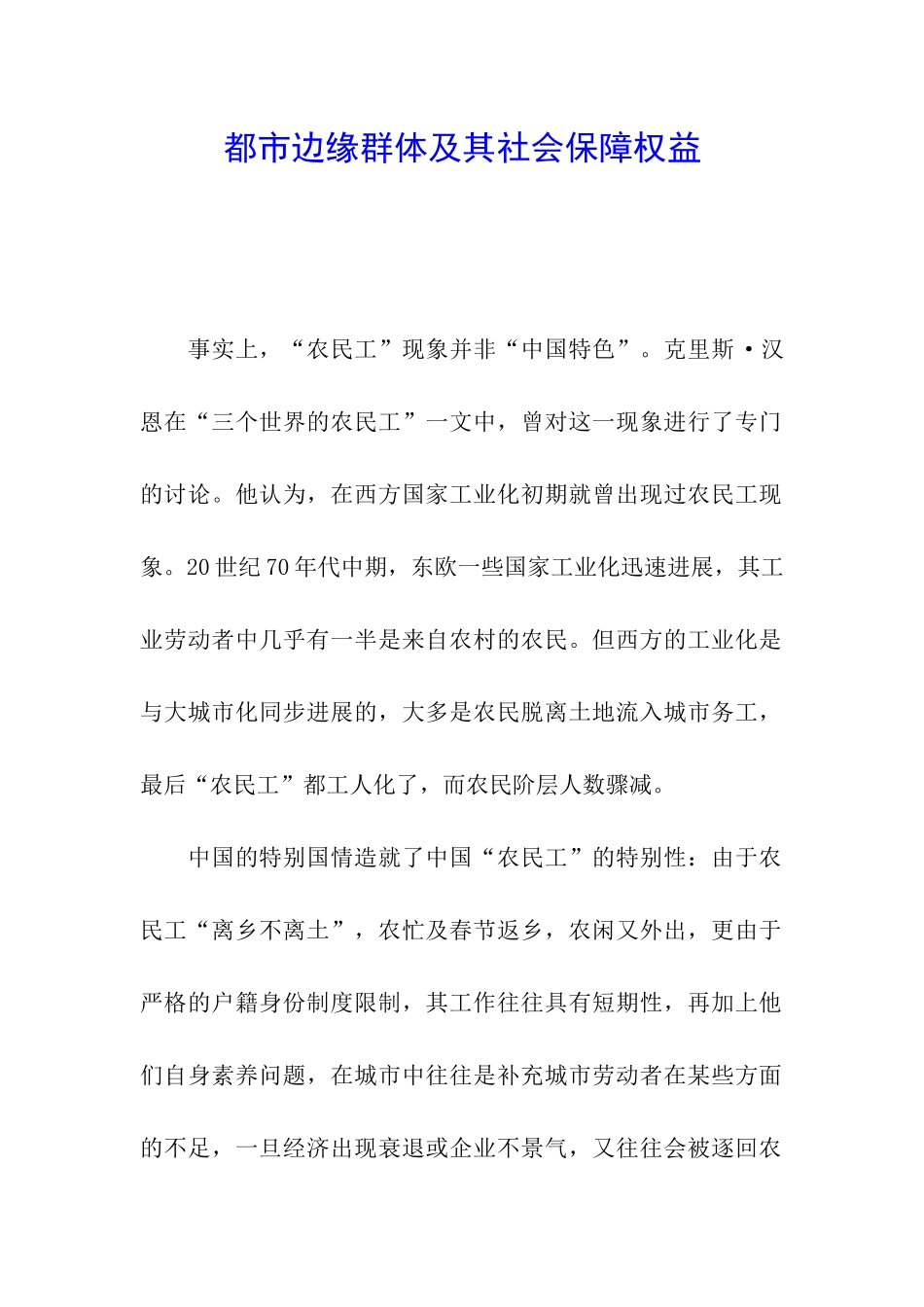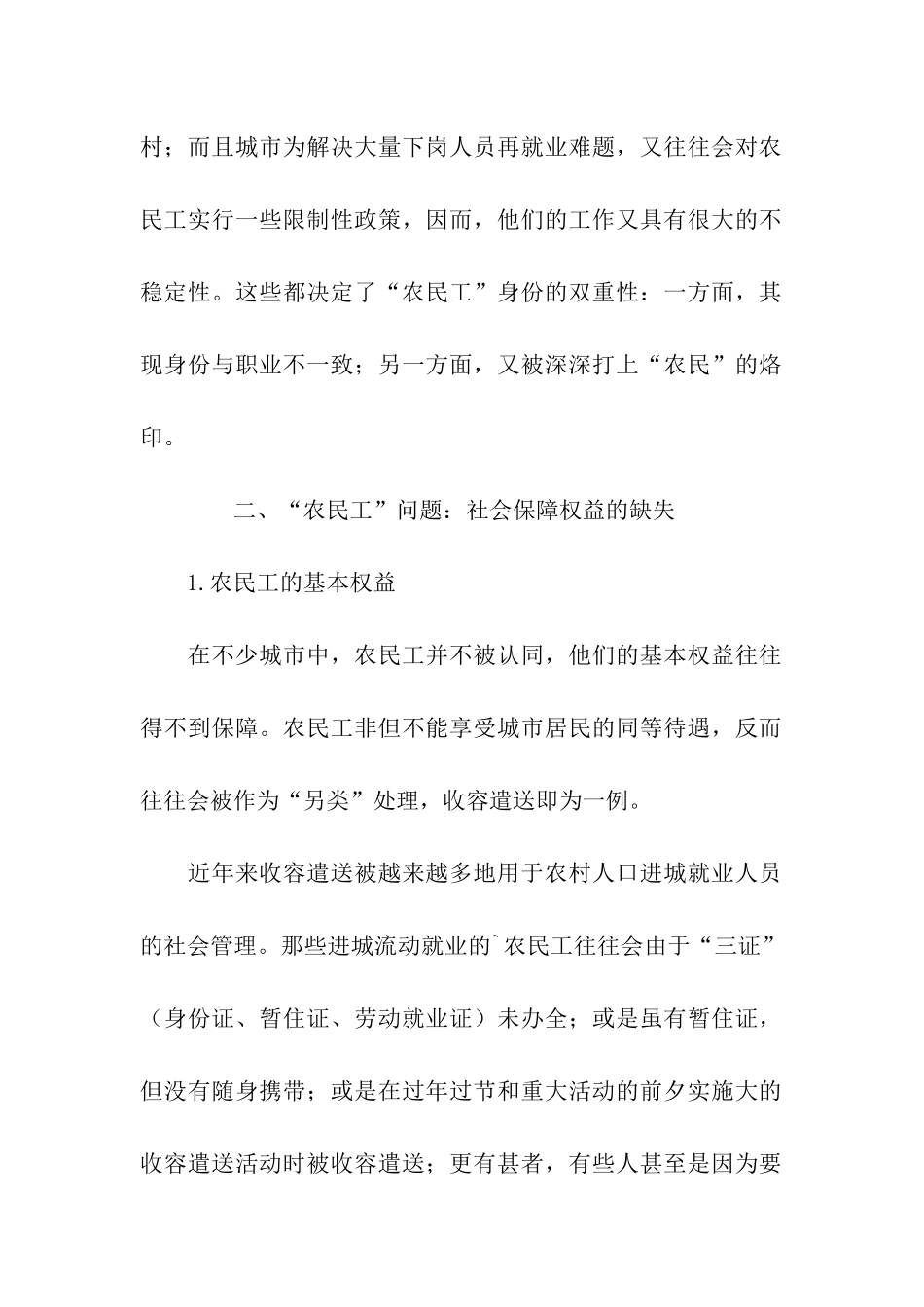都市边缘群体及其社会保障权益 事实上,“农民工”现象并非“中国特色”。克里斯·汉恩在“三个世界的农民工”一文中,曾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就曾出现过农民工现象。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工业化迅速进展,其工业劳动者中几乎有一半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但西方的工业化是与大城市化同步进展的,大多是农民脱离土地流入城市务工,最后“农民工”都工人化了,而农民阶层人数骤减。 中国的特别国情造就了中国“农民工”的特别性:由于农民工“离乡不离土”,农忙及春节返乡,农闲又外出,更由于严格的户籍身份制度限制,其工作往往具有短期性,再加上他们自身素养问题,在城市中往往是补充城市劳动者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企业不景气,又往往会被逐回农村;而且城市为解决大量下岗人员再就业难题,又往往会对农民工实行一些限制性政策,因而,他们的工作又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些都决定了“农民工”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其现身份与职业不一致;另一方面,又被深深打上“农民”的烙印。 二、“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 1.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在不少城市中,农民工并不被认同,他们的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农民工非但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反而往往会被作为“另类”处理,收容遣送即为一例。 近年来收容遣送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农村人口进城就业人员的社会管理。那些进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往往会由于“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劳动就业证)未办全;或是虽有暂住证,但没有随身携带;或是在过年过节和重大活动的前夕实施大的收容遣送活动时被收容遣送;更有甚者,有些人甚至是因为要“凑够”收容任务而遭此厄运。 我国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原来是针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济、教育(-雪风网络 xfhttp 教育网)和安置的措施。这种措施对于开展社会救助、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执行政策的偏颇,收容遣送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化了。事实上,这种做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限制公民自由、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不合理措施。这种强制性措施不仅仅会使进城务工人员的公民权益受到损害,损伤了广阔农民向城镇转移及扩大就业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展,同时也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预期目标。他们绝大多数人连轻微的违法犯罪也没有,这种做法会严格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会由于对立情绪而形成不稳定因素。 2.农民工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