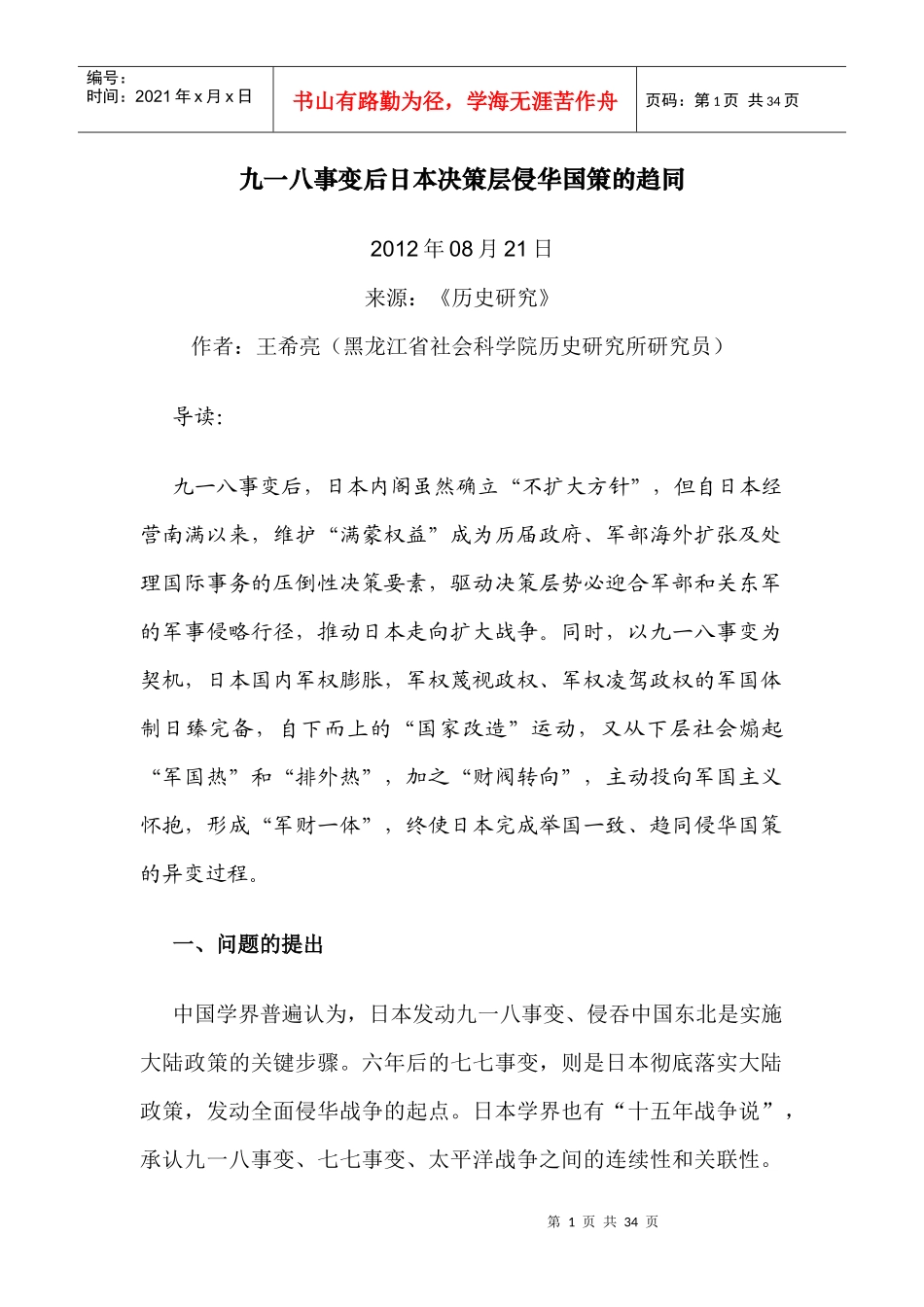第1页共3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34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2012年08月21日来源:《历史研究》作者: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导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虽然确立“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驱动决策层势必迎合军部和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推动日本走向扩大战争。同时,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煽起“军国热”和“排外热”,加之“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日本学界也有“十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第2页共34页第1页共3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34页但是,同样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把研究视角放在“协调派”和“扩大派”的纷争上,片面强调“协调派”的“不扩大方针”,以及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努力”,甚至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客观上出现为日本政府开脱侵华责任的“独走论”和“偶发说”。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日方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1931年9月18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9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论述模式类同。即: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独走论)→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军部为关东军行动转圜→政府追认、承认伪满洲国。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驻华北日军发动武力(偶发说)→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政府决定出兵→走向战争。第3页共34页第2页共3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3页共34页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80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读卖新闻》2005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34.2%,另有33.9%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因此,在探讨战争责任问题搁置至今的原因时,不能忽略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为名,忽略宏观性的俯瞰和把握,“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落入“无构造历史观”的窠臼,从而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原本就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推波助澜,以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自然被引入日本“并非好战”、“没有领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小甬道。这为彻底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投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台了“不扩大方针”。但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