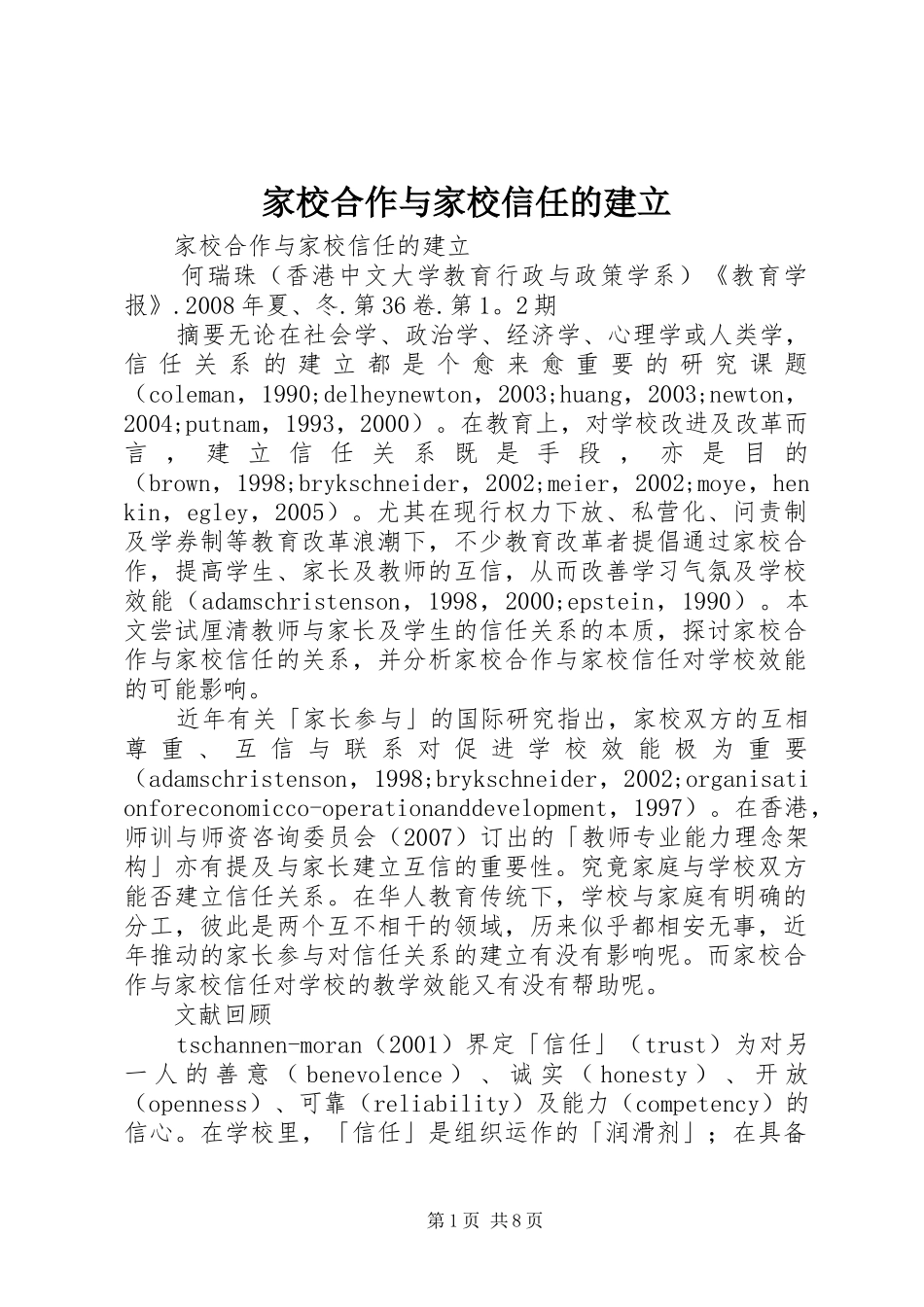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的建立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的建立何瑞珠(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育学报》.2008年夏、冬.第36卷.第1。2期摘要无论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或人类学,信任关系的建立都是个愈来愈重要的研究课题(coleman,1990;delheynewton,2003;huang,2003;newton,2004;putnam,1993,2000)。在教育上,对学校改进及改革而言,建立信任关系既是手段,亦是目的(brown,1998;brykschneider,2002;meier,2002;moye,henkin,egley,2005)。尤其在现行权力下放、私营化、问责制及学券制等教育改革浪潮下,不少教育改革者提倡通过家校合作,提高学生、家长及教师的互信,从而改善学习气氛及学校效能(adamschristenson,1998,2000;epstein,1990)。本文尝试厘清教师与家长及学生的信任关系的本质,探讨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的关系,并分析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对学校效能的可能影响。近年有关「家长参与」的国际研究指出,家校双方的互相尊重、互信与联系对促进学校效能极为重要(adamschristenson,1998;brykschneider,2002;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7)。在香港,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2007)订出的「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亦有提及与家长建立互信的重要性。究竟家庭与学校双方能否建立信任关系。在华人教育传统下,学校与家庭有明确的分工,彼此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历来似乎都相安无事,近年推动的家长参与对信任关系的建立有没有影响呢。而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对学校的教学效能又有没有帮助呢。文献回顾tschannen-moran(2001)界定「信任」(trust)为对另一人的善意(benevolence)、诚实(honesty)、开放(openness)、可靠(reliability)及能力(competency)的信心。在学校里,「信任」是组织运作的「润滑剂」;在具备第1页共8页信任关系的组织,人们毋须浪费精力于互相猜忌之中,能全情投入组织的工作。「信任」亦是人际关系的「凝聚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及关怀,使他们不单要完成更且要做好某项工作,而人在工作当中亦得以成长。tschannen-moran认为「信任」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需要刻意经营的。身为教育领导者,校长及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学校成员(包括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互信关系。就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而言,rempel,holmes,zanna(1985)提出三个层次:(1)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以个体行为为基准;(2)可靠性(dependability)──以个体个人属性(attribute)为基准;(3)可信赖性(faith)──以个体信念(belief)为基准。第三个层次超越个体行为及属性,正如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一样,只要对方有需要,便会委身协助。rotter(1980)认为「信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某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承诺及可信靠的程度。holmesrempel(1989)采用一个更广泛且功能性的定义,提出「信任」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能有助达至正面成果。教育界的学者特别指出,在学校内要建立家校互信,必须透过家长、教师及校长持久而非短暂的合作,而且互信关系对和谐的学校要具有自足价值,同时亦有助促进学生的持续成长(adamschristenson,1998;weissedwards,1992)。adamschristenson(1998)曾在美国进行家校信任程度的研究,调查了132名家长及152名教师,结果显示家长对学校的信任程度与家校合作活动的参与有关。他们指出,信任程度愈高的家长,更多参与学校各项的家长活动。adamschristenson(2000)后来再在6所学校进行相似研究,总共调查了1,234名家长及303名教师,而研究的级别由幼儿教育、小学以至中学阶段。他们进一步发现:家长及教师在幼小学段的信任程度均比中学为高;家长对教师的信任程度比教师对家长的信任程度为高;教师对家长的信任程度与级别无显著关系,但家长的信任程度随年级增加而降低;信任程度与家校沟通的关系最大,可见正面的沟通对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至为重要。就香港而言,在现存一般学校的环境下,第2页共8页家长与学校双方的接触机会不多,互信的基础较薄弱(何瑞珠,2002;ng,1999)。双方必须及早以「正面」接触为起点,让大家对对方有良好的印象,这样才能有效...